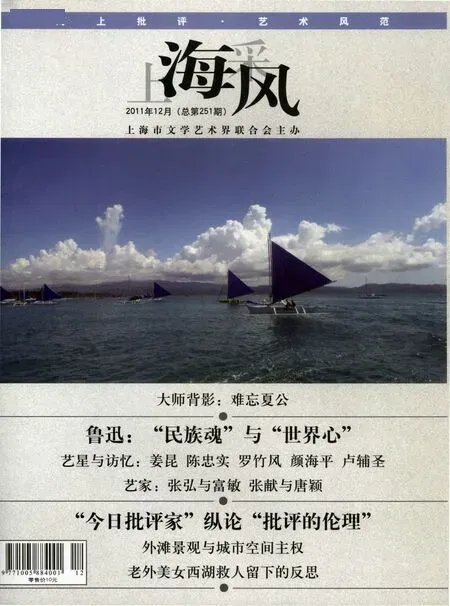美麗戰士
文/影 子
“我是三分之一的父親!”作為一個男人,高興還是無語?旅行家比爾是一聲驚呼,但在確認可能性后,倒是樂于承擔責任,承諾在婚禮上把可能是自己的女兒親手交給新郎。如果比爾因其一貫的單身狀態而無所謂后果的話,建筑師山姆則要糾結很多,畢竟他有家,但山姆也沒有退縮,還有那個糊里糊涂自己都不清楚當年行徑的甩頭黨哈里。
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正盛行著性解放熱潮。這個背景與中國人對應的歷史是隔膜的,而那三個男人如此熱衷于做1/3的父親,歡欣雀躍地戴“綠帽子”那點兒精神,更是與中國的傳統格格不入。機緣巧合,風云際會,2003年時我在美國女權運動的發祥地——芝加哥扮演女兒蘇菲,2011年我在中國的土地上扮演母親唐娜。
我了解即將披上婚紗的女孩兒,從對婚姻的感知中迫切想知道自己生身父親的天命!盡管在過往二十年的獨立生活中,并不存在這樣一個確切應該存在的人。但基于渴望對自己的了解,對“我是誰”的了解,非常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何許人,這是她對未來婚姻生活中角色定位的自我意識,也是對戀人的憧憬和希冀。憑著對美好未來的渴望,她才會對即將見到而從未謀面的三個男人充滿自信的表達“我一定會認得他”——父親。
大多數中國女孩兒會痛恨這個不負責任的男人。在封閉的男權社會中,單身母親帶大的女孩兒會受到多大的歧視和屈辱,是不難想象的,而在這樣悲催的童年環境中長大,心中又有多大的陰影覆蓋,她母親心中孳生了二十年的毒株傘蓋投下的那片陰影。
但愛琴海邊長大的女孩兒是這樣的,生活在愛琴海邊的資深女孩兒——女孩兒她媽媽,對白色婚禮冷嘲熱諷,從未披上過婚紗的女孩兒她媽也是這樣,既然愛過就不后悔,因為這是愛琴海,是一片藍色的海洋文明,“動力樂隊”是女權主義的文化樣式,自然應該有這樣的氣派。
年輕的唐娜是一個少女搖滾樂團“動力樂隊”的主唱,在短時間里與那三個男人發生了關系的她,正是這種“杯水主義”其中的一員。這是個“重口味”的故事。但唐娜的了不起就在于,她獨立承擔了這種后果,獨自把女兒撫養成人,簡直是以一種天真的姿態在戲弄命運。唐娜出場時候,是個希臘某小島上的老板娘,忙碌,拮據,頭發凌亂,不修邊幅;然而,隨著劇情的推進,唐娜和她的兩位好友譚亞和羅茜在一起時候,仿佛重回年輕時候的樂隊現場,動力加速,魅力回來了。那個家庭婦女唐娜在激揚的歌聲和富有彈性的舞步中,蛻變成美國戲劇家尤金奧尼爾筆下的女性,性感,迷人:“一個強壯、安靜、肉感的女人,皮膚鮮活健康、胸部豐滿、胯骨寬大,她的大眼睛像做夢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騷動。她嚼著口香糖,像一條神圣的牛,忘卻了時間,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種種歷練,仿佛只是促使她這樣一顆年輕的漿果的人生愈加成熟,愈加豐盈。
經營山姆圖紙上的酒店成為紀念和理想,獨立撫養女兒,交納沉重的賦稅……20多年生活中會有種種艱難和困惑,這是生活無法回避的現實。但唐娜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對待卻是可以選擇的。“伴著歌聲,朝夢遠行”,是蘇菲的態度,也是唐娜的態度,怎知不會是蘇菲女兒的態度。
作為一出1999年才開始在倫敦首演的音樂劇,《媽媽咪呀!》與別的經典劇目不同,它具有真正的現代性。它并沒有展出一種正確的生活方式,也沒有給你看歷經劫難癡心不改的美好愛情;甚至可以說,里面的戀情都是非常態的:唐娜未婚先孕,山姆訂婚了還和唐娜搞在一起,然后又拋棄了她去結婚;哈里成了同性戀;譚雅結婚三次離婚三次成了有錢人,還勾引可以當她兒子的小酒保;羅茜是一直沒有結婚的老姑娘;女兒蘇菲舉行婚禮時忽然又不想結婚了。有其母必有其女,什么樣的人交什么樣的朋友——一朵從缺陷中奮力開出的花,一旦怒放,必定驚世駭俗。這樣的生活充滿了張力,既痛苦又迷人。《媽媽咪呀!》徹底與古典主義分道揚鑣,還原到現代人生中的本相。即便如此,唐娜也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她們的生活仿佛是由激情、痛苦、隱喻、音樂所匯成的雄偉的尼亞加拉瀑布,恣意飛揚,活一遍就等于別人的幾輩子。
人性的光芒就是世界的語言。生活大多數時間是沉悶而苦痛的,你可能懷上孩子而分不清誰是父親,你可能被親人拋棄在小島上獨自生存,你可能已過不惑之年還在天天修修補補中苦捱,而碼頭上接來的是身著名牌盡情富貴的老友。你有理由為自己的窘迫艱辛而神傷,你也有理由選擇率性的態度歡笑歌唱。同一個風景在不同的心境和狀態下看過去就是不一樣,夕陽不等于逝去,荒涼不等于絕望。
而三分之一的父親們在嬉皮士運動中是被動的,只是跟隨女權主義與個性解放所開創的風氣,年齡漸長后,復歸到傳統社會的框架中。“動力樂隊”解散后也是飄蕩無依,譚雅斯凱這個80后卻不一樣,他來自于島外世界,帶著對愛情與事業的夢想,將和蘇菲一起去外面的世界尋找未來。這是女權主義發展到女性主義階段的必然認知:不再是“把男人吸引過來踩在腳下”,而是“要與男性團結在一起,共同用正義去戰勝邪惡,是男女更加平等的一種自信,就是說你想好接受我了,但我想沒想好接受你還不一定哪。
演出《媽媽咪呀!》,總有看過的人對我說,你確實符合音樂劇女一號的所有特質了,外形,聲音,能力,氣場,你可以去演花木蘭和穆桂英,只要有合適的作曲和編劇,無疑這些生長在腳下這片土地上的形象都跟唐娜一樣,是一群美麗戰士,而且更為亙古久遠,浪漫堅毅,我們有沒有勇氣和天才來唱出她們的故事呢?與《媽媽咪呀!》類似,我把它們設想為一個個女性主義的歡樂故事,永遠年輕,永遠歡樂,永遠熱淚盈眶——七十年代或更為久遠的日子,雖不能至,亦在歌聲中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