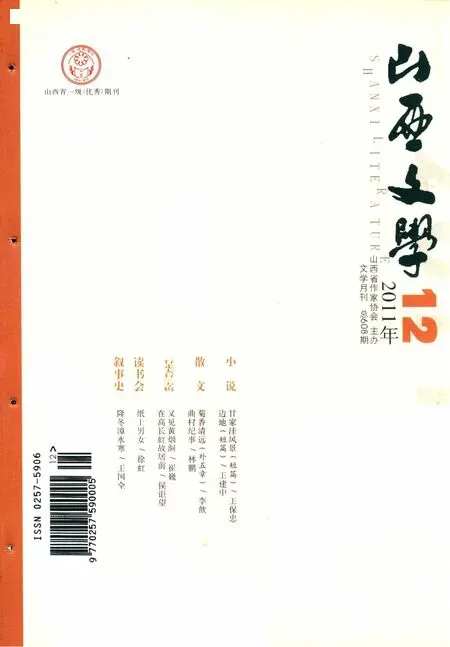隆冬漳水寒
王國全
虛幻的理想與嚴酷的現實
1968年底,我和同學們來到山西,在一個叫長勝的村子里插隊落戶。去插隊那一年,我16歲。同村插隊的同學共有20多人。
對于上山下鄉,我當年曾有過一些極其幼稚的想法。下鄉之前,我曾在北京郊區參加學農勞動。那時,上山下鄉已經是我們不得不認真考慮的人生抉擇。在京郊一座幽靜的農家院落中,我見到過幾位剛剛落戶的知青。我覺得他們無拘無束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頗有浪漫色彩,很受吸引。我還讀過《邊疆曉歌》,這本描寫支邊青年的小說也使我對未來的插隊生活產生了美好的聯想。
然而,真的要遠離家鄉,到偏遠的農村去生活,畢竟令人恐慌。在下鄉前的一段時間里,背井離鄉的憂慮困擾著我們。到1968年的12月,我們都明白:命運已經決定了,我們已別無選擇。對于前途的一切思慮都淹沒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之中。
離開北京前,我跑了幾家書店,買了許多農業技術書籍。有同學問:“想當農業專家嗎?”我笑而未答。想象中的“田園牧歌”和“邊疆曉歌”式的插隊生活,在一步步向我走來。
插隊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在我的感覺中,雖然沒有多少“田園牧歌”的色彩,可是真的頗有一點“邊疆曉歌”的味道。我們長勝村的插隊知青,有好幾位是喜歡文藝而且頗有文藝天資的。在插隊初期,他們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排演了節目,如《紅燈記》、《收租院》等。這些,給插隊初期的生活增添了絢麗的色彩。同學們還自編自演了知青歌曲,開頭的歌詞是“風梳頭,雨洗臉……”。
可惜,這段日子太短暫,太短暫了。
來到長勝村后不久,我們20多個知青就分到了六個生產隊,每個隊四到五人。由于村里還沒有準備好給我們集體居住的房子,我們就都按所在的生產隊分散住進了老鄉家里。
我和三位女生分到了第四生產隊之后,獨自一人住進了村北的一間小屋。房主是一位小伙子,和我們知青關系甚好。這是一間西房,顯然是歷經了多年的煙熏火燎,屋頂是黑的,墻壁也是黑的。窗子很小,只能透進很少的光線。空蕩蕩的土炕上,放著我的一只漆成黃色的木箱和簡單的行李,這就是我全部的財產了。在離開長勝村許多年之后,我依然不時地記起我在村里住過的那間小屋,回憶起那一段夢想與幻滅交織在一起的日子。當然,更多地記起的,是那時艱辛的勞動與生活。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1969年的春天,有這樣一個早晨。天還沒亮,生產隊長就把我喊醒了。在黑黢黢的田野上,我跟在牲口后面撒糞肥,奔跑了許多來回,天才剛剛透亮。早飯是送到地里的。與我同隊的有三個女同學,每天早晨留一位女同學做早飯。那一天的早飯又是玉米面煮餅子。餅子很硬,有一種苦澀的味道。然而,我們那時已經懂得,能夠吃飽肚子就是最高的享受了。我疲憊地靠著糞堆坐著,吃著盛在瓦罐里的煮餅子,無意之間,看見了坐在對面的那個50多歲的漢子,并且注意到他正在吃的飯食。他的早飯是摻了谷糠的窩頭。由于谷糠摻得太多,窩頭變得很松散,他不得不雙手掬成碗狀,捧著那窩頭吃。食物在他嘴里咀嚼著,良久,才艱難地咽入喉管。我看著他吃窩頭,仿佛自己的喉頭也在發緊。直到他終于吃完了那窩頭,我才深深舒了口氣,并且暗自慶幸我們插隊知青享受著每月44斤原糧的待遇,有純玉米面餅可吃。雖然我們也經常要忍受饑腸轆轆的感覺,但是比起當地農民來,生活還是要強一些的。
當時在生產隊里,我們和當地農民一樣干活,包括最累最臟的活計。有很多勞動是在相當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挖溝澗”。本文寫到這里,我要鼓起勇氣,讓那段塵封已久的記憶在這里復活。我在《白皮回憶錄》中有這樣的相關記述:
山西農村的廁所,是磚砌的又大又深的井一樣的建筑。淘廁所時,把上面的稀糞掏干之后,還剩下一層很黏稠的沉積層,叫做“溝澗底兒”,要挖的正是它。
我要下溝澗了,穿上高靿膠靴,換上一身破衣服,還聽了一個伙伴的話,戴了頂草帽。一架梯子放進溝澗口,那溝澗口本來就不大,又放了梯子,勉強能夠下去人。我小心翼翼地一級一級下去,盡量不蹭上井壁。下到最后一級,再下面就是糞了。“下呀!”有人在上面喊,我才發覺自己的動作竟然停頓了。我把腳從梯子上移開,朝糞中踏下去。軟和的糞使我的腳下陷、下陷,終于,我接觸到了軟綿綿的底層。這時,我的意識深處閃出一個念頭:我是站在糞里了!梯子升了上去。
我適應了溝澗中的陰暗之后,看清四周都是發黑的磚,粘滿了糞。抬頭向上看,半個溝澗口被石板擋住,另外半邊敞著,從那里吊下來一只糞桶,一把鐵锨。我的任務,就是用鐵锨把糞桶裝滿。
這工作絕非輕而易舉。四周的磚壁上都是糞,我不能自由地揮舞鐵锨。雖然腳下到處都是糞,可它們是如此“滑頭”,如此易流,我幾乎捕捉不住它們。
過了一會兒,我漸漸學聰明了。先把腳邊的糞挖開,讓自己有一個立足之地。腳下靈活了,就可以更主動地向糞“進攻”了。我把它們全部趕到一邊去,然后,哪里有糞膽敢朝我流過來,我就先挖掉它!就這樣,糞在一點點地減少。
糞桶一次又一次地被提上去,又放下來。從桶沿上、井口上,一滴滴糞汁滴落而下。它們落下的聲音滴滴答答地響著,回蕩在這洞穴般的溝澗中。幸虧戴上了草帽。
也不知干了多久,我忽然感到頭暈,仿佛還記得糞中是有一些有害氣體的。而且,溝澗里的涼快已經變成襲人的寒氣了。幸而,我的工作在這時結束了。梯子放了下來,我上去了。我是滿不在乎地上去的,反正都一樣了。
關于我們在農村經受的磨難,在這篇文章中是無法一一記述的。我曾獲得過一張五好社員獎狀,可以作為這一時期艱辛勞碌的證物吧。
盡管生活中有諸多困苦,但當時也有一些應對困苦的理念,比如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我們當時是認真地相信這些的。
在插隊的初期,我們這一群食僅可以果腹、衣僅可以遮體的青年人,憑著一腔熱情,也曾試圖改變農村的面貌。我們搞了科學實驗,譬如玉米優種繁育、點播耬,等等。當時我們20多個知青分散在6個生產隊,但都在一個大村子里,住的地方相距也不太遠,彼此經常有交流溝通。為了科學實驗,同學們時常在一起切磋,共同實施這些試驗。
我們那時認真地相信自己可以改變農村的面貌,相信自己是在干一番“大事業”。我自己是這些試驗的特別熱心的參加者和推動者,也曾將希望維系在這些大膽而艱苦的嘗試上。但是,這些試驗都失敗了。現在回想起來,即使這些試驗成功了,又能怎樣呢?

長勝村的知青在排練節目/作者供圖
我終于明白了,我們這些知青沒有能力去改變農村的面貌,來農村時的那些想法,其實都只是虛幻、不切實際的“理想”。在現實面前,這些虛幻的理想很快就破滅了。虛幻的理想破滅之后,我們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然而,前途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呢?
小屋燈下,踏上自學之路
記得那是1969年10月的一個晚上,我躺在黑洞洞、陰森森的小屋里,守著孤零零的一只木箱和一盞孤燈,面對黑漆漆的屋頂和四壁,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在人生的某些時刻,能夠從紛紜迷茫的世事中抽出身來,進行冷靜的思考,往往會受益匪淺。
在那個晚上,我想了很多很多。那時,下鄉初期的熱情還沒有完全消退,生活的艱辛和肉體的痛苦都還可以忍受。我甚至打算在農村科學實驗上再下一番功夫。我覺得,在農村再堅持兩三年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但是,兩三年以后會怎樣?五年十年以后又會怎樣?當時回答這些問題的,卻只有幾句空泛的口號。令人憂慮的是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希望。
那天夜里,我下了一個決心:自學。決定自學,這是我生活歷程中的一個轉折點,是我在長夜中為自己點燃的新的希望之光。我在“文革”前只讀了一年初中,如果不通過自學來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識,將來怎么可能有出路呢?
其實,在更早的時候,我就為自學做過準備。前面曾提到,我在下鄉前做到書店買了許多農業技術書籍。我在這里隱瞞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當時還跑了幾家舊書店,買了許多數、理、化書籍。我不得不隱瞞著,因為那時人們對數、理、化諱莫如深。下鄉初期,對“自學”二字我連想都不敢想。后來,我逐漸認識到“再教育”并不像預期的那個樣子。在這偏遠的鄉村,在我獨自居住的小屋里,“思想改造”也是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來進行的。
就這樣,在黑洞洞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燈光下,以木箱代替桌子,我獨自一人踏上了艱苦而漫長的自學道路。多少個夜晚,我蜷伏在木箱旁,學啊,學啊……回想起來,令人百感交集啊。
生活很艱苦,勞動也很繁重,還要自學,就更是苦上加苦。但我那時有極強的、無法壓抑的求知欲望。艱苦生活的重壓之下,求知欲反而愈發強烈。我也很清楚,在當時的氛圍下,學習“數、理、化”是犯忌的事情。但我下決心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走自己選擇的路,即使碰得頭破血流也心甘情愿!
1970年春天,我在倒虹吸工地當民工時,曾經住在直徑1米的水泥管子里。晚上,我趴在自己住的水泥管子中,繼續進行著自學。
開始,我的自學是秘密進行的。到后來,我自學的事情漸漸泄露出去了。有人問我為什么自學,我總是回答為了搞科學實驗。這當然也是我進行自學的目的之一。但我還有一個深藏心底的愿望,當時卻只能守口如瓶,這愿望就是上大學。
我在北京師大附中上學的時候,就把讀大學作為努力的目標。如果沒有“文革”,我們這些師大附中的學生是能夠順利升入大學的。雖然經過“文革”風雨的沖刷,在中學接受的熏陶卻并未完全消失。用當年的話來說,叫做“流毒沒有肅清”。上大學的愿望,像一支微弱但卻不可泯滅的燭光,在我的潛意識中燃燒。
1970年秋收時節,縣里組織一批知青到外村搞“運動”,大部分同學都去了。我因在村里籌備辦一個小工廠(這“小工廠”其實只是曇花一現),沒有去。同村插隊的一位同學作為赤腳醫生,也沒有去。村里只剩下四五個知青,這使我們預先感受到了后來真的只剩下四五個人的時候的那種滋味。有一天,我忽然想和赤腳醫生同學一起出去逛逛,看看在各村搞“運動”的同學們。他欣然同意了。
我們沿山路登上山頂,眼界頓時開闊了,心情也很舒暢。這時,我們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談到了將來可能離開農村的問題。盡管是小心翼翼,盡管只是談到“可能性”,話一出口,我們還是互相對視了一眼。須知,在那時,“扎根農村一輩子”還是一條金科玉律哪。
遭受打擊,促成《山村的早晨》誕生
1971年春天,我早早地就從北京回了村。不久,傳來了“太行五七大學”招生的消息。“太行五七大學”是一所什么學校,我至今也不知道。但我那時興奮異常,上大學的愿望終于有可能實現了!
為了報考“太行五七大學”,我每天復習功課到深夜。在我住的小屋的土炕上,鋪蓋占了大約二分之一的面積,另一半攤滿了各類書籍:代數、幾何、三角、化學、物理……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背著行李卷,走進了大學新生的行列。夢中的大學校門是圓拱形的,就像我們附中的校門一樣。夢境雖然清晰,畢竟是夢。
第二天,我懷著極大的希望,去縣里報名。接待我的兩位干部,態度極為和藹可親。他們讓我回去安心勞動,說上大學的愿望,他們一定認真考慮。我誠惶誠恐地告退,懷著希望回了村。
然而,當時這類上大學的機會,是屬于知青中有一定名氣的代表人物的。我根本排不上號,但又不甘心,徒勞地爭取了幾次,毫無結果。
大學沒上成,是對我的一次巨大打擊。上大學是我那時最高的人生愿望,可想而知,這打擊對我是多么殘酷。我受到的打擊不僅僅在于大學沒上成,而在于我根本就沒有獲得參與競爭的資格和機會!我就像是一個被生活遺棄的人。自插隊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命運對我是不公平的,生活捉弄了我。這種捉弄,遠比農村生活的艱辛更讓人難以承受。
我的自信心在崩潰,心緒如翻江倒海。到哪里去尋找一根結實的繩索,來維系我的即將傾覆的心靈之舟呢?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開始寫作一部插隊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山村的早晨》。可以說,下決心寫這部長篇小說,就是我為自己尋找的維系心靈之舟的繩索。
剛開始動筆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能寫出小說來,但內心的種種情感又驅使著我去寫。我只能自己拯救自己,從命運的泥沼中掙扎著爬出來。《山村的早晨》的寫作,就是在這樣的情感沖動中開始的。
最初的文稿是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寫出的。那時正值春耕大忙,幾乎沒有空閑時間。我只能見縫插針,能寫10分鐘就寫10分鐘。每天晚上,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小屋,感覺肉體中最后一點精力已經耗盡的時候,一提起筆來,奇跡就出現了,我感到周身重新充滿了活力。
寫作是秘密進行的。一方面,我擔心自己粗糙笨拙的“作品”被別人笑話;另一方面,就如同以前學習數理化一樣,寫小說也有可能被當做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我獨居的小屋再次慷慨地為我提供了方便。歷時一個月,終于寫了130頁。這就是《山村的早晨》的第一稿,是寫在極其粗糙的稿紙上的。現在回想起來,這130頁讓我自己都感到不勝驚訝。
有人說“插隊出詩人”,這話是有道理的。在我插隊的那個縣,有不少知青才子。我們長勝村的知青集體中也有一些才子和才女,像丁東、繆力、惠文、丹妮、張軍等。
但是,與這些知青才子相比,我的情況是不同的。我在來農村前只讀了一年初中,文化素質是很欠缺的。我生長在工人家庭,沒有受到過多少文學的熏陶。況且,從小學高年級起,我就酷愛自然科學;我喜歡數學,喜歡航空模型和礦石收音機的制作;我景仰居里夫人,向往儒勒·凡爾納描繪的科幻世界。那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會拿起筆來寫小說。
到農村以后,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許多新鮮的或辛酸的感受,有許多深沉的感慨,想要抒發,以至于我好幾次動了這樣的念頭:寫點什么吧!在勞動的間隙,田間地頭休息的時候,我也曾琢磨過那幻想中的“作品”的某幾個片段。這幾個片段,就像天邊的云彩一樣漂浮在我腦子里,但很快就會消散,消散得無影無蹤。
然而,生活中的沉重打擊如同颶風一般,猛烈地向我襲來,它把那“天邊的云彩”卷了來,并讓濃云化雨,傾盆大雨,在我面前降臨了!
《山村的早晨》的最初文稿就這樣誕生了。恰如一位原內蒙知青在回顧插隊經歷時所說:“上山下鄉的暴風和泥濘,并沒有泯滅知青這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青年人在生活的搏擊面前表現出不肯回頭的勇氣,種種磨難神奇地迸發出一種局外人難以理解的、璀璨的火花。”
在寫《山村的早晨》之前,我恰巧看過三本小說:《牛虻》、《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是這三本書,為我提供了最初的寫作知識。
寫完《山村的早晨》第一稿,我已經有勇氣把文稿拿給同學們看了。盡管小說的文字極為粗糙,描寫人物就像是填寫“履歷表”,同學們還是給了我熱情的支持,還提了中肯的修改意見。在大家的鼓勵下,6月中旬,我回北京寫《山村的早晨》第二稿。大家的鼓勵給我注入了信心,我當時真心地希望為下鄉知青寫出一部小說來。北京的夏天很熱,汗流浹背,但寫作條件比長勝村強多了。在北京,又寫了近300頁,《山村的早晨》的第二稿已完成了大約三分之二。
知青集體的最后一次盛會
1971年7月下旬,我帶著已寫出的《山村的早晨》文稿返回長勝村。
我乘汽車回到縣城時,同村的同學雨銘來車站接我,我們一起回到“祠堂”。這是我們長勝村知青新搬的住處。原來分散居住在老鄉家,直到不久前才搬到這里。至此,長勝村知青想集體住一起的由來已久的愿望,總算實現了。
祠堂的院子不小,已經種上了各種蔬菜。茄子、白菜、西紅柿,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北房前有寬闊的房檐,檐下是用兩塊寬厚的石板搭成的石凳。院里還有同學們自己挖的一個地窖,用來儲存土豆、胡蘿卜等。
我和雨銘住西房,他已經把房子收拾得很干凈。
在北京時,聽說村里知青搞了一個“每日音樂會”,每天晚上,祠堂里歌聲琴聲不絕于耳。這是插隊的第三年了,最初的盲目熱情已經消退,思想的禁錮也已經松弛,一股清新的風透過這剛剛打開的小小縫隙,吹進了長勝村知青中間。
然而,自我陶醉的作用畢竟有限,對前途的憂慮如同陰云遮住了同學們的心。在我回村時,每日音樂會已經不搞了。
在這一時期,幾位同村插隊的同學還組織了一個文學小組,并且活動了多次。在我回村后,文學小組又活動了一次,這次活動是討論《山村的早晨》。我在發言中,第一次公開陳述了寫作《山村的早晨》的基本想法。雖然聽者寥寥,我那時的心境卻是極為動情的。若干年后,當我回憶我所參加的這唯一的一次文學小組活動時,所惋惜的是我當時能夠奉獻給文學小組的,只有《山村的早晨》這樣一部很不像樣的作品。這次討論,不幸竟成了文學小組的最后一次活動。后來,我們雖然以“常青文”為筆名進行了一個時期的寫作與投稿活動,但那時真正的“常青文”——長勝村知青文學小組,卻已經名存實亡了。
這時候,“扎根農村一輩子”的意念已不再被奉為金科玉律,變得像泡沫一樣,悄然地消散了。其實,它原本就是虛幻的泡沫。知青同學們各自“找出路”的努力,也已經不再是秘密。
盡管有對于前途的深深憂慮,許多同學在各自尋找著出路,但從表面上看,知青集體仍然是興旺的。大家正在籌備即將到來的“八一”聯歡會。
丹妮每晚練習唱蘇聯歌曲“烏克蘭”,張軍拉小提琴為她伴奏。張軍拉小提琴已有一段時間,頗有幾分功底。對于丹妮,我原來只知道她的文筆不凡,卻不知她的歌也唱得這樣好。
最后的高潮場面,是“八一”聯歡。那一天,同在一個縣的漫水、李家溝等村子的許多插隊同學都來了,其中有漫水的魏光奇、李家溝的盧叔寧,等等。
聯歡晚會是在祠堂正房里開的。
魏光奇唱了一曲“怒發沖冠,憑欄處……”。
丁東在屋子中間,手朝下一揮,吟出了“……環球動向依我旋”!
惠文跳了“紅色娘子軍”。
我朗誦了一首臨時拼湊的詩,很糟糕。那時還根本不會寫詩。
“烏克蘭”也唱得不好。可能是丹妮那天中午聽說要把她調到縣農林辦公室去的緣故吧。
那天白天,外面下著小雨。各村知青坐在屋檐下的石凳上高談闊論,也廣泛地談到了農村問題。有人甚至談起“體制改革”。須知,這是1971年啊。這位同學真可謂先知先覺。
聯歡會后,第二天早晨,漫水等村的同學回去了。張軍背上他的小提琴,也走了。丁東和盧叔寧一起走了,開始了“南國之行”。這是他們的旅行計劃,他們想去南京看長江大橋,結果歷盡艱辛,只到了商丘(在1994年出版的《老插話當年》一書中,盧叔寧對他們的這次“南國之行”作了詳細的記述)。丹妮去了縣農林辦公室。在這之前,繆力已去了縣廣播站。
1971年的“八一”聯歡,成了長勝村知青的最后一次盛會。同學們各奔東西,已經是大勢所趨。
而這時的我,因《山村的早晨》尚未最后完稿,一心投入到了寫作中。
隆冬漳水寒
1971年9月,我帶著尚未寫完的《山村的早晨》文稿,到白家溝參加挖漳河的工程。后來又到了段柳村,一直干到11月底。這時,天已轉冷。初冬的漳河寒風颼颼,河水冰涼刺骨。我們穿著高靿水靴,站在河里挖著河泥。然而,水深已經沒過膝蓋,冰涼的河水灌進了靴子。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我的兩腳都生了瘡。
在白家溝,《山村的早晨》寫到了最后幾章。小說最后的高潮,是在與隆冬漳河的寒風冰水進行苦戰的同時寫下的。那時,一天三出工,根本沒有空閑。我每天只能在睡覺前寫一會兒,起床前再寫幾行。經過幾十天奮斗,終于寫完了《山村的早晨》最后一章。收尾有些草率,但已竭盡我之全力。
寫完《山村的早晨》,總算完了一件大事,身上輕松了不少。有一天,我借口腳上生瘡,請假去縣城。其實,我是去郵局把《山村的早晨》寄給出版社。
天上飄落著星星點點的雪花。從白家溝到縣城往返20公里,我甩開兩條長腿,一路步行。身上穿的是下鄉那年享受知青優待購買的黑布短棉大衣,這時已破舊不堪。因為心情舒暢,腳上的傷痛已不覺得。雪花落下來,落在我頭上,化成了水。我覺得心里很熱很熱,觸到冰涼的雪花,痛快極了。
我那時19歲,衣著寒酸,但又躊躇滿志。
《道路》劇本:希望再度化為泡影
寫完《山村的早晨》第二稿后不久,挖漳河的工程也結束了,我于1971年年底回到北京。大概是寫《山村的早晨》耗費了太大的精力吧,我感覺到疲憊不堪,心力交瘁,很想靜靜地休息一下。
然而,命運并沒有給我留下喘息的時間。
1972年1月下旬,我和丁東一起回到長勝村。聽說大學招生又要開始了。
回到了祠堂,我們簡直不認識我們的“家”了。院子里滿目荒涼,雜草叢生。去年“八一”聯歡時,我們在屋檐下高談闊論坐過的石凳,已經倒塌。看著這景象,我們心里很難過。
這次大學招生和上次一樣毫無希望,連報名都沒有報上。
過了一個多月,在3月初,丁東被調到了省委機關的一個部門工作。分手之際,他送給我一首詩,寫在一枚書簽的背面,作為留念。
丁東走后,其他同學還沒有回來,祠堂里就只有我一個人了。我獨自一人徘徊在祠堂院子里,面對荒涼而空曠的祠堂大院,心里涌起難以排解的惆悵。一種情緒在我心中涌動,大約是我又想寫點什么了。
此后不久,我到縣廣播站,見到曾在同村插隊的繆力,為她寫了一首敘事長詩《繆力的故事》。這是我寫的第一首詩。這首詩寫完之后,我有些驚訝地發現,原來寫詩并不難,而我也是能夠寫詩的。當時,丁東是我們長勝知青中的詩人。我長期和丁東等喜歡文學的同學在一起,也受了不少感染和影響吧。
這一年的早春,我與縣文化館建立了聯系,開始為他們寫劇本。我怎么突然又寫起劇本來了呢?原因很簡單,縣文化館正需要劇本。大約在3月下旬,我帶著用小說《開會姑娘》改編的劇本《道路》,住進了縣文化館。
《開會姑娘》是我在這一年1月寫的一部短篇小說,寫的是一位插隊女知青的故事,她是知青中的“先進典型”,經常不斷地參加各種報告會,久而久之,竟成了眾人議論中的“開會姑娘”。后來,她在現實的教訓和同學、老鄉的幫助下,幡然醒悟。這篇小說對當時下鄉知青中的虛浮風氣有一定的針砭意味,一些情節還頗為感人。小說寫好后,拿給丁東等同學看,受到了他們的一致稱贊。
我在縣文化館住了8天。8天時間里,總共將《道路》劇本修改了4稿。對我來說,寫劇本比寫小說、寫詩難得多,因為我連一丁點舞臺經驗都沒有。幸而有文化館負責人老楊的指點,每次修改都有較大進步,到最后一稿,一部還算像樣的四場歌劇劇本居然出爐了。我為自己的第一部劇本而感到沾沾自喜。
寫完《道路》,從縣文化館回到村里,春耕大忙已經過去了。這時,部隊某兵工廠到縣里來招收知青,這是首次大規模給知青安置工作。招工的軍人還想為某部隊文工團招一些有文藝專長的人。我聽說后,趕快前往面談。共談了4次,還送上了剛寫好的《道路》劇本。對方是滿意的。
有一天,我和另一個村子的知青白錫喜一起找解放軍招工人員談過之后,天已晚了,我們在縣文化館過夜。白錫喜也很喜歡寫詩,當時已發表了一些詩作。(白錫喜的哥哥白錫雙、妹妹白愛菊也是插隊知青。1994年,《老插話當年》出版,時任大眾文藝出版社編輯的白愛菊為該書責編。)
大約是想到就要成為部隊文藝工作者了,我和白錫喜都激動不已,難以入睡。夜很靜,滿天星光從窗子透了進來。我們大概都不會忘記這個夜晚吧。那時,我已經在一心向往著“部隊文藝工作者”的生活了,并且慶幸這《道路》劇本寫得如此及時。可惜,好景不長。到了最后,因為縣里沒有安排我們村的招工名額,只好作罷。一段時間的夢想又成泡影。
招工的事過去后,我就自己安慰自己,雖然沒能進文工團,可畢竟《道路》劇本還在。想到《道路》不久將在舞臺上展露風姿,我又高興起來。然而,這次也沒有高興多久。《道路》被上級主管部門判了“死刑”,理由是劇中的主人公是個“中間人物”。這個評價倒是一點兒也不錯,按當時的標準,那人物的確是一個“中間人物”。現在回想起來,上級主管部門給《道路》判“死刑”,其實也是為我好。如果《道路》真的上演了,很可能會遭到嚴厲批判,我身為作者,能夠逃脫“罪責”嗎?
有一天,我又去縣文化館,看到垃圾堆里有厚厚一疊廢紙,還散發著油墨香味,那便是已印好的我的《道路》。
5月底,我又一次心灰意懶地回了北京。這次,在北京整整住了4個月。這4個月卻成了我文學創作的“繁榮時期”,寫了獨幕話劇《新年》、短篇小說《隊長》、中篇小說《海燕》,還有長詩《中國與世界》。最后,我在難以克制的情感的驅使下,寫下了敘事長詩《沒有寫完的詩篇——關于格爾丹的傳說》。這詩的名字挺長,我更喜歡簡稱為《格爾丹》。
1972 年,那個寒冷的冬天
寫完《格爾丹》后不久,大約在9月底,我離開北京,到長治參加地區創作會,緊接著又去太原參加省創作會,帶去的是署名“常青文”的一篇小說。在太原期間,聽到了長治東風鋼鐵廠和長治鐵路局要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起先,我曾想去鋼鐵廠,但經過反復考慮,我又想去鐵路局了。我很想回到縣里爭取這次招工的機會,但是當時在開創作會,脫不開身。如果我身上有夠打一次長途電話的錢,給縣里打一個長途電話,那我就很可能去到鐵路局當養路工了。然而,我那時一文不名。在怔忡不寧的心緒中,開完了創作會。我又聽到消息,說我們準備去晉城紡織廠了。
我這次參加創作會,似乎是離“作家夢”近了一步,本該是高興的。然而,在會議期間,我一直被關于前途出路的重重思慮所困擾著。既然是這樣,真的沒必要細說這次創作會了。
就在這樣令人焦慮不安的氛圍中,1972年的冬天到來了。
我記得,那個冬天非常寒冷。“屋子里沒有生火,水缸里漂著冰塊……”我曾在一封信里這樣寫道。這個冬天之所以如此寒冷,并不完全是因為氣候,還因為那個消息:凍結。
“凍結”前夕,恰值丁東回縣里辦理調動手續。那天上午,我們一同去李家溝找盧叔寧。一路上,我們心情都很好,談笑風生。丁東這時在省里某部門工作,已通曉農村政策,他指著路邊山坡上那一塊塊零星的梯田,揶揄地說:“看吧,這就是要割掉的資本主義尾巴!”我們都會心地笑了。
沒有找到盧叔寧。下午,我們回到縣城。這時,傳來了可怕的消息:凍結。知青分配工作全部凍結。
誰也沒有想到形勢會突然急轉直下。已經被前一段各種波折搞得精疲力竭的我,此刻的心情是近于絕望的。
我的《格爾丹》:我魂牽夢縈的詩篇
也許,我在1972年中唯一值得珍重的收獲,就是寫下了《格爾丹》這首256行的敘事長詩。《格爾丹》敘述了一個傳說中的英雄的故事,寫了格爾丹從建立功業到消沉沒落的全過程。格爾丹最初的青春力量和宏大志向與他最后的衰敗沉淪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結局具有強烈的悲劇色彩。在當時的條件下,寫這樣一首詩是需要勇氣的。
這首詩寫完之后,每次重讀,我都感到驚訝,不知是怎樣的靈感的撞擊,使我創造了格爾丹的形象,并將那段坎坷人生道路上的甘苦悲歡都溶入了格爾丹的形象之中。在以后的歲月里,我曾走南闖北,多少東西都丟掉了。這篇《格爾丹》詩稿,我卻一直珍藏著它,保護著它,唯恐失落了它。因為我認為,倘若失落了它,便是失落了自我。過了好幾年以后,我仍然在潛意識中認為,格爾丹就是我,我就是格爾丹。所不同的是,我不甘心像格爾丹那樣沉淪。
為了擺脫格爾丹那樣的厄運,在以后的艱難困苦中,我一直在與命運頑強抗爭著。今天,那段坎坷的歷程已成為過去。然而,《格爾丹》仍是我最珍愛的作品,是我清貧的人生中一份無價的精神財富。
1973 年招生考試:仍然是一枕黃粱
1973年,我在北京一直住到5月份。這期間,我又將《山村的早晨》修改了一遍,寫出了《山村的早晨》第三稿。此外,我還把插隊生活中一些感觸深刻的經歷記了下來,共寫了40多頁,覆以白色封面,后來稱之為“白皮回憶錄”。尚未離開農村就開始寫插隊回憶錄,說明我那時已預感到插隊生活就要結束了。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我們這一群青年人在農村的坎坷生活歷程,總有一天要向世人展示的。
5月份,聽說大學招生又將開始,我便動身返回長勝村。
回村后,我和插隊同學國楠輪流在瓦窯干了十幾天。深夜,在高高的窯頂上攪水,倚著井架仰望夏夜的星空,這便是我在農村勞動生活的最后一幕。
這一年的大學招生方法有了改變,要進行開卷考試。雖然開卷,畢竟是考試!經過數年來為上大學而進行的毫無結果的努力之后,一線希望的曙光終于出現了。人們終于可以在比較公平的條件下進行競爭了。
某日,我領到了準考證(當時叫“入場證”)。薄薄的紙上貼著我的照片,蓋著縣“革委會”文教辦公室鮮紅的印章。捧著準考證,像捧著稀世珍寶,捧著光明,捧著希望。
考場設在縣城。考試那一天,我見到了來自全縣各村的許多知青,大家在考試之前聚在一起,互相鼓勵,爭取好的成績。
考試順利結束了。我對自己在考場上的發揮是滿意的。據說,一位參加閱卷的語文老師事后曾到處打聽誰是王國全。他說,那作文寫得實在好。我很想告訴這位老師,我是把一腔熱血都噴灑到了考卷上啊!
填報志愿了,我報了吉林大學物理專業。雖然曾經在文學的海洋里遨游,我卻并沒有學習文科的意愿。我相信我的生命應該屬于另一個領域——科技的領域。神奇莫測的科技領域,對我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在這期間,我寫下了長詩《大江三部曲》,詩中寫道:
天發怒了,
閃電射出千道金光,
暴風雨
席卷了小小的池塘。
我——
大海的兒子
在暴風雨中放聲歌唱……
風急了,
雨烈了,
水也驟然急漲。
在這風吼雷鳴中,
我昂然地奔向海洋!
我覺得我們這群知青如同大江里洶涌的浪濤,就要奔向海洋了!
在考試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就這樣懷著焦急的心情,等待著命運之神的微笑。然而,我們這一代人真是命運多舛。災難,深重的災難,再一次無情地降臨了。
這一天,報紙上刊登了關于張鐵生交白卷的報道。曾如曇花一現的夢想再度被撕碎,平等競爭的權利再度被剝奪,我們再度被拋入命運的深淵。
剛剛進行的考試無須宣布就自行失效,一切又都故伎重演。我們又得去奔波、乞求。有誰能告訴我,希望在哪里?出路在那里?
插隊生活的最后時日
插隊生活最后的、最痛苦的一段日子開始了。我們的心情,如同犯人等待判決一樣。當時村里只剩下我和國楠、雨銘、時民等幾個知青了。
誰也沒有心思下地干活了,我們打撲克消磨時光。連打撲克的心思也沒有的時候,我們就想喝酒。
有一天,國楠捉了一只鱉,他把鱉燒好,又拿出從北京帶來的白酒,邀我一起喝。那只鱉味道極其鮮美。
我們喝二鍋頭,喝果酒。不幸的是,我們那時經濟上十分困窘。插隊五年,我總共只從生產隊分紅40元錢。生活費用主要是靠家里接濟的。我們不愿意清醒,清醒了我們將面對嚴酷的現實;然而,我們也不能沉醉,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錢!
又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問時民:“能炒一鍋菜嗎?”
時民透出一絲微笑:“有酒嗎?”
我拿出了最后一瓶紅葡萄酒。不一會兒,時民燒好了一大鍋土豆和胡蘿卜,那氣息、那色澤都很誘人。我們吃光了菜,喝干了酒。當最后一滴紅色的液體從瓶口上消失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感覺到滿足。小小一瓶酒,如何能填滿我們心靈上深深的溝壑呢?
這時,天已薄暮。我提著空酒瓶,步履略有些蹣跚地走向村后空曠寂寥的山野。我高高地舉起酒瓶,朝著一塊大石頭重重地砸下去。“砰”的一聲巨響。然而,我卻沒有得到期望的刺激。我的心已經麻木了。
終于有一天,我接到了山西省一所中專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談不上高興,“高興”這個詞已經被我們遺忘得太久了。想上大學卻上了中專,也并不盡如人意。但當時知青中有一句響亮的口號:“倒盤盤”。只要離開農村就算是倒了盤盤。中專雖然比不上大學,畢竟是倒了盤盤。應該知足了。
離開村子的前一天,我去向房東小伙子告別,也告別了我曾經獨自居住的小屋。
那幾天,一直下著小雨。秋意正濃。臨行的前一天晚上,雨還是不停,而且更大了。
天還沒亮,幾位同學都起來了。我們收拾東西,準備出發。幸好,雨在這時候停了。
出村的路是黑漆漆的,泥濘的。雨銘扛著我的大行李卷,另一位同學幫我抬著大箱子,艱難地向村口走去。時民在深深的泥漿中吃力地拖著一輛平車。
我們上了公路,天色剛剛微明。這一天是1973年10月23日。天氣雨后微寒,寒氣中夾著幾絲離別的傷感。大家沉默不語。
到了縣城長途汽車站,灰蒙蒙的天空中又飄著星星點點的雨霧。插隊同學盧叔寧、丁振剛等也來送行了。
我從長途汽車的窗口向同學們揮手告別。
車開動了。縣城的景物轉眼間就消失了,我忽然意識到5年的插隊生活已經結束了!千思萬緒突然涌上心頭。插隊生活中的許多場景不分先后次序地在我眼前閃動。我忽然想到,要重寫《山村的早晨》,要把《山村的早晨》再修改一遍!接著,《山村的早晨》也如同一條航船,消失在思緒起伏的大海之中。
到了太原,下了長途汽車后,我來到一家小飯館,掏出最后一點錢,買了二兩白酒。然后,憑著醉意中麻木的感覺,蹣跚在大街上。
插隊之后的經歷
在這里,我還想把插隊之后的經歷作一簡要記述。
我在1973年10月離開插隊的村子后,到山西運城上了兩年中專。在上中專期間,寫作《山村的早晨》依然是我難以割舍的夙愿。我被自己的意愿所驅使,將《山村的早晨》又大幅度修改,幾乎是重寫了一遍。這就是《山村的早晨》的第4稿。前后4稿,累計總共寫了大約60萬字。這些文稿是在很艱難的條件下寫出的,為了免于遭受非議,常常還要避開周圍人們的視線進行寫作,其艱辛就更可想而知了。
1975年,我中專畢業,分配到水利測量隊工作,在昔陽縣做過大約一年的測繪,此期間寫過一些詩,如《風雨歌》。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我和幾位同事一起被派到忻州地區的申村搞“運動”,在此期間也寫過一些詩,如《織天網》。
1977年上半年,一家出版社組織討論會,對四五部長篇小說書稿進行討論,我的《山村的早晨》是其中之一。這次參加討論會,是我對《山村的早晨》投下的最后希望。然而,依然是無果而終。會議結束那天,參會人員的聚餐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在我的人生中,這是第一次醉到如此地步,也是最后一次。我在自己心底里,永遠地埋葬了我的《早晨》。現在回想起來,《早晨》是屬于那段已經過去的時代,就讓它靜靜地安息吧。
后來,我參加了1977年底恢復的高考。1978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自插隊初期開始,含辛茹苦奮斗了9年多,終于如愿以償實現了上大學的夢想。在大學畢業以后的20余年間,我一心埋頭于專業,在自己研究的領域里取得了應有的收獲。
我在插隊期間,以及插隊后留在山西期間,共寫了20余首詩。1988年,在插隊20周年的時候,我選出了其中的6首,與自己寫的插隊回憶錄等文稿匯集在一起,油印成了《王國全自選詩文集》。
1998年是上山下鄉30周年,《中國知青詩抄》出版,我的《自選詩文集》中的兩首詩《大江三部曲》和《長空的閃電》被收入。
2008年是上山下鄉40周年,為紀念上山下鄉40周年,我撰寫了《當我們50歲之后》一書,與知青朋友們一起回憶過去,一起思考現實,一起展望未來。
2008年12月19日,北京知青網舉辦“紀念上山下鄉40周年聯誼會”,我在會上向知青朋友們贈送了《當我們50歲之后》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