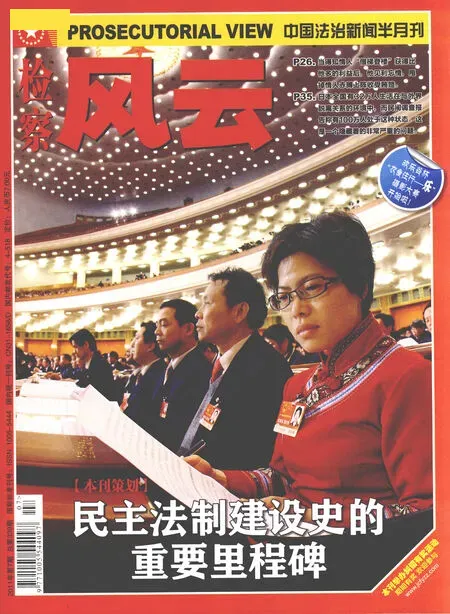科學(xué)打拐
文/阿 碧
科學(xué)打拐
文/阿 碧

(圖/CFP)
前一階段,微博打拐行動(dòng)正在網(wǎng)絡(luò)上轟轟烈烈地進(jìn)行著,成為近期最重要的網(wǎng)絡(luò)事件之一。打拐活動(dòng)還從網(wǎng)絡(luò)走向現(xiàn)實(shí)生活,成為人們普遍關(guān)注的公共事件,也成了人們近期重要的一項(xiàng)公益活動(dòng),全民打拐由此開(kāi)始。2月12日,李承鵬、張洪峰等著名的網(wǎng)絡(luò)活動(dòng)人士從湖南、福建、甘肅等地齊聚北京,就微博打拐、解救乞討兒童活動(dòng)進(jìn)行商議。著名社會(huì)學(xué)家于建嶸、徐小平等人和相關(guān)組織,在壹基金發(fā)起成立“壹基金救助乞討兒童專(zhuān)項(xiàng)基金”,使救助乞討兒童的行動(dòng)常態(tài)化、法制化、公益化。專(zhuān)項(xiàng)基金公開(kāi)透明,接受政府、社會(huì)、公眾監(jiān)督。還有不少新技術(shù)也應(yīng)用到打拐中來(lái),比如中國(guó)科學(xué)院自動(dòng)化研究所為微博打拐提供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不少地區(qū)的司法機(jī)構(gòu)開(kāi)始利用DNA技術(shù)打拐。
微博打拐
前不久,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農(nóng)村發(fā)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在新浪網(wǎng)設(shè)立“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微博,吸引近百萬(wàn)名網(wǎng)民圍觀。在網(wǎng)民的幫助下,公安機(jī)關(guān)通過(guò)網(wǎng)上照片辨認(rèn),順利解救被拐賣(mài)兒童6名。一直以來(lái),“打拐”都是政府行為,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應(yīng)用,公民“打拐”成為了現(xiàn)實(shí),這讓我們?cè)俅晤I(lǐng)略到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巨大影響力和滲透力。微博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使網(wǎng)民的力量得以匯聚并被放大。“微博打拐”這一網(wǎng)民行動(dòng),正是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媒體疊加網(wǎng)民“微力量”,擴(kuò)展了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道德力量。
相關(guān)鏈接:微博的力量
自從第一家微博網(wǎng)站Twitter于2006年6月13日成立后,微博開(kāi)始席卷整個(gè)互聯(lián)網(wǎng)。三言兩語(yǔ)、現(xiàn)場(chǎng)記錄、發(fā)發(fā)感慨……微博網(wǎng)站打通了移動(dòng)通信網(wǎng)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界限。除了可以通過(guò)電腦上網(wǎng)發(fā)布信息,在無(wú)法上網(wǎng)的地方,只要有手機(jī)也可以即時(shí)更新微博的內(nèi)容。



事實(shí)上,在一些突發(fā)事件或重大事件現(xiàn)場(chǎng),很多第一手的信息都是網(wǎng)民通過(guò)手機(jī)發(fā)布在微博上,其實(shí)時(shí)性、現(xiàn)場(chǎng)感以及快捷性甚至超過(guò)傳統(tǒng)媒體。2010年8月7日,在泥石流沖擊舟曲縣城的時(shí)候,回鄉(xiāng)過(guò)暑假的大學(xué)生網(wǎng)民王凱通過(guò)手機(jī)發(fā)布了最早的災(zāi)害信息,讓公眾在第一時(shí)間知道了舟曲的災(zāi)情,被網(wǎng)民稱為“報(bào)道災(zāi)情第一人”。接下來(lái)的9天里,他背著一臺(tái)便攜式相機(jī),手里拿著一部老式手機(jī),在災(zāi)區(qū)一處處即將坍塌的廢墟,向外界傳遞災(zāi)情和救災(zāi)情況。
相對(duì)于傳統(tǒng)博客的長(zhǎng)篇大論,微博的字?jǐn)?shù)限制恰好決定了它的內(nèi)容只需由簡(jiǎn)單的只言片語(yǔ)組成即可,大大降低了文字功底的要求和進(jìn)入的門(mén)檻,節(jié)約了時(shí)間成本,符合現(xiàn)代社會(huì)快節(jié)奏的生活方式。隨著微博的升溫,微博已經(jīng)成為了信息整合最及時(shí)、傳播速度最快的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相對(duì)于博客來(lái)說(shuō),用戶的關(guān)注屬于一種“被動(dòng)”的關(guān)注狀態(tài),寫(xiě)出來(lái)的內(nèi)容其傳播受眾并不確定;而微博的關(guān)注則更為主動(dòng),只要輕點(diǎn)“關(guān)注”,即表示你愿意接受某位用戶的即時(shí)更新信息。在微博網(wǎng)站上,即使一個(gè)普通的用戶也可能擁有數(shù)量眾多的“粉絲”,可以向他們發(fā)布信息。而微博的轉(zhuǎn)發(fā)功能就像是一個(gè)信息放大器,信息在不斷的轉(zhuǎn)發(fā)中,影響力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不少司法機(jī)構(gòu)也看中了微博的信息快速傳遞功能,紛紛在網(wǎng)絡(luò)上開(kāi)設(shè)微博,向人們解釋一些特殊案件的疑點(diǎn),或是征集懸案的偵破線索。2010年11月23日晚,一條“懸賞尋尸全城通緝”的消息首次出現(xiàn)在“廈門(mén)警方在線”的微博里。消息稱:“11月14日,隨著退潮,一具女童的尸體被沖上高崎附近海灘,最后‘陪伴’她的只有一身破舊的衣褲和一個(gè)編織袋,她身上傷痕累累,生前受盡虐待,死后才被投入大海。警方懸賞5000元征集線索,相信網(wǎng)民的力量,您知道任何線索,請(qǐng)告訴我們!”消息后面,配發(fā)著重要的三條線索:女童的臉部照片以及衣褲和編織袋照片。結(jié)果一星期內(nèi)就有2000多條評(píng)論,1萬(wàn)多次轉(zhuǎn)發(fā)。廈門(mén)警方利用網(wǎng)民提供的100多條有用線索,在一星期內(nèi)偵破了此案。




當(dāng)后人研究微博傳播的歷史時(shí),打拐將是一起值得被銘記的重要事件。微博打拐源于2010年9月27日發(fā)出的一條微博,這條微博在4個(gè)月內(nèi)被轉(zhuǎn)發(fā)了數(shù)萬(wàn)次,數(shù)十萬(wàn)人知曉了這條信息。這條微博開(kāi)頭的第一句話是:“互聯(lián)網(wǎng)能再創(chuàng)奇跡嗎?”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3歲半的兒子彭文樂(lè),令這位父親裂肺撕心。近年來(lái),國(guó)內(nèi)掀起打拐狂潮,已解救了5896名兒童,移交民政部門(mén)736人。但是,小文樂(lè)一直沒(méi)有下落。當(dāng)兔年春節(jié)的爆竹聲響起時(shí),一位回鄉(xiāng)探親的大學(xué)生,發(fā)現(xiàn)村里一個(gè)小男孩像極了那張?jiān)谖⒉┥蟼鞑サ膶と藛⑹拢杆偻ㄟ^(guò)微博傳遞消息。在警方的幫助下,彭高峰終于找到了失蹤幾年的兒子。
彭高峰的痛苦令許多網(wǎng)民感同身受,人們通過(guò)過(guò)往的經(jīng)驗(yàn)發(fā)現(xiàn),一些被拐兒童被乞丐頭子用作乞討賺錢(qián)的工具,而行走在公共場(chǎng)所的乞兒是人們所能看見(jiàn)的,解救被拐兒童可以從那些乞兒入手。于是,一場(chǎng)轟轟烈烈的微博打拐行動(dòng)由此開(kāi)始,一場(chǎng)名為“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自發(fā)活動(dòng)在網(wǎng)絡(luò)上迅速流傳。截至2011年2月底,已有5名兒童通過(guò)微博打拐行動(dòng)被救出。更多失散的孩子,有望重歸親人的懷抱。
微博是可實(shí)時(shí)發(fā)布消息的迷你型博客,一般不超過(guò)140個(gè)字符。與在報(bào)紙、電視和電線桿子上登載尋人啟事相比,微博的確是一種更加有效的打拐新技術(shù)。微博的優(yōu)越性體現(xiàn)在哪里?首先,用戶可以通過(guò)自主地發(fā)布信息,只要是合法的信息就可以發(fā)布。其次,微博發(fā)布信息的渠道也很多,用戶可以通過(guò)電腦登錄網(wǎng)站來(lái)發(fā)布被拐兒童信息,也可以通過(guò)手機(jī)網(wǎng)絡(luò)、即時(shí)通信、短信、電子郵件等等多種方式來(lái)發(fā)布。
更為重要的是,微博的傳播是一種網(wǎng)狀的傳播方式,信息一旦發(fā)布之后,你的所有“粉絲”都可以看到相關(guān)消息,然后他們會(huì)轉(zhuǎn)載,他們的粉絲接著轉(zhuǎn)載,這就像是一場(chǎng)網(wǎng)絡(luò)尋人接力賽。效率高的時(shí)候,在幾小時(shí)內(nèi)全國(guó)各地?cái)?shù)以萬(wàn)計(jì)的網(wǎng)民都可能看到了被拐兒童的信息,他們會(huì)幫助發(fā)帖者在日常生活中留心身邊的兒童,這樣找到失蹤兒童的概率就要比利用傳統(tǒng)方式大得多。
最近的一個(gè)尋人案例,就充分顯示了微博作為求助平臺(tái)的威力。2010年12月24日下午1點(diǎn)多,北京一位10歲的女生何同學(xué)放學(xué)未歸,父母開(kāi)始在大街小巷張貼啟事,其中寫(xiě)道:“10歲,1.38米,平安夜放學(xué)未歸,一直到今天都沒(méi)有消息。爸媽都快急瘋了,圣誕就報(bào)警了,孩子走失時(shí)身上沒(méi)有錢(qián),且小孩不會(huì)上網(wǎng)。這么寒冷的冬夜,孩子到底去了哪兒?拜請(qǐng)達(dá)人傳播”。有熱心網(wǎng)民看見(jiàn)紙質(zhì)版后,將其發(fā)布在微博上,引發(fā)網(wǎng)民轉(zhuǎn)發(fā)5000多次。由于微博上聚集著大量新聞?dòng)浾撸瑐鹘y(tǒng)媒體開(kāi)始對(duì)此跟進(jìn)報(bào)道。終于在9天之后,失蹤學(xué)生被找到。原來(lái),何同學(xué)被西單一名保安收留,好吃好喝的。保安從媒體的報(bào)道獲知電話聯(lián)系了何的家人,何同學(xué)順利回家。
對(duì)于網(wǎng)民的打拐熱情,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通過(guò)微博回應(yīng):“我會(huì)通過(guò)微博和大家保持溝通,歡迎提供拐賣(mài)犯罪線索。對(duì)每一條線索,公安部打拐辦都會(huì)部署核查。”目前,陳士渠每天都會(huì)在微博上關(guān)注最新的消息,并發(fā)布實(shí)時(shí)動(dòng)態(tài)。目前,他已經(jīng)把一些地方乞討兒童的消息和當(dāng)?shù)鼐綔贤ú⒍酱偬幚怼?/p>
面部識(shí)別
微博作為一種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它本身只能起到網(wǎng)狀傳播信息的功能,要確認(rèn)某個(gè)孩子是不是被拐兒童,還需要更加先進(jìn)的身份識(shí)別技術(shù)。日前,百度推出的公益互動(dòng)開(kāi)放平臺(tái)“百度尋人”測(cè)試版正式上線,該平臺(tái)打算建立一個(g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失蹤兒童與流浪兒童的開(kāi)放數(shù)據(jù)庫(kù),并利用中科院計(jì)算技術(shù)研究所提供的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迅速匹配孩子的照片,幫助家長(zhǎng)和熱心網(wǎng)民獲取失散兒童的信息。
面部識(shí)別與指紋識(shí)別、虹膜識(shí)別并稱為三大生物特征識(shí)別技術(shù)。當(dāng)網(wǎng)民拍攝到流浪兒童的視頻圖像后,把它傳遞到網(wǎng)絡(luò)上,面部識(shí)別系統(tǒng)首先會(huì)把視頻中的人臉抓取出來(lái)。隨后,系統(tǒng)把焦點(diǎn)對(duì)準(zhǔn)眉骨到下頜這一倒三角區(qū)域,找出該區(qū)域的4000多個(gè)特征點(diǎn)位,如眼角點(diǎn)位、鼻翼點(diǎn)位,計(jì)算它們之間的距離比值,就可以確定一個(gè)人的身份。正因?yàn)槊娌孔R(shí)別技術(shù)可以識(shí)別身份,在微博打拐行動(dòng)興起后,中國(guó)科學(xué)院計(jì)算機(jī)所的專(zhuān)家想到了將它用于識(shí)別被拐兒童。該所生物識(shí)別與安全技術(shù)研究中心主任李子青表示,利用他們開(kāi)發(fā)的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從百萬(wàn)張照片中比對(duì)出同一張臉,只需要幾秒鐘的時(shí)間,可以大大提高打拐的效率。
最近,李子青等人已經(jīng)將他們研發(fā)的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無(wú)償提供給了百度網(wǎng)站,建立了“百度尋人”測(cè)試版。該網(wǎng)站分為兩個(gè)板塊:一個(gè)是“我的寶寶失蹤了,要找相似的流浪寶寶”;另一個(gè)是“我拍到流浪寶寶,要找相似的失蹤寶寶”。失蹤兒童的家長(zhǎng)、“隨手拍”的網(wǎng)民都可以上傳兒童照片,當(dāng)兩個(gè)照片庫(kù)中出現(xiàn)一對(duì)相似度很高的人臉時(shí),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就能將他們識(shí)別出來(lái)。此后,根據(jù)網(wǎng)民提供的信息,如發(fā)現(xiàn)孩子的時(shí)間、地點(diǎn),以及個(gè)人聯(lián)系資料,家長(zhǎng)就有望找到自己的孩子。
網(wǎng)民如何“隨手拍”才能更有效地尋找失蹤兒童?專(zhuān)家建議網(wǎng)民在拍照時(shí)要掌握一些基本技巧。首先,要盡量拍攝到孩子的正面臉部,照片清晰度最好要高一些。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允許上下15度、左右30度的側(cè)臉,太偏了就很難識(shí)別。同時(shí),對(duì)拍攝的光線有一定要求,不要在光線反差太大的情況下拍照,因?yàn)槟菚?huì)拍成系統(tǒng)很難處理的“陰陽(yáng)臉”。此外,要盡量多拍攝一些疑似被拐兒童的面部照片,因?yàn)閷?duì)孩子的面部識(shí)別難度要大于成年人。利用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識(shí)別一個(gè)成年人,電腦會(huì)從龐大的數(shù)據(jù)庫(kù)中選出5張最相似的照片;要識(shí)別孩子的身份,“最相似照片組合”也許要擴(kuò)大到50張,這些孩子可能就是50個(gè)相似者中的一個(gè)。對(duì)同一個(gè)兒童多拍攝一些照片,就可以減少相似者的數(shù)量,縮小尋找的范圍。
一些專(zhuān)家建議,警方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和網(wǎng)民的力量合作打拐。由于目前警力有限,而打拐需要的人力又很大,警察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nèi)還可以和網(wǎng)民互動(dòng),利用網(wǎng)民的力量打拐。比如,警察可以調(diào)出在機(jī)場(chǎng)、網(wǎng)吧、銀行、火車(chē)站、碼頭、地鐵等公共場(chǎng)所的監(jiān)控錄像,截選出其中涉及流浪兒或乞討兒的視頻部分,公布到微博上,讓網(wǎng)民利用面部識(shí)別網(wǎng)站協(xié)助調(diào)查。
相關(guān)鏈接:為被拐兒童定位
日本一些研究人員開(kāi)發(fā)了一些定位孩子的技術(shù),幫助家長(zhǎng)降低孩子被拐的概率。
日本著名書(shū)包制造商KYOWA研發(fā)了一種帶有GPS全球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的書(shū)包,售價(jià)大概是330美元。孩子背著這種書(shū)包去上學(xué),父母可以通過(guò)定位系統(tǒng)知道孩子的行走路線和停留位置。即使犯罪分子扔掉了孩子的書(shū)包,父母也可以知道孩子被拐的位置,可為警方破案提供線索。
日本安全公司西科姆集團(tuán)研發(fā)出一種保護(hù)兒童安全的服務(wù)系統(tǒng),名為“COCO-SECOM”。家長(zhǎng)只要支付60美元的申辦費(fèi),并在其后每月支付7美元的月費(fèi),他們就能獲得該系統(tǒng)的服務(wù)。該系統(tǒng)會(huì)在孩子們的書(shū)包上安裝一種特殊定位裝置。如果孩子遲歸家了,家長(zhǎng)還能夠致電控制中心。該中心能夠在半分鐘左右便報(bào)出孩子的具體位置。如果家長(zhǎng)額外多支付82美元的話,控制中心還能夠從全國(guó)2100名緊急服務(wù)人員中馬上調(diào)派人手前往孩子所在地方,把孩子安全帶回家。
日本一些手機(jī)廠商為家長(zhǎng)們?cè)O(shè)計(jì)了可以定位的兒童安全手機(jī),其中安裝有GPS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當(dāng)異常情況發(fā)生時(shí),該定位系統(tǒng)會(huì)將孩子的確切位置傳送到父母的手機(jī)中去。生產(chǎn)商開(kāi)發(fā)出色彩鮮艷和外形漂亮的手機(jī),以吸引孩子們隨時(shí)把它們帶在身邊。這些手機(jī)還可以拍照和報(bào)警。當(dāng)孩子們遇到罪犯的攻擊時(shí),他們可以按下該款手機(jī)上的報(bào)警按鍵。兒童安全手機(jī)不但會(huì)把報(bào)警信息傳輸給警察局,還會(huì)發(fā)出震耳欲聾的警報(bào)聲。當(dāng)兒童安全手機(jī)被違法犯罪分子強(qiáng)行關(guān)機(jī)時(shí),手機(jī)上的攝像系統(tǒng)將悄悄地自行啟動(dòng),拍下當(dāng)時(shí)發(fā)生的一切。
DNA識(shí)別
利用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尋找失蹤兒童有一個(gè)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兒童的面部變化比較快。孩子在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身體發(fā)育很快,面部特征變化也很快,雖不是一天一個(gè)樣,一個(gè)月一個(gè)樣不算稀奇。面部識(shí)別技術(shù)對(duì)于尋找短期內(nèi)失蹤的兒童成功率較高;對(duì)于失蹤幾年的兒童,則難度較大。要更加準(zhǔn)確地識(shí)別流浪兒是不是某位家長(zhǎng)失蹤的孩子,就不能再利用全民參與這種方式,需要技術(shù)含量更高且更加準(zhǔn)確的DNA識(shí)別技術(shù)。不過(guò),人們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或者其他途徑提供有用線索還是很有必要的。
每個(gè)人DNA同一位置上的一對(duì)基因稱為等位基因,一般一個(gè)來(lái)自父親,一個(gè)來(lái)自母親。對(duì)比圖譜數(shù)據(jù),雙方有沒(méi)有血緣關(guān)系一目了然。若是DNA鑒定乞討兒與隨行的成人有親子關(guān)系,則可以排除兒童被拐的可能性;如果沒(méi)有親子關(guān)系,乞討兒就列入被拐兒童的嫌疑數(shù)據(jù)中。對(duì)于一些不能提供隨行成人姓名的流浪兒,則也可以照此辦理。全國(guó)失蹤孩子的父母可以到當(dāng)?shù)毓矙C(jī)關(guān)提供DNA檢測(cè)數(shù)據(jù),輸入到公安系統(tǒng)的數(shù)據(jù)庫(kù)中。如果某個(gè)嫌疑被拐兒童的DNA數(shù)據(jù)和某個(gè)流浪兒或乞兒的數(shù)據(jù)比對(duì)成功,則可以成功解救出被拐兒童。
目前,國(guó)內(nèi)不少省市的公安部門(mén)都展開(kāi)了DNA打拐的工作。比如,石家莊市公安局打拐辦和石家莊市救助管理站,對(duì)成人帶著兒童行乞的人員進(jìn)行驗(yàn)血辨親。通過(guò)DNA鑒定比對(duì),確定血緣關(guān)系的勸其返鄉(xiāng),沒(méi)有血緣關(guān)系將被重點(diǎn)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被拐兒童將全力解救。江蘇省公安廳打拐辦對(duì)丟失孩子報(bào)案的家長(zhǎng)都采集血樣,建立“打拐DNA數(shù)據(jù)庫(kù)”,同時(shí)對(duì)網(wǎng)民微博提供的、來(lái)歷不明的流浪乞討未成年人一律采集DNA樣本,錄入“打拐DNA數(shù)據(jù)庫(kù)”,除了鑒別是否涉嫌拐賣(mài),還用于將來(lái)找到親人時(shí)做親子鑒定。海口市警方對(duì)來(lái)歷不明的流浪乞討未成年人一律采集DNA樣本和指紋,拍下相片,經(jīng)檢驗(yàn)后將數(shù)據(jù)錄入“打拐DNA數(shù)據(jù)庫(kù)”和指紋庫(kù)。公安部打拐辦已建立了“全國(guó)打拐DNA數(shù)據(jù)庫(kù)”,便于各地辦案民警更快速地識(shí)別和解救被拐兒童。
還有一種DNA新技術(shù)正在測(cè)試中,這種技術(shù)可以查找到被拐兒童姓氏、族群圖譜。不單是被拐兒童的親生父母,連兄弟姐妹、祖輩、民族,甚至是姓氏,將來(lái)都有可能通過(guò)DNA來(lái)推斷。如果這種技術(shù)能夠研制成功,解救被拐兒童的行動(dòng)將更加有效。■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