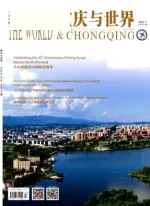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法治建設(shè)——馬克斯·韋伯理論的啟示
梁文生,丘國(guó)漢
(1.電子科技大學(xué)中山學(xué)院,廣東中山 528400;2.江門市新會(huì)區(qū)人民法院,廣東江門 529000)
社會(huì)轉(zhuǎn)型乃指社會(huì)的運(yùn)作從一個(gè)主流模式向另一個(gè)模式轉(zhuǎn)變。無論是緩慢的改良,還是劇烈的革命,社會(huì)轉(zhuǎn)型均牽動(dòng)諸多社會(huì)因素的變化。在有關(guān)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社會(huì)理論當(dāng)中,德國(guó)學(xué)者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是頗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1],它對(duì)我國(guó)目前法制建設(shè)頗有借鑒意義。
一、馬克斯·韋伯理論與中國(guó)的社會(huì)發(fā)展
馬克斯·韋伯首先以“合法性”(legitimacy)來劃分社會(huì)模式。合法性通常指一個(gè)政權(quán)有權(quán)作出指示和提出要求,而被民眾所普遍接受的狀態(tài)[2]。在馬克斯·韋伯看來,合法性被指為國(guó)家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auth·rity),或政治秩序[3]。即表明某一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具有被承認(rèn)、被認(rèn)可、被接受的基礎(chǔ)[2]。
在考察東西方古今社會(huì)異同的基礎(chǔ)上,依合法性或統(tǒng)治權(quán)威的標(biāo)準(zhǔn),馬克斯·韋伯提出了3種合法性政權(quán)的理想類型。一是法治型(Legal-rati·nal auth·rity),二是傳統(tǒng)型(Traditi·nal auth·rity),三是卡里斯瑪型(Charismatic auth·rity)。第1種類型,法治型政權(quán)奠基于人們普遍對(duì)被制定法律的信念,統(tǒng)治者權(quán)威的根據(jù)就是法律,而這種法律的頒布必須符合一定的程序。韋伯認(rèn)為這種型態(tài)的政權(quán)的最后根據(jù)是理性。第2種類型,傳統(tǒng)型政權(quán)則奠基于對(duì)于一直存在著的東西具有神圣性這個(gè)信念上,這個(gè)神圣性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情感、習(xí)俗和慣例等權(quán)威之中。第3種類型,卡里斯瑪型政權(quán),或稱魅力型政權(quán),則來源于人們認(rèn)為某些領(lǐng)袖具有非凡的品質(zhì),如神所賜予一般,具有超凡的魅力,因此認(rèn)為他應(yīng)該擁有統(tǒng)治權(quán)[4]。
雖然上述3種社會(huì)模式是馬克斯·韋伯提出的理想模型,并且我們無意將其生搬硬套到中國(guó)的情形來,但是,運(yùn)用馬克斯·韋伯的3種社會(huì)模式,仍然能夠充分分析中國(guó)近百年的歷史發(fā)展階段。
一個(gè)世紀(jì)以來,如西方社會(huì)的發(fā)展一樣,雖然時(shí)間先后不同,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歷過3個(gè)階段的變遷:第1階段是傳統(tǒng)社會(huì),此階段自中國(guó)的王朝形成以來,保持長(zhǎng)期的穩(wěn)定性,直至清末,在西方列強(qiáng)的侵襲下土崩瓦解。這個(gè)傳統(tǒng)社會(huì)的長(zhǎng)期性有賴于傳統(tǒng)型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第2階段是革命時(shí)代,此階段只是過渡環(huán)節(jié),其目的是邁向第3階段。中華民國(guó)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可視為革命時(shí)代的時(shí)段。其中,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為界線,前者為革命時(shí)代前期,后者是革命時(shí)代后期。在革命階段,卡里斯瑪型政權(quán)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第3階段是步入現(xiàn)代社會(huì),這個(gè)階段尚未完全確立,仍然處在繼續(xù)變化的狀態(tài)。從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直至現(xiàn)在,中國(guó)社會(huì)尚處于邁向現(xiàn)代化的初級(jí)階段,其未來走向如何,只能在求索中前進(jìn)。如何能夠轉(zhuǎn)型成為現(xiàn)代化社會(huì),則法治型政權(quán)將成為主流選擇。
二、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法治建設(shè)的關(guān)系
后革命時(shí)代社會(huì)轉(zhuǎn)變何去何從?馬克斯·韋伯提出“卡里斯瑪常態(tài)化”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卡里斯瑪型政權(quán)結(jié)束后,要么倒向傳統(tǒng)型合法性,要么邁向法治型合法性統(tǒng)治[5]。也就是說,中國(guó)社會(huì)革命的目標(biāo)雖然是邁向現(xiàn)代化,但是在革命時(shí)代之后,社會(huì)仍然可能倒退回傳統(tǒng)社會(huì)。因此,中國(guó)社會(huì)要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社會(huì),仍須做出一番更大的努力。
然則中國(guó)在目前如何實(shí)現(xiàn)向法治型轉(zhuǎn)變?法治建設(shè)屬于社會(huì)系統(tǒng)工程的一部分,實(shí)現(xiàn)法治型政權(quán)必須從社會(huì)構(gòu)成的各個(gè)要素入手。
首先,社會(huì)由3個(gè)層次構(gòu)成:上層是社會(huì)觀念,中層是社會(huì)制度,下層是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社會(huì)觀念是人們?cè)谏鐣?huì)生產(chǎn)和生活實(shí)踐中所形成的關(guān)于社會(huì)生活、生活問題、生活模式的思想、構(gòu)想或理論。社會(huì)制度指在社會(huì)組織及其可以反復(fù)適用的規(guī)則和程序,包括了規(guī)范、組織以及設(shè)備等可見內(nèi)容。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則是指各種社會(huì)力量之間所形成的相對(duì)穩(wěn)定的關(guān)系。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3個(gè)層次分別在社會(huì)過程中發(fā)揮作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是基礎(chǔ)和基本因素。社會(huì)制度是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功能,社會(huì)觀念則表達(dá)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力量,并反映整個(gè)社會(huì)制度。然而,三者并不獨(dú)立存在,從系統(tǒng)論而言,社會(huì)是一個(gè)整體的系統(tǒng),由三者共同組成,三者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約,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當(dāng)三大層次形成一個(gè)穩(wěn)定狀態(tài),社會(huì)轉(zhuǎn)型基本完成。從宏觀來看,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三者并不是同步變化的,它們的變化或先或后,相互排斥,相互整合,它們之間的沖突性推動(dòng)了社會(huì)變遷。
其次,中國(guó)的法治也應(yīng)該從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三大方面進(jìn)行系統(tǒng)建設(shè)。法律制度本屬于社會(huì)制度之一,當(dāng)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必然牽涉社會(huì)制度變動(dòng),或者社會(huì)制度變動(dòng)導(dǎo)致社會(huì)變遷。因此,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法律隨之變化,或者法律變動(dòng)時(shí)社會(huì)隨之變化。
馬克斯·韋伯提出的3種社會(huì)模式,可以歸入社會(huì)構(gòu)成中的社會(huì)制度層次。與此相對(duì)應(yīng)的社會(huì)觀念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兩個(gè)層次則與之互相配合,同為一體。如果將此分析應(yīng)用到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階段,可以看出不同時(shí)期法制建設(shè)的特色。
如前所述,在中國(guó)近百年的3個(gè)社會(huì)階段的轉(zhuǎn)型過程中,法律也是隨之而轉(zhuǎn)變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法律變化之間的關(guān)系見表1。

表1 中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法律變化
從表1中可見,社會(huì)構(gòu)成是一個(gè)整體,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三大部分是相輔相成的。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時(shí)期,國(guó)家政權(quán)的社會(huì)觀念(即意識(shí)形態(tài))以天命為合法來源,以儒家倫理為指導(dǎo);在社會(huì)制度上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型合法性,法律制度表現(xiàn)為由習(xí)慣、法律等構(gòu)成的依法而治模式;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方面,國(guó)家、士紳和農(nóng)民三足鼎立,其中士紳成為溝通國(guó)家和農(nóng)民階層的中堅(jiān)力量,國(guó)家政權(quán)表現(xiàn)為半自治型合法性。隨著時(shí)間進(jìn)入革命時(shí)代,特別是革命后期,國(guó)家政權(quán)的意識(shí)形態(tài)以沖突論為主導(dǎo),主張通過階級(jí)斗爭(zhēng)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制度層面由傳統(tǒng)型合法性逐漸轉(zhuǎn)向卡里斯瑪型合法性;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方面則以動(dòng)員型合法性推動(dòng)社會(huì)革命,以摧毀傳統(tǒng)社會(huì)的族權(quán)、神權(quán),使國(guó)家與工人、農(nóng)民階層相結(jié)合,由國(guó)家支配資源,形成以國(guó)家資本為驅(qū)動(dòng)的模式,目的是為了在短期內(nèi)達(dá)到現(xiàn)代化。此社會(huì)階段,領(lǐng)導(dǎo)意旨代替法律,法律制度化極低,甚至不存在法律。譬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司法機(jī)關(guān)就完全被取消了。因此,人治成為此階段的法律治理類型。當(dāng)國(guó)家一旦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代社會(huì),在社會(huì)觀念層面則體現(xiàn)為涂爾干所言的有機(jī)團(tuán)結(jié),即社會(huì)分工高度發(fā)達(dá),社會(huì)呈現(xiàn)和諧有序狀態(tài);在社會(huì)制度層面,以馬克斯·韋伯所指的法治型模式為主,整個(gè)社會(huì)以理性態(tài)度遵守法律,每個(gè)公民將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層面,公民力量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他們通過選舉進(jìn)行自治,并以理性態(tài)度構(gòu)建公民社會(huì)。
由此看來,法治建設(shè)必須依照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規(guī)律,從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制度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3個(gè)層面進(jìn)行實(shí)施。
三、實(shí)現(xiàn)法治的途徑
有關(guān)法律是如何變化以適應(yīng)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法律變化的3種機(jī)制:法律擬制、衡平和立法[6]。梅因所舉的標(biāo)準(zhǔn)其實(shí)是英美法系法官造法和議會(huì)立法的手段。英美法律主要是判例法,由長(zhǎng)期的判例積累而成,并且社會(huì)變遷從沒有發(fā)生過決裂,因此他所說的法律變化,往往只適應(yīng)于穩(wěn)定的英美法系國(guó)家,而不能解釋斷裂性的大陸法系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美國(guó)學(xué)者羅伯特·昂格爾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法律》中則提出3種法律類型,說明社會(huì)應(yīng)在不同的變遷階段采用3種不同的法律類型。他分類的標(biāo)準(zhǔn)是一個(gè)由寬泛的法律概念向嚴(yán)格的法律概念變化的過程[7]。他所指的第1類型法律是習(xí)慣法或相互作用的法,第2類型是官僚法或規(guī)則性法律,第3類型是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昂格爾還以中國(guó)為例,說明中國(guó)古代從習(xí)慣法發(fā)展到官僚法,卻無法產(chǎn)生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法律秩序[8]。昂格爾的觀點(diǎn)可以解釋長(zhǎng)時(shí)段的社會(huì)發(fā)展下法律的轉(zhuǎn)變,卻不能解釋較短時(shí)期,如中國(guó)百年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
與此相反,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仍然起著重要的啟迪作用,不僅在于它提醒我們,中國(guó)在后革命時(shí)代,面臨著倒向傳統(tǒng)型合法性抑或邁向法治型合法性的選擇,而且在于指出法治型社會(huì)的具體特征及其可欲性。中國(guó)在目前急劇轉(zhuǎn)型時(shí)期,為實(shí)現(xiàn)法治型社會(huì),亟須從制度、觀念和結(jié)構(gòu)3方面進(jìn)行法制建設(shè)。
第一,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型的現(xiàn)代社會(huì),要實(shí)現(xiàn)法律至上的統(tǒng)治而非人的統(tǒng)治(人治),因此,“最好是把法治理解為一種獨(dú)特的機(jī)構(gòu)體系而非一種抽象的理想。這種體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形成了專門的、相對(duì)自治的機(jī)構(gòu)。”這種機(jī)構(gòu)的建立,是通過制度安排而落實(shí)的。這意味著法律機(jī)構(gòu)取得足夠獨(dú)立的權(quán)威,通過規(guī)范約束政府的權(quán)力[9]。因此,法律制度化程度高才能保障法律機(jī)構(gòu)的獨(dú)立性,讓法律機(jī)構(gòu)通過有效的程序把糾紛納入法律解決的軌道。
第二,培養(yǎng)公民的憲政觀念。雖然法治不是一種抽象的理想,但是它具有抽象的理念,這體現(xiàn)在社會(huì)觀念對(duì)法律制度的意識(shí)當(dāng)中。如果從革命時(shí)代進(jìn)入現(xiàn)代社會(huì),制度發(fā)生改變,社會(huì)觀念必須與之相應(yīng)地變化。在革命時(shí)代的意識(shí)形態(tài)是沖突論,講究階級(jí)斗爭(zhēng)。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意識(shí)形態(tài)則是法治觀念,其目的是保護(hù)公民權(quán)利,此時(shí)應(yīng)該把沖突論轉(zhuǎn)變?yōu)楹椭C論。和諧論并非沒有矛盾,而是把矛盾平等地包容在一個(gè)共同體里討論,容忍多元價(jià)值,做到和而不同。然而,這種差異性的共同體應(yīng)當(dāng)由法律來規(guī)定,特別是由憲法予以保障。制度上的立憲主義,就是在理念上讓憲法成為公民團(tuán)結(jié)起來的根本性的聲明,“以闡述他們共享并同意用于自我約束的基本規(guī)則和價(jià)值觀念”[10]。在憲法的框架內(nèi),社會(huì)全體民眾均視為公民,都受法律的保護(hù),即使違法犯罪,也應(yīng)該在法律的限度內(nèi)進(jìn)行審判。把原本屬于政治術(shù)語(yǔ)的階級(jí)斗爭(zhēng)轉(zhuǎn)化為法律術(shù)語(yǔ)的公民矛盾。也就說,把政治法律化。相反,如果把法律政治化,則容易出現(xiàn)超出法律限度的現(xiàn)象,法律得不到尊重,法治得不到施行。
第三,從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上約束權(quán)力的濫用。法治其實(shí)就是一種制約的機(jī)制,通過法律的調(diào)整,制約各種力量的濫用權(quán)力,并逐漸改變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在向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程中,建設(shè)公民社會(huì)是法治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基礎(chǔ)。從國(guó)家—社會(huì)的兩分法來看,這種轉(zhuǎn)向就是讓社會(huì)力量強(qiáng)大起來,讓國(guó)家成為服務(wù)型機(jī)關(guān)。西方對(duì)法治學(xué)說的貢獻(xiàn)的核心就是“政府本身必須接受法律約束的概念”[10]。通過法律制約權(quán)力,是保護(hù)公民的權(quán)利有效途徑。當(dāng)然,權(quán)力制約與分權(quán)有所區(qū)別。權(quán)力制約可以分硬制約和軟制約兩類。其中,硬制約包括了分權(quán)制度、公民選舉制度。而軟制約包括:思想自我制約、內(nèi)部制約(如政黨內(nèi)部民主)、市場(chǎng)制約、結(jié)構(gòu)制約(階層力量對(duì)比)或協(xié)商制度制約。公民社會(huì)是結(jié)構(gòu)制約方式之一,在未來的中國(guó),必須建立強(qiáng)大的公民社會(huì),才能制約權(quán)力的濫用,才能實(shí)現(xiàn)法治。
中國(guó)是否要完全移植西方的制度,才能達(dá)到法治呢?其實(shí)不然,只要遵循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規(guī)律,從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制度3方面對(duì)癥下藥,使三者相互適應(yīng),相互配合,即可邁進(jìn)現(xiàn)代法治社會(huì)。
[1]Trevor Noble.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change[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118 -144.
[2]Robert Weatherley,Politics in China since 1949: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 rule[M].London:Routledge,2006:3.
[3]馬克斯·韋伯.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M].林榮遠(yuǎn),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238-240.
[4]石元康.天命與正當(dāng)性:從韋伯的分類看儒家的政道[J].開放時(shí)代,1999(6):5.
[5]布勞,梅耶.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科層制[M].馬戎,時(shí)憲明,邱澤奇,譯.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1:63-73.
[6]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7:15.
[7]尹伊君.社會(huì)變遷的法律解釋[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229-230.
[8]昂格爾.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法律[M].吳玉章,周漢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44 -131.
[9]諾內(nèi)特,塞爾茲尼克.轉(zhuǎn)變中的法律與社會(huì):邁向回應(yīng)型法[M].張志銘,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53.
[10]海格.法治:決策者概念指南[M].曼斯菲爾德太平洋事務(wù)所中心,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