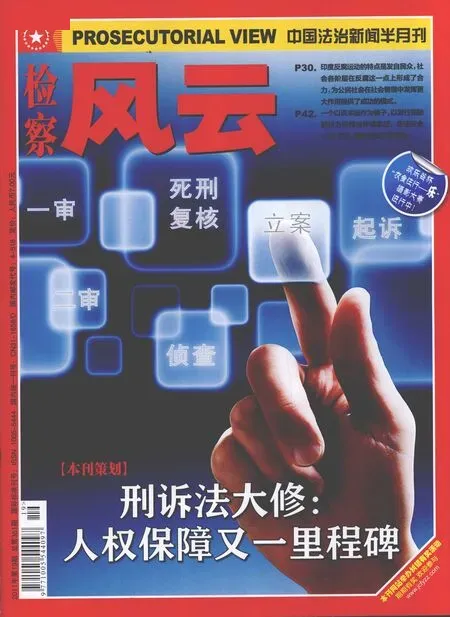哈瓊文與他的宣傳畫
文/華逸龍
哈瓊文與他的宣傳畫
文/華逸龍
哈瓊文,1925年生,今年已87歲了。因年事已高,故已封筆。現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曾為該同盟第十屆上海市委委員)。游龍姑(哈瓊文之妻)1993年去世,她也是知名的宣傳畫家,代表作有1962年出版的宣傳畫《支援世界人民的反帝斗爭》(1988年載于日本東京都株式會社講談社版《世界現代招帖畫設計》)等。包括她在內的大家庭十人中有九人是畫家。除了我之外,應當說大家從事繪畫都是受了哈瓊文、游龍姑的影響。現在大家都各自忙著,曾有人提議說,什么時候開個家庭畫展,出本畫冊,也是對過去的總結和紀念。
去年,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往事》欄目播放了“哈瓊文宣傳畫浮沉記”,嘉賓是哈瓊文的女兒(即我太太哈思陽)。看了節目的親戚朋友、小區鄰居紛紛反饋自己的觀感。太太的一個知青插妹說看兩次哭兩次;樓上的一位老太太講自己做姑娘時收藏了《毛主席萬歲》的小印刷品,搬了幾次家還保存得好好的。多不容易啊,這張小畫片足足保存了51年。巧的是,今年3月12日,上海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上海故事》欄目播了“記憶中的宣傳畫”,說到哈瓊文時,這位老太太接受采訪中說到了這事。
《毛主席萬歲》宣傳畫是哈瓊文1959年創作的。從1959年出版到1964年連續五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以全張、對開、16開、32開等大小七種不同形式20多次重版印刷了250余萬張。此作品出版后沒幾天,在上海南京路中百一店正門上方的墻上,就出現一幅幾層樓高的《毛主席萬歲》巨幅復制品。1960年作家冰心在《北京晚報》上也以熱情洋溢的文章《用畫來歌頌》贊揚此畫,說:“我見過一幅宣傳畫……畫筆十分生動,看過就不能忘懷。以后在報刊上看過幾次,但是我在市場上始終沒有買到。最近我托一位城里的朋友替我弄到一幅。拿到了釘在墻上,仔細欣賞,果然是好!”哈瓊文的老上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楊可揚在《哈瓊文》一書的序文中就這樣說:“特別是(哈瓊文同志)為建國十周年而精心創作的《毛主席萬歲》,更是轟動一時,譽滿全國。”這幅哈瓊文宣傳畫中的代表作后來被上海美術館收藏。2009年,在此畫問世時隔50年后,該社再次將它重版并以盒裝、年歷等多種形式發行,一件作品出版前后跨時50年。


其實哈瓊文的畫得到人們的喜歡不是偶然的。除了內容喜聞樂見、積極向上,還在于他的作品有著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而這一切的取得都源于他具有嫻熟的表現力。他1949年畢業于中央大學,老師呂斯百、黃顯之、秦宣夫等都曾留學法國,在他們那里他學到的是寫實風格的油畫。他在1950年當過華東軍事政治大學藝術系教師;1953年做過中央軍委總政文化部美術工作室專職創作員;后因同是同學、同事的妻子游龍姑1955年轉業到了上海,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當創作員,哈瓊文隨后也轉業到了上海,也進了該社當了創作員。哈瓊文的造型能力極強,油畫是他的強項,水彩、水粉更是手到拈來,出手又極快,就是在畫家眾多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其專業水平也是較為突出的。他除了高產之外,還常常當同事的教員,我就看到他幫其他創作員改畫,既肯定又迅速。楊可揚就這樣斷言:“哈瓊文同志當時在出版社編創人員中,是一位作品多產、優質的佼佼者。”
哈瓊文是北京人,說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在上海住這么多年仍不會說上海話,性格也具北方人的豪爽。正因為如此,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遭小組批大會斗,差點掉了性命,并使一只眼睛喪失了視力(哈瓊文語)”。
讓人沒料到的是,人人喜歡的《毛主席萬歲》這張畫卻在“文革”中受到了強烈的批判,畫中那個在冰心眼里被看做“穿上深色素靜的衣服,戴上綠玉的別針和耳環,這節日的裝飾,使她顯得更加精神、更加俏麗”的少婦,在有些人的眼里變成了“資產階級少奶奶”,那么,創作出此形象的人一定是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藝術觀”了。雖然有人在批他的畫,但是凡是有繪畫任務,有關方面還是交給他或者派他領銜去完成,因為他不是那些只會嘴上喊喊口號之人可以代替的繪畫“佼佼者”,當然這少不了那些人對他的監視。他事后寫道:“‘文革’后期,工宣隊把我送交魯迅紀念館參加有關魯迅歷史畫的創作,我當時像被送去監督勞動,工宣隊過一段時間就要去了解我的表現,使我心情十分壓抑。”那時,哈瓊文的確是很艱難,妻子游龍姑雖患嚴重心臟病,還是被“發配”到農村勞動,家里有三個十幾歲的孩子無大人照顧,他自己剛畫完油畫《魯迅》,又被送到南匯去做農村工作,這一去又是一年。對一個藝術上有這么高造詣又這么癡迷繪畫的畫家,這種摧殘給他帶來的痛苦可想而知。無奈之下,只能拼命作畫;雖然畫的是任務畫,但畫畫時能讓他暫時忘卻那些痛苦。
“文革”結束時哈瓊文已51歲了,雖然只能用一只眼睛來畫畫,比較困難,但是可以畫自己想畫的東西,心情愉快了。除了為自己單位創作宣傳畫外,他還創作了不少油畫。常常有作品發表、出版、參加國內外美展并獲獎和被收藏。他早期的作品寫實,形準,塑造感強,所畫形象呼之欲出,色彩強烈,調子和諧,整個畫面呈更多的西畫風格;后來的作品更多展示裝飾意味,構圖更具構成意識,造型趨于平面化,線條感強烈,色彩更主觀,整個畫面呈中國民族風格。如果說前者是因作者追求真實而更具時代共性的話,那么后者是因作者追求抽象的繪畫性而顯現了個性,所以說哈瓊文后期作品已具自己鮮明的風格。
我曾和哈瓊文合作過一對門畫(年畫),畫面是兩個解放軍騎在馬上。我負責起稿,他負責上色,他竟把其中一匹坐騎畫成漆黑。這讓我很吃驚,也很受啟發。門畫本來有一個鮮艷的紅色底子,在它上面畫明度差不多的顏色都會使畫面灰掉。黑色是極色,以它最低的明度與紅底色的中等明度建立起了畫面強烈的黑白關系。這是包括我在內的有些畫色彩的人不懂的竅門,即色彩不光只有色相、純度,更起碼的是要有明度。哈瓊文是諳熟此法的:早期畫的《毛主席萬歲》中的母親的旗袍就是純黑色的,在粉紅色的花海底子上特別顯眼;1983年畫的《撒滿神州處處春》中的天女亦一襲黑衣,在淡綠色的空中,平涂的黑色比前者受過環境色影響的黑色更黑更濃更單純。自此我懂得了這個道理,不但使我的畫面色彩關系正確起來了,還解決了色彩中的素描關系,也就是說會使用色彩了。與哈瓊文合作時學到的這些東西,在我以后畫畫時一直派著用場。
編輯: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