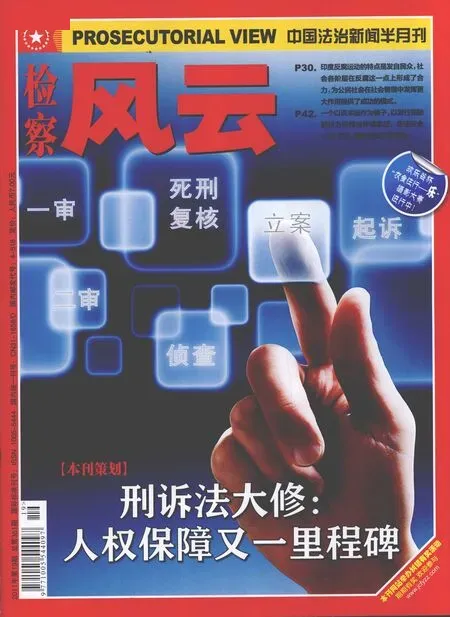證據(jù)是否為王?透視刑事證據(jù)法條在刑訴法中的增修
〈焦點二〉
證據(jù)是否為王?透視刑事證據(jù)法條在刑訴法中的增修

證據(jù),是司法機關查明案情、認定犯罪、進行訴訟活動的基礎。人們常說“打官司就是打證據(jù)”,可見證據(jù)在訴訟中的重要地位。刑事訴訟中,證據(jù)事關被告人的生死、人身自由的剝奪、此罪與彼罪的區(qū)別,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近期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中涉及證據(jù)制度的立、改、廢,既有不少亮點,也引來多方熱議。
明確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
本次修法,非法證據(jù)排除入法,廣受關注。
現(xiàn)行的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終結(jié)、提起公訴和作出有罪判決均規(guī)定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修正案草案對這個標準進行了細化。草案規(guī)定,證據(jù)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jù)證明;據(jù)以定案的證據(jù)均經(jīng)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jù),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汪建成說,關于證明標準問題,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比較籠統(tǒng),究竟什么是符合“證據(jù)確實、充分”,確實、充分到什么程度,法律上不明確。這次修正案草案明確了“綜合全案證據(jù),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就是對證據(jù)確實充分的最好注解。這是一個明顯進步。
對于“排除合理懷疑”,又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wèi)東認為,證明標準中列舉的三個條件,是對證據(jù)確實充分的認定。排除合理懷疑主要是吸收了英美法系的證據(jù)標準,就是說認定的事實所存在的懷疑,必須要做到有具體根據(jù),建立在對案件客觀事實的綜合分析上,在法官內(nèi)心確信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從而達到排除合理懷疑。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在分組審議草案時認為,這次證據(jù)方面的修改確立了“證據(jù)確實、充分”的原則,這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在如何認定證據(jù)具備確實、充分條件的時候,要充分考慮證據(jù)使用的三個基本要求:一是真實性、二是合法性、三是關聯(lián)性。現(xiàn)在提出要對所認定事實以排除合理懷疑,出發(fā)點很好,但對合理懷疑的排除在操作上不好把握,草案中如何表述和把握需要慎重。
“逼”出來的口供無效
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定》,強調(diào)經(jīng)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jù),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jù)。這次刑訴法修改,將這一重要成果寫入了草案:“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fā)現(xiàn)有應當排除的證據(jù)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jù)。”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wèi)東說,凡是以刑訊逼供這樣的方式獲得的口供不應作為定案的依據(jù),這才能從根本上切斷刑訊逼供的動力源,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汪建成表示,“此次修法重點放在了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定上,而且還規(guī)定了嚴密的、嚴格的證據(jù)收集程序。這將對遏制刑訊逼供起到重要作用。”
修正案草案中增加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fā)現(xiàn)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jù)的,應當進行調(diào)查核實。在對證據(jù)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diào)查的過程中,由人民檢察院對證據(jù)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法律規(guī)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jù)的情形的,應當對證據(jù)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diào)查。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經(jīng)依法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
專家指出,通過程序設計使得司法機關嚴把證據(jù)關,規(guī)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排除非法證據(jù)的程序,形成法庭初步審查——控方提供證據(jù)——控辯雙方質(zhì)證——法庭審查處理等一套完整的非法證據(jù)排除體系。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程序才能使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落到實處。
專家表示,這些規(guī)定體現(xiàn)了立法者希望通過公、檢、法三家機關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各環(huán)節(jié)排除非法證據(jù),共同遏制刑訊逼供的立法意圖。
摒棄“毒樹之果”還需循序漸進
修正案草案中的規(guī)定,主要排除了非法獲得的言詞證據(jù)。那通過這些言詞證據(jù)派生出來的實物證據(jù),例如嫌疑人被刑訊之后交代了作案兇器,辦案人員又通過合法手段找到了兇器,是否能夠作為定案依據(jù),是個重要的問題。
談到排除非法證據(jù),就不得不說“毒樹之果”。刑事證據(jù)中的“毒樹之果”理論是一個讓人兩難的問題。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汪建成解釋了何為“毒樹之果”——以非法行為收集證據(jù)為“毒樹”,以這個非法行為為線索,又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證據(jù)叫“之果”。比如說,通過刑訊逼供讓犯罪嫌疑人說出了在某個地點藏匿了行兇的兇器——一把刀,偵查人員通過找到了這把刀作為物證,證明了犯罪嫌疑人有罪。刑訊逼供是“毒樹”,找到的這個物證——刀,就是“之果”。如果說刑訊得到的口供是一棵有毒的樹,那么根據(jù)這個口供找到的實物證據(jù),就是毒樹結(jié)出的果實。
因此,非法證據(jù)排除要排除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個問題了。有的人說,非法證據(jù)排除到“毒樹”,“之果”不必排除。有的人說,應當排除非法取證行為,就要排除“毒樹”和“之果”。目前,學術界兩種意見有分歧。
汪建成說,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排除“毒樹之果”的,多數(shù)國家在排除上是慎重的。即使是美國,表面上看排除,但是也有很多判例法中的例外規(guī)定。把這些例外都排除了,很難想象有什么“毒樹之果”能排除。
汪建成認為,中國法制建設還要循序漸進。我們先做到第一步,把“毒樹”排除了就很好,“之果”排除不太現(xiàn)實。因為,“之果”的收集程序是合法的。目前,我國能按照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認真貫徹執(zhí)行就實屬不易了,現(xiàn)在是要解決發(fā)展中的問題。
陳衛(wèi)東也表示,對“毒樹之果”不能一概否定,但應該有一個底線。現(xiàn)在的修正案草案規(guī)定,違反法律規(guī)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對該證據(jù)應當予以排除。我認為這是對的,但不應僅限于此,還應包括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毒樹之果”。有這個底線,就會對偵查人員起到警示作用,時時提醒他們依照法定程序去收集證據(jù)。
非法取證當包括“威脅、引誘、欺騙”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規(guī)定了嚴禁采用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jù),但把刑事訴訟法中原有的“以威脅、引誘、欺騙”刪掉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金碩仁認為,草案修改導致法條規(guī)定過于籠統(tǒng),缺少對偵查人員濫用偵查權(quán)的針對性限定,建議繼續(xù)保留原有的“以威脅、引誘、欺騙”。
有學者表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非法取證方法的規(guī)定,僅僅表述為“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guī)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對該證據(jù)也應當予以排除。”這種修改過于籠統(tǒng),應該用明確和詳細的列舉,才可能在一定限度內(nèi)遏制刑訊逼供。
采用暴力、威脅、引誘、利誘、欺騙、體罰、限制休息和飲食等其他心理、生理上的強制方法,都應明確寫入非法取證條文中。
對此,也有刑事訴訟法學專家提出了相反意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認為:“威脅、引誘、欺騙與一些偵查訊問技巧和手段有重合,籠統(tǒng)規(guī)定未嘗不可。”
陳衛(wèi)東強調(diào),偵查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做出特別惡劣、嚴重的威脅、引誘、欺騙應當被禁止。他建議增加一條:如果威脅、引誘、欺騙已嚴重地侵犯了當事人的權(quán)利、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該屬于非法證據(jù)加以排除。
至于誰來界定威脅、引誘、欺騙是否“嚴重”,陳衛(wèi)東認為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范圍,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者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判例來確定,而不能完全憑法官的主觀判斷。
尊重行政處罰中的物證
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規(guī)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zhí)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jù)材料,經(jīng)過司法機關核實,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
行政執(zhí)法中取得的物證、書證,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采納,得到檢察機關的一致贊同:這意味著行政處罰證據(jù)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確,對偵查機關的影響很大。
第一,刑事審判中,很多案件從行政執(zhí)法中轉(zhuǎn)化而來。現(xiàn)實中,行政執(zhí)法機關往往“大權(quán)在握”,處于懲治違法犯罪的第一線。但由于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權(quán)利義務不同,行政執(zhí)法機關掌握的大量違法犯罪一手材料不能作為刑事案件的證據(jù)被采用,需要偵查機關重新收集整理,無疑造成偵查機關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
第二,有望消除以往由于偵查機關重新取證存在的隱患,即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在行政執(zhí)法后消滅或者隱藏涉案物證、書證。
陳衛(wèi)東認為,物證、書證與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陳述不同,物證、書證具有很強的客觀性,不因調(diào)取證據(jù)的執(zhí)法機關不同而發(fā)生改變。
對擁有行政執(zhí)法權(quán)的執(zhí)法機關而言,這條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新規(guī)利弊兼而有之。
弊是,行政執(zhí)法人員需要更加重視對物證、書證的整理收集。但行政執(zhí)法人員不懂刑事取證規(guī)則的情況并不罕見,身處行政執(zhí)法一線,有些物證、書證按照刑法規(guī)定究竟該不該扣,行政執(zhí)法者未必清楚。以煙草專賣機構(gòu)查獲的銷售假煙商販為例,詢問筆錄、調(diào)查清單、售假香煙的作價、獲利金額的統(tǒng)計等,煙草專賣機構(gòu)往往可以第一時間獲取。一旦煙草專賣機構(gòu)行政處罰這一環(huán)存有疏漏,售假案值按照單次售假金額計算,而未按刑法規(guī)定累加計算。售假者有可能交一筆大額罰款后,逍遙法外。
利是,如果行政執(zhí)法人員能夠準確收集物證、書證,則可以將售假者繩之以法,免除后患。杜絕了有案不移、有案難移、以罰代刑的發(fā)生。既懲治了犯罪,也維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
對此,陳衛(wèi)東也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在“行政機關在行政執(zhí)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jù)材料”中,行政機關收集的錄音、視頻資料、行政機關做出的鑒定結(jié)論和處罰結(jié)論是否屬于可以被偵查、審判機關采納的證據(jù)?草案中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
來自基層公安、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呼聲強烈:行政執(zhí)法機關面臨的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本來就很復雜,如果不能以立法的形式明確哪些證據(jù)在刑事訴訟中不能使用,恐怕實踐中混亂的局面難以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