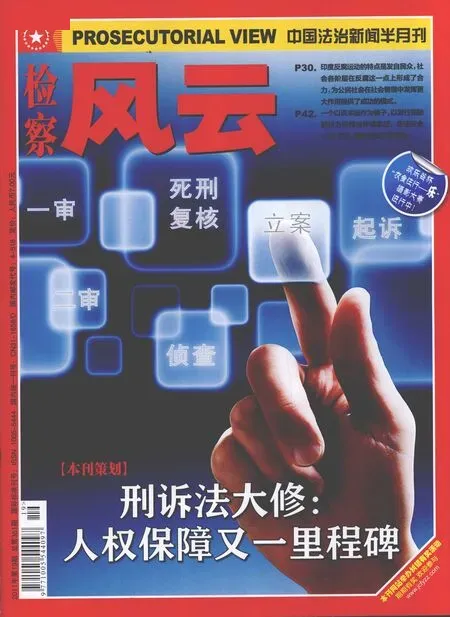“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之解讀
文/馮波
新視點·專家視點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之解讀
文/馮波

馮波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政治與法律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
傳媒社會學關注傳媒與社會的關系及其規律,將傳媒看做是嵌入于社會中又對社會有自己獨特作用的社會事實。在傳媒的各個要素中,傳者與社會的關系是最動態、具體的。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歷史時期,傳者受社會的制約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都是不同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作為當下中國社會環境下的一種傳者角色要求,有其從傳媒社會學角度透視下的意義。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是當代中國社會對傳者的要求,在其他國家不可復制。
在我國的傳媒界,存在著一些與“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相悖的現象,例如,有的記者不愿意下基層,涉及基層的新聞報道只是靠打個電話、網絡郵件等間接途徑來完成,這就大大影響了新聞報道的公信力。所以,必須通過大規模的組織動員,鼓勵記者轉變工作作風,下基層掌握第一手資料,以使新聞報道真實、準確地反映新聞事實。在文風方面,提倡用“我”這種第一人稱進行報道,以使記者的直接經驗充分呈現。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也是中共中央向全黨提出的向人民群眾學習、拜人民為師要求在傳媒業界的體現。2011年7月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只有我們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各級黨政機關和干部要堅持重心下移,經常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做到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從眼睛向上到眼睛向下,這種重心轉移的背后,是對執政黨合法性基礎、資源的考量,是對黨員干部、黨的各項工作的根本要求之一,新聞媒體也自然包括其中——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責無旁貸。《大眾日報》報業集團的資深媒體人劉明洋2011年9月9日回答筆者的咨詢時對筆者說,作為集團的領導之一,他現在要保證每個月帶領記者們下基層一次,回來后要親自執筆寫一篇詳細的下基層匯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記者劉菲也向筆者介紹說,《人民日報》是按照職務高低分期安排下基層活動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特別制定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臺領導落實“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方案》,計劃在2011年9月初至11月底,由臺領導按照各自分工范圍,以全臺各頻率為主體,組成若干個下基層小分隊,根據各自頻率定位,自主確定對象地區,自主策劃選題。
就“走基層”的社會功能來看,可以從顯功能和潛功能、正功能和負功能兩個角度來分析。
就顯功能和潛功能而言,“走基層”的顯功能,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云山在2011年8月9日召開的中宣部、中央外宣辦、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記協等五部門“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視頻會議上所強調的:新聞媒體要深入到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線,接受社會實踐的鍛煉;要有針對性解決突出問題,推動新聞宣傳工作邁上新的臺階,為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應有貢獻。“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新聞工作承擔著宣傳群眾、動員群眾、服務群眾的重要職責,必須牢固樹立群眾觀點,自覺踐行群眾路線。新聞戰線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是堅持黨的新聞事業性質宗旨、履行新聞工作責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實‘三貼近’要求、增強新聞宣傳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徑,是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新聞工作者綜合素養的有效舉措。”簡言之,新聞媒體“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接受社會實踐的鍛煉,有針對性地解決突出問題,推動新聞宣傳工作邁上新的臺階,為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應有貢獻。上述目標是“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的倡議者希望實現的顯功能,這些功能能否實現、實現的程度如何,取決于新聞媒體的從業者對“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的踐行程度。
從潛功能方面看,“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對參與主體也會發揮一些微觀層面的作用,這些功能是潛在的,是活動的發起者之前沒有預料到的。實際上,很多社會行為都同時存在潛功能和顯功能,正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筆者于2010年10月到北京海淀黨校參加培訓,本來的顯功能當然是接受黨的理論、政策、方針教育,但筆者在三周的時間里收獲到了來自不同的北京高校同仁之間的坦承與友誼。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后,位于甘肅隴南的災區記者們不顧危險、克服道路不通的困難,堅持到災區第一線去。他們依靠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充分報道了災情,同時,也充分安慰了人民。時任隴南電視臺臺長的陳永貴2009年4月底向去隴南調查地震災害及災后重建報道情況的筆者及隨行師生介紹說:在地震剛剛發生之后,政府給了災民物質上的支持,深入災區的隴南電視臺記者給了災民精神上的支持,很多災民見到記者后大哭,他們像看到親人一樣,找到了精神的宣泄口。同理,“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在發揮其顯功能的同時,也存在著其必然的潛功能。中國傳媒大學2010屆社會學專業畢業生、現供職于黑龍江電視臺的出鏡記者朱方芳2011年9月6日在人人網上回復筆者的留言(關于記者下基層,你有何感想和體會?盼復!)時這樣寫道:“老師,我剛去了幾次基層,去大興安嶺林區拍了公路勘測者,一天的路才走了一半,已經疲憊得連話都不想說了。其實現在下基層這個表述我覺得有點不妥,基層本來就是記者應該在的地方,用‘下’字來形容就不太合適。在基層感觸特別多,人性的好多東西特別吸引人。比如那些話不太多但是特別有韌勁的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努力的人,其實一點都不會覺得生活累。”方芳的回答充分說明了下基層的潛功能。在任務范圍之外,記者可以體會到平凡勞動者的心靈境界:話不太多但是特別有韌勁,知道自己為什么而努力。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他們并不會如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覺得生活累。這些關于人性的體驗對下基層的記者本身是一種震撼,是特別吸引他們的地方。
只有意識到可能會出現的負功能,才能采取措施盡量避免其發生,也才能使正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正功能、負功能。因為,任何社會行動都是人的一種選擇,作為選擇,一定有利有弊。今年7·23動車事故處理的負功能在民間有很豐富的、多角度的傳聞和解釋。無論何種社會行動,無視負功能的存在都是愚蠢的。只有意識到可能會出現的負功能,才能采取措施盡量避免其發生,也才能使正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就筆者訪談和觀察、思考所及的資料限度,筆者認為,“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存在以下幾種負功能:
其一,流于形式,形式大于內容。筆者發現,很多電視臺、報紙都開辟了“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的專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正在成為一場如火如荼的媒介運動。但是,筆者所擔心的是:這種運動似乎有一種追求為下基層而下基層的趨勢。有的專欄中,報道的只是一些表層的東西,比如,記者走了多遠的路,到了什么什么學校,看到一群孩子在上課。他們中午吃自己帶的冷飯,立志考大學改變命運,等等。筆者真不知道這樣的“新聞”報道有什么意義?難道只是為了湊數,證明這些記者下基層了嗎?其二,過多、過濫、魚龍混雜的下基層活動非但不能很好地起到關心群眾疾苦、反映群眾心聲的作用,反倒會引起群眾反感,甚至增加群眾的負擔。基層干部頻繁地接待媒體的“下基層”活動,勢必會增加基層的招待費用,分散基層干部的精力。因此,需要對“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進行精心的策劃,周到的安排,選取有價值的新聞線索去采訪,以避免盲目性、形式化的、為下基層而下基層的下基層活動。第三,正如方芳所說的,基層本來就是記者應該在的地方。《北京日報》的佟志革編輯2011年9月9日回答筆者的咨詢時也談到:記者本來就應該在基層,下基層是對媒體領導而言的,領導要下基層。筆者認為,對下基層的主體不做具體區分的現狀,不僅是邏輯上的混亂,更會造成角色的混亂,特別是把本來是記者分內的角色規范當做一種高標準來要求,會給傳媒業界帶來不良的影響。這正如一個廠長的分內之事就是搞好生產,但是他把生產搞好了卻被大加贊賞,這不是很滑稽嗎?所以,筆者建議:一定要盡快區分出下基層的主體到底是誰?不是新聞媒體,新聞媒體作為一種社會組織,一個集體稱謂,不可能下基層。也不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從基層獲取新聞信息,是作為記者的職責所在。下基層的主體應該是新聞媒體的領導干部。
總之,“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作為當前中國新聞媒體的一道媒介景觀,需要我們從廣泛的、深入的社會視角去審視,盡量避免其負功能,這樣才能把“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這部“真經”念正,不使其念歪。否則會事倍功半,發揮不了應有的顯功能和正功能。
到基層去,在任務范圍之外,記者可以體會到平凡勞動者的心靈境界:話不太多但是特別有韌勁,知道自己為什么而努力。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他們并不會如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覺得生活累。這些關于人性的體驗對下基層的記者本身是一種震撼,是特別吸引他們的地方。
編輯:董曉菊 dxj5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