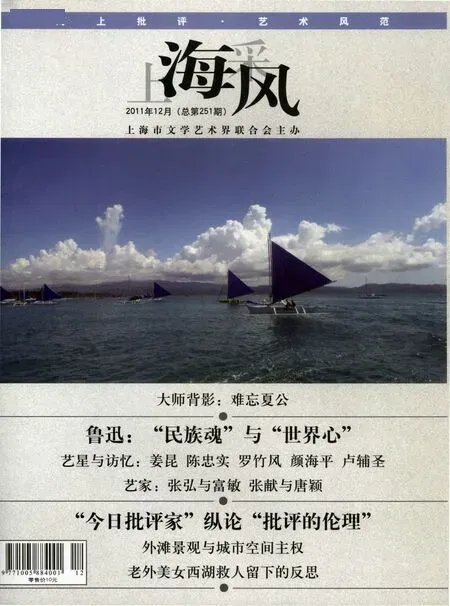姜昆:永遠有一顆探索之心
文/特約記者 程 也

他是舞臺上的開心果
在整潔的辦公室里面對面坐下,終于見到了家喻戶曉的笑星姜昆。與舞臺上、熒屏里一樣,生活中的姜昆也是一付樂呵呵的模樣,平易近人,忙忙叨叨。能夠如此近距離地看他樂呵呵的笑臉,聽他妙語連珠的神侃,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我知道,這樣的聊天,對于他這個出了名的大忙人來說,可謂是難得的奢侈時刻。果然,采訪一再被前來拜訪的客人打斷。我們的話題也就總離不開那些讓他忙碌的事情。不過,姜昆似乎并不以忙碌為苦,相反倒是樂在其中。
好奇讓我保持工作狀態
姜昆聊起天來給人一種天文地理無所不知的感覺,他自己說并不是無所不知,而是無所不感興趣:“世界上未知的東西太多了,很多領域的很多東西并非我能了解,每個人的認識都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去嘗試了解它,或者思考一下現在的最新技術將可能給人們的生活帶去什么變化。”說到很多話題他的眼里都會閃過一些光彩,臉上則露出些許頑皮和好奇,好像推開了一扇進入新奇世界的大門。
姜昆說自己是一個有多方面愛好的人,詩詞歌賦、科學技術等等,關于宇宙世界各個方面的知識他都很好奇。“我每天都像海綿吸水一樣在吸收新東西,從報紙上看到的、從人們談論中聽到的新事物都會引起我的思考。”他說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并不能按照上班下班截然分開,他的狀態是,只要醒著就在不斷地打量著世界,思索著。世界萬物如此豐富,都成了他創作的源泉。
姜昆告訴我,相聲的素材往往是很小的,但卻是經過了長期的搜集和積累才能得到的。創新是火花亮點,也是水到渠成。所以盡管如今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有資格吃老本了,但他卻不斷有金點子閃現,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保持著工作狀態。他有意識地通過各種途徑去發現新知識,并且進行思考。“世界太豐富了,從農耕時代到現在的信息時代,那么多新的東西不斷涌現,總給我一種永遠渴望求知的感覺。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心去想,用自己的腦子去記,大跨度地去了解與探索,爭取多發掘一些相聲素材,多產生一些新的、好的相聲作品。”他說,“全國各地的觀眾經常問我有什么新作,問我‘今年春節晚會給我們制造什么新的歡笑?’我覺得大家對我抱有希望,我自己也有這份責任不斷地進行創作。”
特別期待演出大幕開啟的瞬間
姜昆從小就特別喜歡文藝。他家住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附近,其父特別喜歡看京味話劇,每次有演出了,父親就會帶著小姜昆去看。雖然買的是最便宜的票,但演員都是大家,比如于是之、刁光覃先生等。精彩的演出讓姜昆備受感染,特別想當話劇演員。童年的姜昆最期待的就是演出大幕開啟的瞬間,因為色彩斑斕的故事馬上就要開場了。
姜昆對音樂也十分愛好,尤其喜歡手風琴。在他小的時候家里生活比較拮據,他想要一個手風琴卻不好意思開口。于是就向別人打聽音符在鍵盤上的位置,然后在課桌上用白紙畫出一個鍵盤比劃著彈,居然也玩得八九不離十。
小學四年級時,姜昆報考了少年宮的“戲劇組”。第一次走上舞臺是參加《媽媽在你身旁》的演出,他在這個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兒童生活的獨幕話劇中飾演主人公“黑牛”。這次成功的演出讓他對“演員夢”更加著迷。在小學六年級畢業時,他鬧著要爸爸帶他去考中國戲曲學校。然而他爸爸看到戲校的小演員練習翻跟頭、倒立時汗流浹背的樣子,感到非常心疼。想起“十年出得了一個秀才,出不了一個藝人”的老話,他楞是沒舍得讓自己兒子去報考。
可是,沒過多久,姜昆在少年宮活動中被影片《白求恩大夫》的導演看中,于是小小年紀的姜昆就自作主張跑到河北保定拍電影去了。這次“觸電”讓姜昆對自己的演員夢大打折扣。原來,他并不是《小兵張嘎》中的“嘎子”那樣的主角,而是一個只有十幾秒鐘鏡頭的“望風的小八路”。就為了這個,他從北京跑到河北專區,整整花了五天的時間,而且還“又跑又喊”了幾遍才算通過。回到北京后,姜昆就一直躲著不肯見人,更不好意思見爸爸,怕說起這個話題。
從那以后,姜昆開始“收心”,不僅努力學習,而且讀了很多文學書籍。可惜,在他剛剛初中畢業的時候就遇上了一個講“階級斗爭”的年代。沒有地方上學的他變得整天無所事事。到他也可以出去“大串連”的時候,在南下的火車上,他每天早上都帶頭高唱《東方紅》,而他的朗誦也引得全列車的人情緒高漲。他回憶說,“在我繪聲繪色的朗誦中,我看到居然能吸引那么多人的目光。他們盯著我,我覺得過癮極了!”在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里,荒蕪很久的文藝舞臺開始繁榮。姜昆叫了幾個同樣愛好文藝的伙伴,拉起了一個“紅衛兵話劇團”,不到兩個星期,寫出了一部六幕八場的話劇。然后又是排練,又是做布景、搞服裝道具,忙得不亦樂乎。他們的演出進行了五十多場,直到姜昆報名上山下鄉去北大荒。

姜昆和外國魔術師交流
我也要說相聲
姜昆在北大荒一呆就是8年,因為他能唱會演,還在表演時經常加入新的笑料,他在兵團漸漸有了一些影響力。但是他沒有正兒八經地聽過相聲,直到1973年的一天,中央廣播文工團的相聲演員郝愛民和李文華到北大荒慰問演出。姜昆得到領導的批準坐了一個多小時的火車,趕到鶴崗市聽相聲。精彩的演出讓姜昆特別激動。當他和隊友們聽完相聲走出劇場時,已經是深夜。回連隊的火車已經沒有了,他們就圍在車站里的爐子旁取暖。姜昆默默回味著相聲的魅力,產生一個念頭——“我也要說相聲”。回去后,他憑著記憶把相聲默寫出來,在連隊進行表演。
1975年,通過層層選拔,姜昆和另外兩個人合說的三人相聲《大鋼連長》代表黑龍江省到北京參加表演,并獲得了成功。他們返回時住在哈爾濱的體委招待所,一天晚上10點多,突然進來一位民警大聲說:“誰是姜昆?跟我走一趟!” 把姜昆著實嚇了一跳。上了民警的車,一路冷風颼颼,姜昆的心里七上八下。讓他萬分驚訝的是,民警把他帶到一個房間,推開門,里面居然坐著大名鼎鼎的馬季和唐杰忠!兩位相聲大師和姜昆一問一答:“你愿意當演員嗎?”“愿意!”你愿意從事相聲事業嗎?”“愿意!”“你愿意到我們團來嗎?”“愿意!”。三個“愿意”說完了,姜昆感覺暈暈乎乎的。這簡短的對話對他的人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他新的藝術生涯就要開始了。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從1985年起,姜昆開始和唐杰忠老師一起合作,這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那時候我當學員,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坐下。我不敢想我們倆以后能一起合作。”還有李文華老師,那個第一次用相聲魅力觸動他心靈的相聲前輩,他做夢也想不到能與他搭檔合說《如此照相》《想入非非》等經典段子。在《藝術人生》錄制現場,因為喉癌做完全喉切除手術而無法說話的李文華老師給主持人朱軍寫了很多他想說的話,對于姜昆,他寫道:“姜給我的印象是最喜歡相聲,姜昆對朋友熱情,很尊重合作者……”對此姜昆覺得恰恰是因為有老一輩的好演員帶著,才能夠有他之后的成績,他覺得相聲走到今天,他有很大的責任要傳好接力棒。每一個創新將來都是傳統。傳統又不斷為創新所取代。在他看來,傳統是基礎、創新是關鍵,創作則是一種責任。
當演員是姜昆最大的夢想,但是他的行政職務也很多,他覺得這對于他在業務上的鉆研會有一些影響,但是對曲藝藝術的發展卻能夠做更多的事情,就這點來說,他認為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情。他組織編撰的《中國傳統相聲大全》《中國曲藝通史》《中國曲藝藝術概論》等已經成為研究中國曲藝的權威資料。姜昆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成功的軌跡,他從說相聲開始,起點比較高,如果只是沿著老套路,也許仍能保持很好的局面,但也就此停滯不前了。人都有惰性,不進則退。他愿意不斷去發現新的知識,不斷創新,不斷突破。人們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就是因為眼界不夠開闊。要想不斷進步就必須不斷接受新的事物,不斷有所發現。
姜昆是一個特別樂于嘗試新事物的人,他曾連續多年主持春節聯歡晚會,上世紀九十年代他還和楊瀾共同主持了《正大綜藝》,一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可謂家喻戶曉。姜昆在說這句話的時候還要有一個擺手的動作,重溫當年,很多人覺得這個動作比較好笑,姜昆也坦言的確有點“傻帽”。雖然這個傻帽的姜昆當時已經有40歲了,但是在主持人領域,他還是青澀而勇敢的,因為他希望表演真正的脫口秀,不要串詞,也不是簡單的報幕,而是嘗試一種新的挑戰。
他不僅轉戰各種舞臺,而且早在1989年就開始接觸電腦的世界,用自己買的第一臺286電腦把寫的東西存起來、打出來,要知道,在當時很多人還不知道電腦為何物。緊跟時代潮流的他在互聯網出現并普及后還嘗試注冊網名,之后又辦起了網站。1998年,他下海籌建公司,并先后開辦了昆朋相聲網和中國名人網。在相聲日益滑坡的時候,姜昆的這種舉動引發了不少質疑。對此,他說:“我一生當中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愿望,但從來沒有一個愿望如此之強烈。我從事相聲事業以來,一直有一個心愿是給我們的相聲事業蓋一座大廈。這座大廈要有我們相聲的歷史,相聲的今天,甚至包括相聲的未來。而且要包含音、像、文字等各種實物,我要讓它展現出來,因為我們中國的相聲藝術和笑的藝術一點也不比外國的差。但我發現真的去蓋一座大廈其實是天方夜譚,根本完成不了。終于有一天,當我接觸到網絡的時候,我發現世界上還有一個方法能夠幫我完成這個事情。”
曲藝藝術是姜昆的最愛,他找到了網絡這種新的傳播途徑。他認為,相聲從出生到現在,每天都在變化創新,如果沒有創新,這種藝術走不到今天。隨著時代改變,人們的語境發生了改變,人們的欣賞口味也發生著變化,所以相聲也必須發生變化。相聲有時代性,要時刻面對觀眾,接受觀眾和市場的檢驗。無論在國內劇場中,還是在國外舞臺上,或者是與網友的交流中,姜昆發現,在曲藝藝術的氛圍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并不那么遙遠,有很多情感是全世界共通的。他說,“我在國外演出,觀眾都會笑,現場氣氛很好,說明交流還是可以實現的。”
曲藝有著獨特的魅力,時代改變,但是人們對曲藝的喜愛沒有變。交流方式在增加,但是人們并沒有舍棄曲藝這種人與人溝通的形式。這些讓姜昆對曲藝的未來一直都抱有信心。或許正是這份信心,讓他每天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態,能夠一直對探索、創新保持著孜孜不倦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