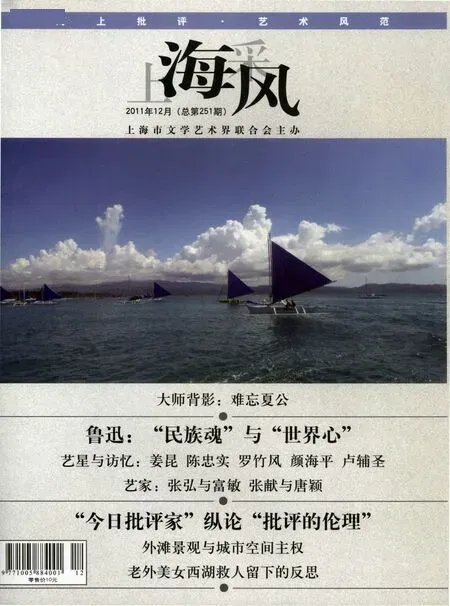顏海平:從《秦王李世民》開(kāi)始的“舊邦新命”寫(xiě)作
文/本刊記者 楊 子


顏海平
1982年畢業(yè)于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1983年底赴美國(guó)康奈爾大學(xué)攻讀歐洲現(xiàn)代戲劇、比較文學(xué)和批評(píng)理論專(zhuān)業(yè),1990年獲博士學(xué)位。現(xiàn)為美國(guó)康奈爾大學(xué)藝術(shù)與人文終身教授,兼華東師大紫江教授。2011年上海首批千人計(jì)劃特聘專(zhuān)家,任上海交通大學(xué)講習(xí)教授。1999年美國(guó)廣播電視公司(CNN)以其在英語(yǔ)和漢語(yǔ)世界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和創(chuàng)造性著述將她評(píng)為“新世紀(jì)最具有跨國(guó)影響力的六位中國(guó)文化人物之一”。入選《二十世紀(jì)杰出學(xué)者錄》(英國(guó);2000年)、《美國(guó)杰出女性錄》(美國(guó);2004年);歷任全美戲劇文化與婦女問(wèn)題研究協(xié)會(huì)主席、全美戲劇文化研究協(xié)會(huì)常務(wù)理事、年度最佳學(xué)術(shù)著作獎(jiǎng)評(píng)審委員會(huì)委員、高等教育戲劇學(xué)科及研究和出版委員會(huì)委員。早年發(fā)表十幕歷史話劇《秦王李世民》,獲1980—1981年全國(guó)優(yōu)秀劇本一等獎(jiǎng)。主要英文書(shū)著包括《戲劇與社會(huì):當(dāng)代中國(guó)戲劇選》《別樣的跨國(guó):散居的亞洲及其表演藝術(shù)審美》《中國(guó)現(xiàn)代女性作家和女性主義想象:1905—1948》等。中譯本《中國(guó)現(xiàn)代女性作家與中國(guó)革命》2011年6月由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1983年10月,顏海平到朱東潤(rùn)先生寓所探望恩師。朱先生在師友瑯琊行館題下書(shū)法條幅一幅,作為送給學(xué)生出國(guó)前的禮物。告別時(shí),朱先生從樓上送到樓下,直到門(mén)外的草坪。
顏海平至今記得,她走出一段,回過(guò)頭去,看見(jiàn)朱先生依舊站在原地。看見(jiàn)他回頭,便揚(yáng)起手揮一揮。“也許是太年輕,那時(shí)我根本沒(méi)有意識(shí)到他已經(jīng)88歲高齡。他題寫(xiě)的是蘇東坡的一首詩(shī),‘兩本新圖寶墨香,尊前獨(dú)唱小秦王。為君翻做歸來(lái)引,不學(xué)陽(yáng)關(guān)空斷腸’。浩瀚無(wú)邊的中國(guó)古詩(shī)里他挑了這一首,而且這么貼題,是囑咐我,要記住祖國(guó)。”
1982年夏天,復(fù)旦大學(xué)77級(jí)中文系畢業(yè)后,顏海平憑著優(yōu)異的學(xué)業(yè)成績(jī)留校任教。接著,人生發(fā)展中的三個(gè)抉擇降臨面前:“師從朱東潤(rùn)先生學(xué)習(xí)傳記文學(xué)的研究;師從南京大學(xué)的陳白塵先生繼續(xù)戲劇創(chuàng)作;第三是出國(guó)留學(xué)。”顏海平最終選擇了出國(guó)留學(xué)。
少年心事當(dāng)擎云
某種程度上,由于時(shí)間上的歷史性轉(zhuǎn)折及人們從十年內(nèi)亂桎梏壓抑中解放思想的訴求,復(fù)旦大學(xué)77級(jí)中文系成就中國(guó)文壇諸多“第一”,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的一個(gè)特別符號(hào)。最先是盧新華的短篇小說(shuō)《傷痕》被張貼在中文系四號(hào)樓走廊7711班級(jí)墻報(bào)上,在校園里引起廣泛討論,其后,小說(shuō)被《文匯報(bào)》的一位編輯注意到,發(fā)表在《副刊》上,《傷痕》很快走出復(fù)旦園,引起全國(guó)性的爭(zhēng)論。1978年秋天,在復(fù)旦校園舉辦的討論會(huì)上,與會(huì)師生辯爭(zhēng)激烈。在復(fù)旦中文系教師吳中杰發(fā)表了批評(píng)意見(jiàn)之后,本科一年級(jí)學(xué)生顏海平站出來(lái),表達(dá)了不同看法,支持盧新華的小說(shuō)。會(huì)后,吳中杰來(lái)到學(xué)生宿舍時(shí),對(duì)這位帶著稚氣的圓臉女生表示贊許,“雖然你的意見(jiàn)和我相左,但女孩子勇敢說(shuō)話,好!”
顏海平更為公開(kāi)的一次“勇敢說(shuō)話”是在兩年半后。1981年1月,她于1979年3月開(kāi)始構(gòu)思、1980年夏天完稿的十幕歷史話劇在《鐘山》雜志發(fā)表,“震驚了整個(gè)中國(guó)劇壇”。李世民的興兵反隋、建唐立國(guó)等系列跌宕起伏的歷史事件,在顏海平筆下以一種“精致典雅的語(yǔ)言”及“創(chuàng)新的舞臺(tái)技巧”呈現(xiàn)出來(lái),這部探索“君位與民意的關(guān)系”的歷史劇,以其深刻的主題、早慧的作者、及其對(duì)歷史題材的深度把握引發(fā)了文化評(píng)論界的熱議。1981年春天,上海青年話劇團(tuán)導(dǎo)演胡偉民將此劇搬上舞臺(tái)。其后,該劇獲得1981—1982年中國(guó)戲劇家協(xié)會(huì)、中國(guó)文化部所授予的全國(guó)優(yōu)秀劇本一等獎(jiǎng)。
直至今日,顏海平仍然認(rèn)為歷史劇寫(xiě)作和寫(xiě)歷史劇的時(shí)代之間,存在著一種豐富多重相互作用的關(guān)系。她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時(shí)是想通過(guò)“對(duì)歷史的一次重訪,針對(duì)民族虛無(wú)主義的問(wèn)題,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現(xiàn)代性的可能。”這部受人矚目的劇作,似乎預(yù)示著作者日后在中美學(xué)界作為一名探尋中國(guó)文化現(xiàn)代之路的史學(xué)者的開(kāi)端。
少年心事當(dāng)擎云。1981年8月,顏海平在《秦王李世民》單行本序言中以“精衛(wèi)鳥(niǎo)”自喻,為自己看似頗為“平淡”的名字尋找意義。她引用唐詩(shī)人王建《精衛(wèi)詞》中的一句“高山未盡海未平,愿我身死子還生”,表達(dá)自己要像“弱小而倔強(qiáng)的精衛(wèi)鳥(niǎo),孜孜不倦、一木一石地奠造理想大廈的根基”。30年后,當(dāng)被問(wèn)及對(duì)自己這段文字的看法,顏海平停頓片刻,笑了起來(lái),“有一句希臘名言說(shuō),人的起步和結(jié)束是有內(nèi)在關(guān)系的。黑格爾又說(shuō),一個(gè)年輕人和一個(gè)有經(jīng)歷的人,引用同一句格言時(shí),內(nèi)涵是完全不同的。人無(wú)法預(yù)知自己的未來(lái),所以也無(wú)法評(píng)價(jià)自己當(dāng)時(shí)或者說(shuō)過(guò)去的文字。”
1983年,顏海平考取公費(fèi)留美,同時(shí)獲得包括康奈爾大學(xué)在內(nèi)的三所大學(xué)的獎(jiǎng)學(xué)金。帶著復(fù)旦大學(xué)謝希德校長(zhǎng)和中文系系主任朱東潤(rùn)先生的支持和鼓勵(lì),顏海平開(kāi)始了“萬(wàn)里之行”。在兩位先生看來(lái),跨出國(guó)門(mén),“看到世界的狀態(tài),才能感受到、認(rèn)識(shí)到我們可以怎么做,我們必須怎么做,我們應(yīng)當(dāng)怎么做。”朱先生親筆題寫(xiě)的書(shū)法條幅跟隨顏海平越過(guò)重洋,現(xiàn)今被安放在她上海居所的書(shū)房里。

從不可見(jiàn)到可見(jiàn)
“我很欣賞這個(gè)設(shè)計(jì)。”顏海平用手指在靛青色的封面上劃了一條弧線,最后停頓在與紅五角星交疊的紅色玉蘭花圖案上。在康奈爾大學(xué)一年學(xué)術(shù)假期中,已過(guò)去的十個(gè)月,她是在國(guó)內(nèi)繁忙的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和教學(xué)研究工作中度過(guò)的。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這十個(gè)月能夠連續(xù)不斷地、長(zhǎng)時(shí)間近距離感觸中國(guó)和每日發(fā)生的變化,“是個(gè)很深的磨練和體會(huì)”。最近,作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入選上海首批“千人計(jì)劃”,意味著她將被正式引進(jìn)回國(guó)。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間,她頻繁往來(lái)中美兩地,與華東師大、清華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南京大學(xué)、上海交通大學(xué)等院校皆有不同方式的合作與交流。
今年6月,她著述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女性作家與中國(guó)革命(1905—1948)》一書(shū)中文版由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該書(shū)英文精裝版于2006年3月由紐約勞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付梓出版。在這部被學(xué)界同行稱(chēng)為“目前讀到的最為經(jīng)典的一部關(guān)于女性解放和女性寫(xiě)作的史詩(shī)性文獻(xiàn)”的著作中,顏海平深入探討了秋瑾、冰心、王瑩、白薇、蕭紅、丁玲等女作家的寫(xiě)作與生活,將她們的寫(xiě)作史和社會(huì)史相結(jié)合,通過(guò)講述 “弱國(guó)、弱勢(shì)、弱女子”再造人生的故事,指向一種生命形態(tài)氤氳發(fā)生的進(jìn)程史;以對(duì)“強(qiáng)”與“弱”的辯證法深厚有力的把握,重訪現(xiàn)代女性的革命性寫(xiě)作,重訪“現(xiàn)代中國(guó)”。
顏海平對(duì)1905年到1948年期間中國(guó)具有開(kāi)創(chuàng)性且影響久遠(yuǎn)的女作家的書(shū)寫(xiě),緣于“在國(guó)際環(huán)境中,感到長(zhǎng)期以來(lái)中國(guó)女性作家被認(rèn)知的程度非常不夠,中國(guó)整個(gè)現(xiàn)代文學(xué)和文化被認(rèn)知的程度非常不夠,其中涉及到認(rèn)知方法和路徑的問(wèn)題”。十年三易其稿的過(guò)程,也是她親身體驗(yàn)在國(guó)際環(huán)境下,“中國(guó)”的一切,如何歷經(jīng)從被冷戰(zhàn)思維所主導(dǎo)的視角與敘事所掩蓋而“不可見(jiàn)”的狀態(tài),走向“可見(jiàn)”的可能。這是一個(gè)漫長(zhǎng)摸索的過(guò)程,也是一個(gè)敞開(kāi)的實(shí)踐過(guò)程。將“不可見(jiàn)”的事物轉(zhuǎn)為“可見(jiàn)”的人生的人文敘述,見(jiàn)證了她嘗試突破歐美中心主義的文化想象、機(jī)制構(gòu)建和思維定勢(shì),超越冷戰(zhàn)邏輯下區(qū)域研究的慣性常規(guī)的一次認(rèn)知實(shí)踐;與她同時(shí)出版的關(guān)于歐洲和第三世界文化現(xiàn)象的著述一起,構(gòu)成她探索進(jìn)入美國(guó)主流學(xué)界的學(xué)術(shù)路徑。
在作者筆下,精衛(wèi)鳥(niǎo)的喻像在女性作家的文學(xué)與日常生活中不斷重現(xiàn),仿佛在示意作者自身30年時(shí)光砥礪打磨的“歷史連貫性”。在2009年夏天于上海舉辦的一次中美學(xué)術(shù)會(huì)議上,上海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陳青山用“一以貫之”來(lái)定位她,“從《秦王李世民》中對(duì)以人為本的主題關(guān)切,到出國(guó)后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過(guò)程中,對(duì)以民生為重、民族復(fù)興的關(guān)切,她的思維邏輯在學(xué)術(shù)生涯里是一以貫之的。”
顏海平自己也承認(rèn),走到今天,確實(shí)是按照內(nèi)心的一種呼喚一路走來(lái):父母作為抗戰(zhàn)期間南京中央大學(xué)的學(xué)生,在整個(gè)中華民族面臨深重危機(jī)時(shí)投入地下革命工作,從浙江一路輾轉(zhuǎn)走遍整個(gè)中國(guó)。家庭的影響鐫刻在童年、少年的成長(zhǎng)時(shí)光中,成為一種內(nèi)心的“歷史連貫性”。在她的書(shū)寫(xiě)——無(wú)論是文學(xué)性或?qū)W術(shù)性的文字——中保持對(duì)祖國(guó)的一份堅(jiān)守,身居海外多年依舊保留中國(guó)護(hù)照,這些只是“歷史連貫性”的一個(gè)個(gè)具象表現(xiàn)而已。
從八十年代初的“尊前獨(dú)唱小秦王”,到當(dāng)下對(duì)全球劇變時(shí)代中國(guó)大問(wèn)題的關(guān)切,三十年的書(shū)寫(xiě)歷程,顏海平援引冰心的母親說(shuō)過(guò)的一句話加以概括,“一個(gè)人的文字,關(guān)乎一個(gè)人命運(yùn)。”她呈之于眾的文字的核心意旨可歸納為“舊邦新命”四個(gè)字。用她的話來(lái)說(shuō),這里的“新命”,就是在全球化的歷史境遇中,探索如何主動(dòng)地包容和超越既定的現(xiàn)代認(rèn)知體系,有效地把握、處理對(duì)“現(xiàn)代中國(guó)”的文化敘述及想象更新。
記者:大學(xué)時(shí)代創(chuàng)作十幕歷史話劇《秦王李世民》,當(dāng)時(shí)的創(chuàng)作初衷是什么?
顏海平:文革剛結(jié)束時(shí)的民族虛無(wú)主義是個(gè)社會(huì)問(wèn)題,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現(xiàn)代是從五四時(shí)期的德先生賽先生開(kāi)始界定的。我記得當(dāng)時(shí)我的問(wèn)題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中有沒(méi)有內(nèi)在活躍的現(xiàn)代元素,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中,有沒(méi)有自己指向現(xiàn)代的資源。我想到唐太宗和他的時(shí)代,在大唐盛世的傳統(tǒng)文化中有哪些現(xiàn)代性的可能。當(dāng)時(shí)有不少公演的關(guān)于李世民的戲曲,主要是談唐太宗和魏征的關(guān)系。我在閱讀史料過(guò)程中,覺(jué)得還有更根本的思路。讀史料的過(guò)程也是一個(gè)發(fā)現(xiàn)過(guò)程,不是理念先行,也不是純粹直接的借古喻今,實(shí)際上是求對(duì)歷史的重新發(fā)現(xiàn)進(jìn)而重新把握。
記者:為什么采用話劇,而不是小說(shuō)或者其他文學(xué)樣式?

《秦王李世民》劇照
顏海平:我從小喜歡戲劇,這和父親的影響有關(guān)。幼時(shí)父親帶我去看話劇《南方來(lái)信》,演出結(jié)束了,別人都走了,我卻不肯走。現(xiàn)代歷史劇說(shuō)到底是對(duì)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性的更新和傳承,一方面是歷史記憶的再呈現(xiàn),另一方面,其呈現(xiàn)的根本形式已經(jīng)是現(xiàn)代的了,歷史記憶即由此獲得現(xiàn)代轉(zhuǎn)化。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是對(duì)英國(guó)民族國(guó)家發(fā)展現(xiàn)代進(jìn)程的一種思考、把握、表達(dá)和贊美,這種含有多重內(nèi)容的贊美很深邃、很豐滿、很精致,它形成一套文化的創(chuàng)造、一種現(xiàn)代語(yǔ)言的誕生,而成為經(jīng)典。我喜歡如《桃花扇》這樣的歷史劇,包括古典的和現(xiàn)代歷史劇版本,這里有民族文化的淵源、傳承、變革,有民族生命記憶在起作用。當(dāng)時(shí),我非常急迫地渴望學(xué)習(xí)。文革結(jié)束不久,民族虛無(wú)主義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全盤(pán)否定,時(shí)代要求我們以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快速補(bǔ)課。學(xué)習(xí)可以通過(guò)各種途徑,和創(chuàng)作結(jié)合起來(lái),是強(qiáng)化學(xué)習(xí)和深化學(xué)養(yǎng)的方法之一。
記者:77級(jí)成為中國(guó)教育史、文學(xué)史上的一個(gè)特別符號(hào)。能否以劇作家及學(xué)者的雙重身份談?wù)?7級(jí)文學(xué)現(xiàn)象?
顏海平:我是改革開(kāi)放后第一批通過(guò)高考入學(xué)的,即77級(jí)。我們77級(jí)、78級(jí)、79級(jí)被稱(chēng)為“新三屆”。相比華東師大,我們復(fù)旦中文系還有相當(dāng)一部分人成為學(xué)者,如陳思和、周斌在復(fù)旦做教授,王云在上戲做教授,張勝友任出版社老總,同學(xué)中還有成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那時(shí)候我們和華東師大走得很近,記得趙麗宏當(dāng)時(shí)結(jié)婚沒(méi)有房子,我去過(guò)他住的一間暗乎乎的屋子,在這里他寫(xiě)出很多很美的散文和詩(shī)歌。九十年代陳思和和王曉明發(fā)起過(guò)人文精神大討論。華東師大中文系形成作家群,都值得感佩贊賞。我覺(jué)得無(wú)論是成為作家還是人文學(xué)者,在新聞出版或其他崗位,大家都沒(méi)離開(kāi)自己的根本宗旨,就是堅(jiān)守并促進(jìn)中國(guó)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兩者內(nèi)涵是一致的。
記者:文學(xué)創(chuàng)作需要感性,學(xué)術(shù)研究需要理性。從感性到理性的轉(zhuǎn)變,或曰感性與理性的合一,你如何把握感性與理性的界限和結(jié)合?
顏海平:我在美國(guó)求學(xué)時(shí)的導(dǎo)師Dominick LaCapra教授,是美國(guó)研究歐洲19世紀(jì)和20世紀(jì)思想史的第一人;美國(guó)文理院院士。師從于他,我全面進(jìn)入了一個(gè)不同文明體系的精神世界;同時(shí),從他那里,我觸摸到、領(lǐng)悟到、最終自覺(jué)開(kāi)拓的重要思想路徑,是如何批評(píng)地學(xué)習(xí)和處理西方思想傳統(tǒng)和人文經(jīng)驗(yàn)。我之所以能夠走出一條自己的學(xué)術(shù)路徑,和這樣的教授分不開(kāi)。如何把握理性和感性的界限和結(jié)合,這是個(gè)非常好的問(wèn)題。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方法的基本前提是研究者作為認(rèn)知主體研究對(duì)象:我研究的對(duì)象是客體,我是主體,這個(gè)關(guān)系不平等。尤其是在美國(guó)研究中國(guó)問(wèn)題,這個(gè)關(guān)系,哪怕意圖是好的,結(jié)果可能是偏的。從學(xué)理上說(shuō),我覺(jué)得對(duì)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邏輯需要有超越,這是一個(gè)理性的思考。學(xué)者和研究對(duì)象保持什么樣的距離,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的回應(yīng),是認(rèn)知的、審美的、政治的、最終是倫理的一個(gè)決定,你在多大程度把自己和它連起來(lái),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拉開(kāi)距離;我們其實(shí)說(shuō)到了比較深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及其各種具體方式的把握問(wèn)題。期待我們國(guó)內(nèi)的學(xué)界同行之間,在提升我們國(guó)際能力的歷史發(fā)展期,有更多討論這個(gè)話題的機(jī)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