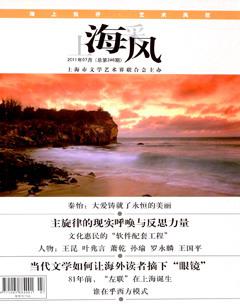以關愛的名義
千里光
看嚴歌苓的《霜降》有點像看李娜在法網打球,大力揮拍,每一下都往對方深處送,直打得底線一帶的那片紅土彈痕累累。夠狠,也夠精準。
如果說李娜的贏球意味著體制外的勝利,《霜降》的寫作和出版,大概也只有體制外的旅美作家嚴歌苓才有這么獨到的眼光和魄力了。
《霜降》說的是一個名叫霜降的農村女孩來到長征老紅軍程將軍家當保姆的故事。別以為這又是一部《黃山來的姑娘》(曾經的電影)的翻版、姊妹篇——不外乎先是小保姆怎么受挫,然后遇到好心人,最后終于靠著自己的努力和執著在大城市占得一席之地;如果寫愛情,則必是勤勞可愛的灰姑娘吸引了白馬王子的眼球,兩人合力,一舉打破傳統觀念的桎梏,沖破世俗眼光的藩籬,最后有情人終成眷屬,皆大歡喜……
基本的套路,一望而知的體制內的構思,萬變不離其宗。
《霜降》完全超越了我們的閱讀經驗。那位鄉村來的18歲的靚女霜降沒遇到過什么好心人,在她的周圍,不是判刑的罪犯就是聚眾淫亂的流氓,不是自以為是的紈绔子弟就是老吃老做的老色鬼,不是深宮怨婦就是啃老啃國的寄生蟲,不是兄妹戀的瘋子就是擅長鑒貌辨色的狗腿子……而這一切竟是發生在一個有衛兵站崗的將軍院里;要說有什么“白馬王子”,那基本上也都不是以婚姻為目的的追求者,也就是說都只是耍流氓。將軍院能這么寫,真讓我們開了一回眼界。
故事的規定情境很簡單:“還沒來得及學壞”的霜降第一次到北京,陰差陽錯地來到了一個有九個子女的將軍家里,很快遇到了三個喜歡她的男人……
這就好比一塊鮮肉,或是一只美味的小動物丟進了一只鐵籠里,那里等候著三只虎視眈眈的野獸,獅子,老虎,或是餓狼。
按常理,三只野獸必然你爭我奪,相互廝殺,斗個你死我活,魚死網破。小說這樣寫,當然在情理之中,那故事也是可以想象的環環相扣,跌宕起伏,高潮不斷。
但那樣寫,就不是嚴歌苓了。
嚴歌苓筆下的《霜降》恰恰是這三只獅子或老虎或餓狼,在見到霜降這塊鮮肉后,都不動聲色,沒有撕咬,沒有火拼,他們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大在乎,甚至不拿正眼去瞧一眼。
三個男人是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他們之所以都“不動聲色”蓋事出有因:
老六四星,因為走私、出賣情報等被判了重刑,雖說被其父保釋在家,但也基本失去自由,房間就是他的牢房,他被噤聲,只能靠霜降給他送飯或整理房間,才有機會搭訕。他只能是個悄悄說話的人。
老九大江,是個在讀博士,少校軍銜,他知道自己前程無量,而結門好親又是必要的條件,起碼要門當戶對。因為自己父親是農民出身,所以他壓根兒就瞧不起鄉下人,更不可能和一個鄉下女孩子結婚。他要霜降的身體,但在外人面前他要和她離得遠遠的,裝得渾身不搭界。
將軍,一家之主,也是院子外那個兵營的最高長官。盡管他明白自己影響式微,大不如前,但他還是每年“至少有四五次靠得住的機會去維持人們對他的記憶:第一是靠‘將軍櫻桃,第二是靠他的書法,第三是一年一度他在老人網球比賽中的表演。有沒有其它機會去提醒人們他的存在,那要看他是否能成功地惹下一件禍事或制造一件逸聞。”他當然不想為一個小保姆再鬧出什么丑聞,成為這“第N個機會”。然而,他也不輕言放棄,不能因為怕丑聞就什么也不做了,丑聞還是香聞,有時包裝很重要。
故事就在不動聲色中展開,平行的幾組人物關系,并沒有多大的沖突和糾葛,波瀾不驚。嚴歌苓幾乎就只是在不斷把握人物,把握人物性格,把握人物的走向。她照樣寫得絲絲入扣,引人入勝。那真是功力。
其實,小說可以說就是一門把握人物的藝術。嚴歌苓對人物的把握精準、傳神,入木三分,尤其她對將軍的刻畫,讓我們看到了她扎實的生活底子、通透的目光,而且文字又是那么靈秀,涵義幽微。
《霜降》最精彩的刻畫就是這位老將軍以“書法”的名義來調戲這位來自農村的小保姆。他要霜降到他這兒寫字,繼而研墨,再繼而在他浴缸里洗澡。命令式的口吻,容不得商量,更容不得違抗,卻都是關愛的名義。以關愛的名義上下其手,以關愛的名義吃豆腐。
這讓人不由想到前不久轟動一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卡恩在旅館強奸女清潔工一事。兩個差不多年齡的糟老頭,差不多的社會地位,都堪稱重量級的,可是卡恩只知道撒野,硬來,以至上了飛機還被抓回來。我估計卡恩是做夢也想不到吃豆腐還能找個崇高的名義。
嚴歌苓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榮獲了國內外各種重要文學獎項,相信《霜降》也會影響日隆,進一步鞏固她“國際嚴”的地位。
她12歲當兵,長期的兵戎生涯讓她熟知部隊,也熟知了“將軍”一類人富有中國特色的“以關愛的名義……”。不過我相信,如果嚴歌苓還在體制內,她未必能塑造出這么活靈活現的小說形象。就像李娜如果還在體制內,必定成不了國際娜一樣,我們需要更多的國際娜,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國際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