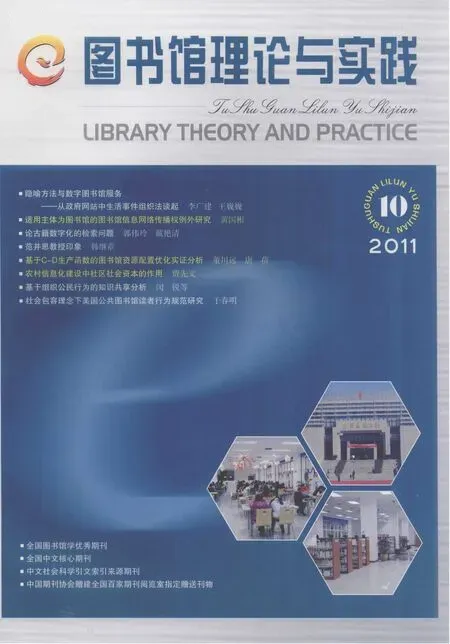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中社區(qū)社會資本的作用
●賈先文(湖南文理學(xué)院 經(jīng)管學(xué)院,湖南 常德 415000)
加快農(nóng)業(yè)信息化建設(shè)是促進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推進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村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增強農(nóng)業(yè)的市場競爭能力,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的重要舉措。但農(nóng)業(yè)信息化建設(shè)存在著困難,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可以有力地破解其困境,促進農(nóng)民合作以提高效率。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是指處于農(nóng)村社區(qū)內(nèi)的農(nóng)民,通過長期交往、合作互動形成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它能促進集體行動中的農(nóng)民合作,提高農(nóng)民整體利益,增進農(nóng)村社會進步。其中,信任、互惠規(guī)范、參與網(wǎng)絡(luò)是主要特征。[1]
1 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困境
為了促進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國家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推進農(nóng)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diào)要進一步搞好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和走有中國特色的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道路,積極發(fā)揮信息化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的作用。[2]從2005年到 2010年期間的一號文件都對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進行了強調(diào)。其中,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對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進行了最直接的表述:“推進農(nóng)村信息化,積極支持農(nóng)村電信和互聯(lián)網(wǎng)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健全農(nóng)村綜合信息服務(wù)體系。”
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穩(wěn)步健康地開展起來,信息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取得了一些成績。首先,農(nóng)村信息化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取得了進步。工信部在2010年完成了“村村通電話”工程,廣電總局也在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了“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其次,搭建了農(nóng)村信息采集和傳輸與服務(wù)平臺。目前我國涉農(nóng)網(wǎng)站達6389個。全國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已經(jīng)在260個地(市)設(shè)立了農(nóng)業(yè)信息服務(wù)機構(gòu),占地(市)總數(shù)的78%;77%的縣、47%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設(shè)置了農(nóng)業(yè)信息管理和服務(wù)機構(gòu),培養(yǎng)發(fā)展了近11萬人的農(nóng)村信息員隊伍,2009年,農(nóng)村網(wǎng)民規(guī)模達到1.0681億,占整體網(wǎng)民的27.8%。[3]再次,農(nóng)村信息服務(wù)體系基本建立。全國農(nóng)業(yè)信息體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已經(jīng)進入到良性發(fā)展階段。
但是我國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起步較晚,還存在著很多制約因素,尤其是政府只是單方面的努力,農(nóng)民參與不夠,沒有充分利用農(nóng)村豐富的社會資本,影響了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進程。
1.1 信息資源采集困難,供給結(jié)構(gòu)不能滿足農(nóng)村的需求
我國農(nóng)村地域廣闊,各地生產(chǎn)、生活差別較大,對信息的需求也不一樣。而政府的單方面的信息化行為,缺乏農(nóng)民的配合,沒有對農(nóng)村進行認真的調(diào)研,或者是調(diào)研中缺少農(nóng)民的支持而使得信息失真;農(nóng)村信息量不夠,信息采集困難,規(guī)范化程度不高,所提供的信息資源數(shù)量與結(jié)構(gòu)不合理,無法滿足農(nóng)民的需要。我國各地雖有一些涉農(nóng)網(wǎng)站,但是這些網(wǎng)站大多都是綜合性的信息多,專業(yè)性的信息少;交叉重復(fù)的多,有特色的少;特別是廣大農(nóng)民迫切需要的帶有地區(qū)差別的農(nóng)產(chǎn)品供求、價格、未來價格預(yù)測及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風(fēng)險預(yù)警等方面的信息嚴重缺乏,不能較好地分析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市場狀況,使一些農(nóng)業(yè)信息對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不具有指導(dǎo)性。
1.2 信息化供給中存在免費搭車,供給與需求“雙不足”現(xiàn)象嚴重
農(nóng)村信息服務(wù)具有公共產(chǎn)品的特性,而公共產(chǎn)品的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意味著消費主體可以免費搭車,可以無償?shù)厝〉煤锰帲鴱哪撤N意義上來說,這使公共產(chǎn)品的付費者就蒙受了外部不經(jīng)濟性的損失,使私人成本收益和社會成本收益出現(xiàn)了差異,邊際私人收益小于邊際社會收益,而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存在著大量享受信息公共產(chǎn)品而不分擔(dān)其成本“搭便車”現(xiàn)象。從而造成信息的需求與供給雙不足。如下圖,居民購買信息的邊際私人收益為MR1,居民的購買、消費給其他人和社會帶來好處,因而社會邊際收益MR2大于居民私人邊際收益MR1。購買信息的私人邊際成本為MC1,邊際社會成本為MC2,私人邊際成本 (MC1) 大于社會邊際成本(MC2)。正因為信息化的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消費者都存在“免費搭車”的心理,希望他人購買、消費而自己享受利益,出現(xiàn)了大量的需求不足。按照MC=MR的原則確定公共服務(wù)的最佳均衡量Q1和Q2,結(jié)果是私人的最佳購買量Q1小于社會最佳需求量Q2,出現(xiàn)“需求不足”現(xiàn)象。正因為信息服務(wù)需求不足,所提供的服務(wù)會出現(xiàn)供給剩余。這樣,在下一次供給中,供給者會根據(jù)私人邊際收益與私人邊際成本來調(diào)整信息服務(wù)的供給數(shù)量,從而,使得信息服務(wù)的供給數(shù)量Q1小于社會最佳需求量Q2。從而,造成所提供的信息服務(wù)偏離社會最優(yōu)狀態(tài),導(dǎo)致需求不足與供給短缺“雙失靈”現(xiàn)象。

圖 信息化供給與需求“雙不足”
1.3 投資渠道單一,信息難以進村入戶
雖然政府出臺了政策,啟動了農(nóng)業(yè)信息化工程,但是由于大多地區(qū)農(nóng)業(yè)信息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農(nóng)業(yè)信息體系建設(shè)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農(nóng)村信息服務(wù)體系。由于政府單方面的投入,沒有有效地利用社區(qū)農(nóng)民固有的聲譽機制、信任機制、網(wǎng)絡(luò)機制來促進農(nóng)民的投入,或通過農(nóng)民的網(wǎng)絡(luò)獲得其他民間投入,使得政府對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資金扶持力度不夠,民間資金又沒有引入,資金難以滿足需要,尤其是村集體缺少發(fā)展公共信息服務(wù)專項資金支持,使得信息傳輸網(wǎng)絡(luò)不夠暢通,存在著“最后一公里”問題。另外,獲取信息手段單一。目前農(nóng)村主要通過電視、電話、集市和鄰里傳播等傳統(tǒng)工具獲取信息,而效率極高的計算機由于電纜設(shè)施投入不到位而無法利用,普及率低,使得農(nóng)民無法獲取某些農(nóng)業(yè)網(wǎng)站為農(nóng)民朋友提供的一些種植、養(yǎng)殖技術(shù)和致富的好經(jīng)驗。
1.4 農(nóng)民整體素質(zhì)不高,缺乏信息技術(shù)應(yīng)用技能
信息化的關(guān)鍵在于應(yīng)用,在于具備應(yīng)用信息化的能力。我國農(nóng)村雖然也出現(xiàn)了信息素質(zhì)比較高的農(nóng)民,但畢竟是少數(shù),他們主要是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村干部、經(jīng)營人員、種植及養(yǎng)殖大戶、農(nóng)民經(jīng)濟合作組織的帶頭人、村辦企業(yè)的管理及業(yè)務(wù)骨干等,而農(nóng)民整體素質(zhì)不高,農(nóng)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農(nóng)民對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了解不多,信息化意識和利用信息的能力普遍不強,嚴重地影響了信息技術(shù)的推廣和應(yīng)用。另外,農(nóng)村信息化發(fā)展過程中專門人才嚴重缺乏。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對專業(yè)人員素質(zhì)的要求有別于其他信息行業(yè),它需要既懂農(nóng)業(yè),又要熟練掌握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等各種信息工具的“復(fù)合型”人才,但農(nóng)村條件較差,農(nóng)業(yè)信息化專門人才不愿下到農(nóng)村,需要政府在加強對農(nóng)村信息技術(shù)人才培養(yǎng)的同時,利用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吸引此方面的人才。
1.5 農(nóng)民參與不夠,信息化效力難以發(fā)揮
政府憑借其壟斷地位,在缺乏農(nóng)村社區(qū)參與的情況下,按照政府勾畫的信息化藍圖大力推進農(nóng)村信息化,按照統(tǒng)一僵化的模式對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進行規(guī)劃,脫離農(nóng)村的實際情況,使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規(guī)劃無法適應(yīng)當(dāng)?shù)貙嶋H需要。同時,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政策不健全,引導(dǎo)、調(diào)動農(nóng)民群眾參與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積極性的政策缺乏。另外,政府信息化建設(shè)的監(jiān)督、執(zhí)行成本高,尋租現(xiàn)象嚴重。這影響了信息化效力的發(fā)揮,信息化效率低下。
2 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對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困境的破解
利用農(nóng)村“熟人社會”,利用農(nóng)村社區(qū)固有的信任、規(guī)范、網(wǎng)絡(luò)、聲譽等社會資本,可以破解農(nóng)村信息化困境,促進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
2.1 改變信息供給結(jié)構(gòu)
我國農(nóng)村面積遼闊,人口眾多,農(nóng)民的信息需求多樣化,須在了解農(nóng)民的需求偏好,得到農(nóng)民支持的基礎(chǔ)上,因地制宜地搞好信息化建設(shè),提供農(nóng)民需要的信息。但是,從原子化的、高度分散的單個農(nóng)村居民中得到準確的需求信息非常困難,偏好顯示成本大。由于存在免費搭車心態(tài),農(nóng)村居民會設(shè)法掩飾自己的偏好,造成搜索成本相當(dāng)高,所搜索的信息存在失真,易造成信息供需數(shù)量或結(jié)構(gòu)失衡。如果將信息搜索縮小到社區(qū)范圍內(nèi),利用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有利于了解農(nóng)村居民對信息產(chǎn)品需求的數(shù)量、質(zhì)量及結(jié)構(gòu)等,尤其是社會網(wǎng)絡(luò),就如一根線將單個農(nóng)民串起來,農(nóng)民單個的偏好顯示變?yōu)榱思w偏好顯示,可以防止農(nóng)民個體表達失真,也可以減少需求表達不暢以及供需失衡的摩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提供了農(nóng)民所需要的信息,提高了農(nóng)民的滿意度,使信息化建設(shè)得到農(nóng)民的支持。[4]
2.2 吸引民間資金對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投入
資金瓶頸是困擾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重大問題。我國農(nóng)村面積大、人口多,政府無足夠的資金投入到信息化建設(shè),市場天然的趨利性也決定了其在農(nóng)村信息化等公共產(chǎn)品供給方面的作用極其有限。為此,可以利用社區(qū)社會資本,提供包括農(nóng)村信息服務(wù)等公共產(chǎn)品。利用信任、網(wǎng)絡(luò)、聲譽機制促進籌措資金。由于外出流動人口增加,農(nóng)民的網(wǎng)絡(luò)半徑不斷擴大,有些村就利用農(nóng)民擴大后的網(wǎng)絡(luò)在春節(jié)期間乘其返鄉(xiāng)探親時發(fā)動捐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信息化建設(shè)開展得較好的幾個村,社會捐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電腦的提供、電纜的拉通、機房的修建、網(wǎng)站的建設(shè)等等就是本村外出務(wù)工人員、企業(yè)家或者在政府重要部門工作的人員出資修建的。而臨近一些村信息化設(shè)施的明顯差別,原因就在于社會網(wǎng)絡(luò)等社區(qū)社會資本的巨大差異。擁有資源多、網(wǎng)絡(luò)廣的村能得到更多的資源,相應(yīng)的信息化設(shè)施更加完善。
2.3 破解免費搭車困境,促成農(nóng)民合作
既然信息服務(wù)是公共產(chǎn)品,就存在免費搭車的集體行動困境。許多學(xué)者(如奧爾森、康芒斯、布坎南、哈丁)都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集體行動問題。實際上,這些精辟的巨作過多地考慮了人們的理性,沒有考慮到非理性的因素,如制度、道德,以及規(guī)范、信任、網(wǎng)絡(luò)、聲譽等社會資本對信息等公共產(chǎn)品供給制度的作用。如果將制度嵌入到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中,利用制度的規(guī)范約束力,結(jié)合社區(qū)社會資本等強大的非正式力量,特別是利用農(nóng)村“熟人社會”,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避免集體困境,形成合作博弈。正如美國著名學(xué)者奧爾森所言:當(dāng)個人為集團利益作貢獻的經(jīng)濟激勵缺乏時,多數(shù)人所看重的是朋友和熟人間的友誼以及自尊、個人聲望和社會地位,這可能會激勵他們?yōu)榧瘓F利益而合作、出力。[5]
奧爾森所言的正是社會資本,它是破解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集體行動困境的重要手段,這已取得了人們一致的認同。不可否認,我國農(nóng)村社區(qū)風(fēng)俗習(xí)慣、倫理道德、家法(宗法)、村規(guī)民約等社會資本是配置資源的重要力量,也是克服“免費搭車”的重要途徑。農(nóng)村居民在長期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習(xí)慣、習(xí)俗和意識形態(tài)是社區(qū)居民的行為規(guī)范。若居民違反規(guī)范而“越軌”,社區(qū)居民群體將利用參與網(wǎng)絡(luò)機制、信任機制、互惠規(guī)范機制來進行懲罰或使之邊沿化。由此可見,社會資本能推動協(xié)調(diào)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破解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集體行動困境,提高農(nóng)民整體利益,促進農(nóng)村社會的進步。
2.4 有利于信息化建設(shè)的監(jiān)督執(zhí)行
政府單方面的信息化建設(shè),監(jiān)督、執(zhí)行困難或者是監(jiān)督、執(zhí)行成本非常高。正確利用社會資本有利于信息化建設(shè)的監(jiān)督執(zhí)行。首先,政府單方面供給農(nóng)村信息服務(wù)的成本居高、效率低下,信息化建設(shè)政策執(zhí)行困難,這增加了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成本。利用社區(qū)社會資本,利用農(nóng)民之間千百年來的信任、規(guī)范、網(wǎng)絡(luò),通過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優(yōu)勢,使信息化建設(shè)得到落實,也可整合社會資源,提高信息化產(chǎn)品供給的效率。其次,政府單方面供給農(nóng)村信息化產(chǎn)品行為難以監(jiān)督或監(jiān)督成本居高。由于信息不對稱、缺乏監(jiān)督,道德風(fēng)險和代理風(fēng)險在信息化建設(shè)過程中會出現(xiàn)。社會資本以“地緣”“血緣”“業(yè)緣”為基礎(chǔ),利用社區(qū)社會網(wǎng)絡(luò)、信任、聲譽機制來監(jiān)督信息服務(wù),大大降低了信息化建設(shè)的成本,提高了信息供給效率。
2.5 提高農(nóng)民的信息技術(shù)能力
如前所述,農(nóng)村信息化過程中,農(nóng)民的信息技術(shù)的應(yīng)用處理能力是信息化建設(shè)成敗的關(guān)鍵。而社會資本能提高農(nóng)民的信息技術(shù)能力。大多數(shù)學(xué)者均認同社會資本促進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促進信息化的演進道路。[6]
3 提升社會資本促進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政策建議
3.1 激活農(nóng)村社區(qū)傳統(tǒng)性社會資本,促進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農(nóng)民合作
建立在傳統(tǒng)的血緣、地緣等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上的信任、慣例、習(xí)俗、規(guī)則等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在農(nóng)村社區(qū)公共產(chǎn)品供給中曾經(jīng)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因而,應(yīng)該激活和重建農(nóng)村社區(qū)傳統(tǒng)性社會資本,增強農(nóng)民間的相互信任和互惠合作精神,為促進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創(chuàng)造條件。政府應(yīng)該在此方面發(fā)揮積極作用。首先,發(fā)揮政府強大的教育功能,激活農(nóng)村傳統(tǒng)社會資本,促進信息化建設(shè)。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資源,通過宣傳、教育以及正確的輿論引導(dǎo),傳遞社會規(guī)則、規(guī)范,增加農(nóng)村社區(qū)信任、規(guī)范等社會資本,促進農(nóng)民積極參與社區(qū)信息化建設(shè)。其次,搞好政治文明建設(shè),恢復(fù)農(nóng)村社會的正義和信任。針對我國農(nóng)村社區(qū)信任減弱和合作減少的現(xiàn)實,政府應(yīng)加大政治文明建設(shè)的力度,在全社會提倡互信合作的風(fēng)尚,建立、健全制度并嚴格、公正地執(zhí)行制度以維護社會正義,增加農(nóng)民對政府的信任,增強農(nóng)民與政府的合作,最大程度地恢復(fù)農(nóng)村傳統(tǒng)型的社會資本,以利于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實現(xiàn)。最后,政府應(yīng)培育社區(qū)內(nèi)的互惠、合作精神,促成公民的互惠、合作,促進信息化建設(shè)的合作供給。
3.2 創(chuàng)建農(nóng)村社區(qū)制度性社會資本,激發(fā)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農(nóng)民合作
應(yīng)在激活傳統(tǒng)性社會資本的同時,創(chuàng)建農(nóng)村社區(qū)制度性社會資本。政府應(yīng)發(fā)揮重要作用,應(yīng)制定相應(yīng)的制度,通過制度來規(guī)范社區(qū)和個體,使農(nóng)村社區(qū)發(fā)展與農(nóng)民個人自由相融合,促進居民合作,遏制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免費搭車,減少交易成本;政府應(yīng)培育社區(qū)組織,并在經(jīng)濟與政策上給予支持,通過社區(qū)組織來規(guī)范農(nóng)民行為,增強農(nóng)民的集體意識,形成社區(qū)居民間相互信任合作、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及社區(qū)成員共同遵守的行為規(guī)范。另外,強化農(nóng)村自我管理意識,減少政府對農(nóng)村社區(qū)具體事務(wù)的干預(yù),發(fā)揮制度、契約、規(guī)則的作用。應(yīng)建立有效的監(jiān)督、評估機制,增強農(nóng)民對政府的信任,促進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農(nóng)民間以及農(nóng)民與政府間的合作,以社會資本帶動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的實現(xiàn)。
3.3 營造擴大農(nóng)村社區(qū)社會資本增量的環(huán)境,強化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農(nóng)民合作
研究表明,優(yōu)質(zhì)的社區(qū)環(huán)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促進社會資本的增加,從而促成信息化建設(shè)中的農(nóng)民合作的實現(xiàn)。為此,政府應(yīng)制定政策,提供安全、民主、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增強社區(qū)居民的交往,增加農(nóng)民對社區(qū)的認同感,使社區(qū)農(nóng)民對社區(qū)自己的事務(wù)有自由參與權(quán)、自主決策權(quán)及監(jiān)督權(quán);增加社區(qū)社會資本,提高居民參與信息化建設(shè)的積極性。同時,政府應(yīng)積極推動社區(qū)建設(shè),在專家及農(nóng)村居民的參與下,構(gòu)建良好的社區(qū)環(huán)境和農(nóng)民參與平臺,真正地把解決農(nóng)村的實際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努力促進居民的良性互動,增加信任與合作,增加公共精神與公共意識,增強農(nóng)村社區(qū)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促進信息化的合作供給。
[1] 羅倩文,王釗.社會資本與農(nóng)民合作經(jīng)濟組織集體行動困境的治理[J].經(jīng)濟體制改革,2009,(1):93互96.
[2] 張博,李思經(jīng).我國農(nóng)村信息化建設(shè)現(xiàn)狀及對策建議[J].中國農(nóng)業(yè)科技導(dǎo)報,2010,12(3):62互66.
[3]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設(shè)立農(nóng)村信息化新目標[EB/OL].(2010互02互05).http://www.itxinwen.com/View/new/html/2010互02/2010互02互05互1016061.html.
[4] 賈先文.兩極失范與農(nóng)村公共服務(wù)的社區(qū)化[J].現(xiàn)代經(jīng)濟探討,2010 (2):61互65.
[5] (美)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Academy ofManagement Review,1998(23):242互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