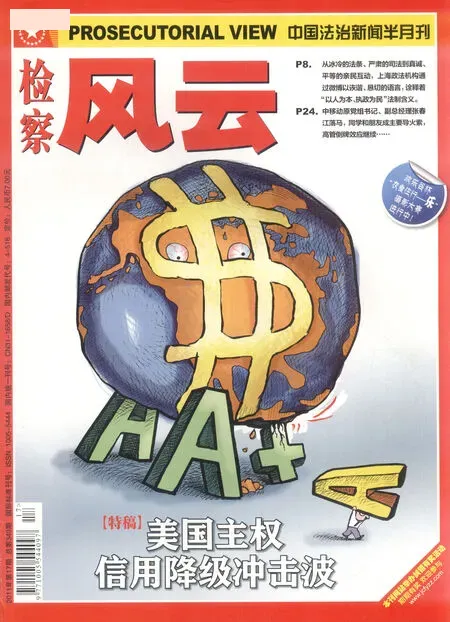《一分錢》兒歌背后的警民關系
文/魯兵
《一分錢》兒歌背后的警民關系
文/魯兵
兒歌大王潘振聲創作的《一分錢》兒歌,滋潤和啟迪了幾代少年兒童的心靈。十多年前,他將歌頌警民關系的兒歌《一分錢》手稿無償地捐獻給了上海公安博物館,他的舉動令征集作品的民警深為感動。
多年前,兒童節前夕收看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欄目,節目主持人朱軍為紀念剛故去的兒歌大王潘振聲老師,特意邀請了幾位兒歌作曲家和上海公安博物館的退休民警孫浩等人做節目。朱軍采訪孫浩時,他說起自己與潘振聲的交往,頗為動情,聲淚俱下。我被潘振聲老師的高風亮節和孫浩的真誠待人深深打動,并應約來到了孫浩家采訪。
尋覓《一分錢》詞曲作者
房門打開的一瞬,見站立眼前的白發男子竟然就是孫浩,令我感慨萬分。幾年不見,他似乎變了一個人,真讓人感嘆歲月無情。寒暄幾句后,我便切入正題:“兒歌大王潘振聲的《一分錢》兒歌手稿,你是怎么征集來的呢?”
說起潘振聲老人,孫浩直感嘆:“他真是一個好人!”感嘆后,孫浩向我娓娓道來——
孫浩原來在北京文化部音樂研究所工作,為了與妻子團聚調入了上海盧灣區越劇團。1992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被調入南市公安分局成了一名警察,從事宣傳工作。因為有點文藝細胞,他與同事搞起了廣播劇《真情歲月》,還獲得了文化部金盾文化工程一等獎。1997年,孫浩被抽調到建國西路394號,與宣傳處副處長俞烈一起籌建“上海公安俱樂部”。
1998年,孫浩在參與籌備上海公安博物館展品時,第一任公安博物館館長俞烈對孫浩說:“《一分錢》兒歌是描寫警民關系的音樂作品,我們都是聽著這首兒歌長大的。這首兒歌家喻戶曉,膾炙人口,而且誕生在上海。你是文藝界出來的,想辦法找到作者,向他征集這首兒歌的手稿。”
孫浩過去雖然從事過音樂研究,但中國之大,作曲家之多,他不可能都認識,一時沒了方向。為難之際,孫浩想起了原南市區區委書記李倫新正在上海市文聯當書記,找找他可能有戲。孫浩冒昧地給李書記打電話說明了緣由,李書記爽快地說:“這個沒問題,兩天后給你回音。”兩天后果然有位上海音樂家協會的同志給孫浩來了電話:“文聯的李書記讓我把《一分錢》的詞曲作者名字告訴你,他叫潘振聲,是我們上海人,原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工作,但是20世紀50年代他被調到寧夏去了,聽說現在是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的副主席。”

《一分錢》兒歌是描寫警民關系的音樂作品,盡管只是上交一分錢,卻傳達了“拾金不昧”的樸素價值觀。

《一分錢》兒歌滋潤了幾代少年兒童的心靈
孫浩得知《一分錢》詞曲作者的名字后,喜不自禁,立刻就有了尋找的方向。他立馬一個電話掛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對方熱情地告知,此人80年代已調入江蘇文聯任副主席。孫浩馬上又打電話到南京江蘇文聯,對方卻警惕地說:“電話里又看不到介紹信,怎么知道你是上海公安局的呢?”孫浩解釋說:“我告訴你電話號碼,你查一下就知道我打的是公安局的內線電話。”對方果然打來了電話,證明無誤后,才告知潘振聲家的電話。
孫浩激動地撥通了潘振聲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正是潘老師,他好奇地問:“你是哪位?”孫浩解釋說:“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們現在正在籌備公安博物館,大家都認為你創作的兒歌《一分錢》家喻戶曉,是警民關系的代表作,我們想征集這首兒歌的手稿,不知潘老師是否愿意獻出來?”潘老師聽后毫不猶豫地說:“你們上海公安籌建博物館,我贊成,我一定支持,我決定把《一分錢》兒歌手稿捐給你們。”孫浩興奮地說:“真是太感激了,我馬上到南京來取。”沒想到潘老師卻說:“你們不必來南京,我親自給你們送來。”孫浩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次得到潘老師證實后才掛了電話。
《一分錢》兒歌的創作過程
1998年12月21日,一個冬日的午后,俞烈館長與孫浩來到上海新客站接潘振聲老師,他們站在陽光下舉著大牌子,潘振聲老師走過來自報家門。俞館長與孫浩激動地將老人接到大滬飯店,時任政治部副主任應根寶特意趕來為潘老師接風洗塵,飯畢,應副主任對孫浩交待說:“你與潘老師談一下,如果對方提出知識產權問題,我們也應該予以適當的經濟補償。”
孫浩陪著老人來到客房,熱情地為老人沏茶,等潘老師一切安排妥帖后,他便開始與潘老師聊了起來。老人深情地向新認識的警察朋友聊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當年創作《一分錢》的經過。
潘振聲是上海人,1933年生于青浦縣,自幼酷愛音樂,在小學念書時就擔任學校合唱隊的指揮,抗日戰爭時期,他小小年紀就上臺指揮過《賣報歌》《大刀進行曲》《只怕不抵抗》等救亡歌曲。后因家境貧寒,只能輟學去當童工和報童。解放后,因為喜歡音樂,潘振聲考進了上海現代影劇演員學校,1950年畢業后,為了報黨恩,他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了一名炮兵,有次新兵連舉行文藝演出,潘振聲吹拉彈唱,樣樣都會,一場下來贏得滿堂喝彩。結果因文藝特長當上了師部的文藝兵。
1955年潘振聲復員后,民政局的同志見他是個文藝兵,便分配他到上海市漕溪路小學任音樂老師兼少先隊大隊輔導員。這年的春天,潘振聲嘗試性地創作了《我們來到了花園里》,歌聲很快飛出了校園,傳遍了上海。隨著他的兒歌創作的出名,1957年,潘振聲被調入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任音樂制作人。1958年,潘振聲創作了兒歌《小鴨子》,歌詞里有一句:“再見吧,小鴨子,太陽下山了。”有人指責他:“太陽下山是影射偉大領袖”,就這樣,潘振聲莫名其妙地被發配到邊區寧夏人民廣播電臺。

《一分錢》兒歌手稿而今已被公安博物館收藏
1965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小喇叭”節目組寫信給潘振聲向他約稿,請他創作一首表揚“好孩子”的歌。潘振聲一接到約稿信,馬上沉浸在了當年任音樂老師的往事回憶中。
潘振聲任少先隊大隊輔導員時,經常給孩子們上道德教育課,教育孩子們要愛祖國、愛社會、愛學習、愛勞動,要做個誠實的孩子。那時,他放在辦公桌上的大頭針小盒內,經常放滿了孩子們交來的一分、兩分硬幣,小孩子們拾金不昧的行為,常常觸動著他的心弦。雖是一兩分錢,但折射出孩子們美好純潔的童心。而當年在漕溪路口有位交通民警,不管是刮風下雨,還是酷暑嚴寒,他每天都護送孩子們過馬路。到了路口的另一邊時,懂事的孩子們總是回過頭來揮著小手,稚聲稚氣地叫著:“叔叔,再見……”并一再回頭目送著警察叔叔遠去的背影。這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潘振聲的腦海里。
這幕難忘的情景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潘振聲創作好孩子兒歌時,這一幕幕真實感人的情景又浮現在了眼前,他感到這是真切的往事,不能虛假,也不能成人化,曲調一定要讓孩子們易學易唱,那就要跳躍、優美。他白天冥思苦想,就是沒感覺。晚上躺在床上夜不能寐,望著天上的月亮,突然家鄉的滬劇紫竹調旋律跳入腦海,他立即爬起來擰亮臺燈,紫竹調的旋律旋即幻化成帶有城市色彩的明快旋律,經典兒歌《一分錢》就這樣誕生了。
兒歌一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就像插上了飛翔的翅膀,旋即飛向了大江南北,孩子們唱著兒歌去上學、去勞動、做好事。幾代兒童的心靈都受到了這首兒歌的滋潤和啟迪。
往事如煙也動情,孫浩聽著老人講述如煙的故事,心里激動不已,但是他心里還在擔心怎么與老人的協商收藏事宜。
孫浩戰戰兢兢地對老人提出:“潘老師,關于《一分錢》手稿的知識產權問題,你看怎么辦?”老人反應極快,他揮著手堅決地說:“孫浩,我是一個受過磨難的老共產黨員,我知道我的社會責任在哪里,我是共產黨的藝術家,上海要建共和國首座公安博物館,我舉雙手贊成,我堅決支持,我決定無償地捐獻給你們!”

上海公安博物館退休民警孫浩向記者展示《一分錢》兒歌的手稿
孫浩聽罷心頭一熱,眼睛有點濕潤。他豎起大拇指動情地說:“潘老師,我從心眼里敬重您老人家,不僅是因為您創作了一千多首兒歌,更是因為您作為老共產黨員的高尚人品!”
兒歌大王與警察的忘年交
有了這次特殊的工作聯系,孫浩認定了要交這位德藝雙馨的兒歌大王為朋友,每年他都會到南京買些禮品去探望這位令人敬重的老人。那年的夏天,孫浩去南京探望潘老時,他們就在潘老師樓下的飯館里吃飯,潘老師走路背有點彎,孫浩攙扶著他過了馬路。
吃飯時,孫浩向老人開玩笑:“您的兒歌是警察叔叔攙扶孩子們過馬路,現在卻是警察后生攙扶兒歌叔叔過馬路。”老人聽了沒有笑,卻辛酸地說:“我背彎曲是因為在寧夏時,那些造反派用鞭子抽的,他們用的是鋼絲鞭子。”老人掀起了自己的衣服給孫浩看,手上、背上還留有鞭印,孫浩無言,心里流淚。
老人講起了自己的往事:被“發配”到寧夏后,娶了一位女工,沒有生育,領養了一個女孩,“文革”時妻子離他而去……這頓飯吃得有點沉悶,老人說著說著念起了自己寫的打油詩,孫浩感到挺有意思,便讓潘老師寫下來,潘老師順手取出了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寫上了那首當年涂鴉的打油詩:
《我不哭》
童年家窮皮包骨,少年歲寒當學徒;
青年得志遭厄運,壯年有家不幸福。
老來伏案何所求,一生無愧大丈夫。
潘振聲作于1990年8月10日凌晨
孫浩接過寫在名片背面的打油詩,讀罷心里是五味俱全,為老人的坎坷一生而唏噓不已,也為老人的豁達大度而嘆服。
一來二往,兒歌大王與孫浩熟了,也認了這個知情重義的警察朋友。他們成了忘年交,老人每次來上海看姐姐,也會給孫浩打來電話,接到潘老師的電話,孫浩都去看望他。有一次,孫浩去他姐姐家告知《一分錢》的手稿被國家文物局評定為現代一級文物,老人聽罷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有一次,老人來上海,孫浩去看望他,這天他心情很好,聊起了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粉碎“四人幫”后,潘老又恢復了名譽,當上了寧夏文聯副主席和音樂家協會主席,后來調到了江蘇任省文聯副主席,不久,又任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潘老師的晚年生活總算安定了下來,他整天沉浸在兒歌創作中,形單影只,無暇顧及自己的生活,有熱心人為潘老師介紹了一位幼兒園的老師,他們一見鐘情,交往了幾次就結了婚,老人還有了兩個繼女,都對他很孝順,晚年的潘老生活得很幸福。

潘老師當年親筆題寫的打油詩令人讀來五味俱全
但他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依然熱心地為孩子們寫歌,他把花了多年時間嘔心瀝血寫成的56首各民族的兒歌,充滿信心地送到音樂出版社,人家卻要收費,而且是幾萬元。老人納悶地感嘆:“人家出20萬元收我的手稿,我都不要一分錢,我為孩子們寫歌,為啥這么難?”潘老有點想不通,便找到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著名作曲家徐沛東,徐主席曾給潘振聲頒發過音樂特別貢獻獎,潘老師還獲得過“五個一”工程獎,并且是唯一獲得過“金唱片獎”的兒歌作曲家,但是這些對于市場經濟、流行歌曲的大潮來說都無濟于事,這成了潘老師終生的憾事。
2004年,孫浩陪潘老師到中央電視臺制作《一分錢》的節目,公安部楊煥寧副部長的愛人特意請潘老師和孫浩到他家做客,楊部長特意拿出了存放多年的五糧液,他給潘老師斟滿酒深情地說:“我們都是聽著您的兒歌長大的,今天我代表全國的公安民警敬你一杯!”
不管潘老師走到哪里,只要提起《一分錢》《春天在哪里》《小鴨子》等兒歌,30歲以上的人都耳熟能詳,都會哼唱幾句,他們都會對這位老人表示自己的敬意。這讓潘老師感到欣慰。
潘老師晚年過著幸福的生活,孫浩每次去南京都會去探望他,見他們老夫妻相濡以沫,舉案齊眉,感到很欣慰。
未料,2009年2月,潘老師的妻子突然被查出胃癌,且已是晚期,潘老的精神被猛地一擊,他每天去醫院照顧老伴,由于身心疲憊,于3月突發腦溢血倒下了。孫浩聞悉潘老師病況,一個月里去了三次南京。第一次和第二次潘老師還腦子清楚,5月8日,孫浩第三次去探望潘老師時,他已深度昏迷,不能言語,孫浩在他的耳旁大聲說道:“潘老,你要堅強,全國3000萬的兒童還等著聽你的兒歌呢!”潘老師慢慢地蹺起大拇指,眼淚從他的眼角緩緩地流了下來。2009年5月14日,潘振聲老人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享年77歲。■
編輯:黃靈 yeshzhw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