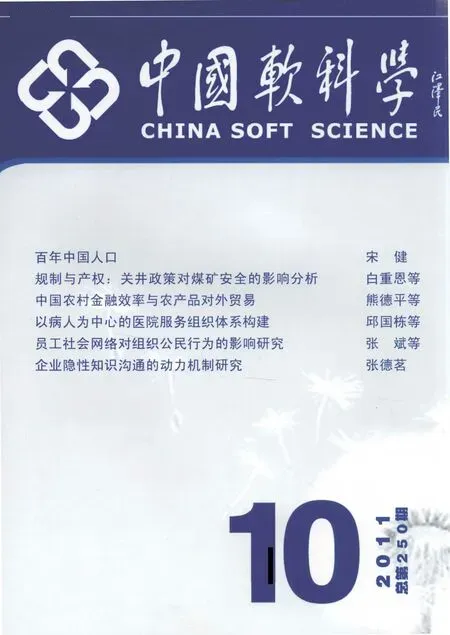我國植物新品種權走出去戰略探析:基于UPOV國際發展和競爭動向的視角
陳 超,張明楊,李寅秋,唐 力
(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南京210095)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各國發展經濟和參與國際竟爭的關鍵因素。有關知識產權和貿易關系的理論研究一直持續,Maskus和Penubarti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制造業出口量與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關系,結果表明,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對雙邊貿易產生積極的影響[1]。此后,Al-Mawali、Catherine、Falvey 等,也得出相同結論[2-4]。然而對于農產品貿易,由于自身存在剛性需求,受知識產權的影響不同于制造業,有關知識產權對農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尚未達成共識,但Perrin指出,如果知識產權沒有得到保護,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率幾乎不可能追趕上發達國家[5]。
植物新品種保護(plant variety protection,簡稱PVP),是WTO-TRIPS協議農業知識產權領域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①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農業領域里《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簡稱TRIPs協定)包括三個方面:地理標記、農產品的專利保護及植物新品種保護,其中植物新品種保護尤為重要。,與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標專用權一樣同屬于知識產權范疇。國家審批機關按照法律、法規,授予完成新品種選育單位或個人生產、銷售、使用該品種繁殖材料的排他權,以法律手段給予育種者充分的權益保障[6-7]。PVP制度的實施激勵育種創新,促進育種技術進步,加快種業集聚,提升種業的國際競爭力,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是農產品降低成本和創造差異的主要途徑。面對種子產業高成長性的誘惑,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積極研究并系統策劃進入種業,以生命科學為背景的種業重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跨國種業出于占領全球更大市場份額的需要,逐步構建一個全球范圍內的育種者創新權利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保障其盡可能獲得壟斷利益。因此,在貿易全球化的今天,誰掌握了品種權,就意味著在國際農產品競爭中占有有利地位。
本文基于UPOV聯盟植物新品種保護的國際發展和競爭動態,分析我國品種權保護現狀及我國優勢農產品出口貿易情況,構建我國品種權海外發展的戰略框架及實施路線,加強我國優勢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為我國品種權早日走出國門提供參考。
一、UPOV聯盟植物新品種保護的國際發展和競爭動向
國際上比較成熟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是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力推的 UPOV模式[8]。1961年《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在法國巴黎締結,1968年公約正式生效,標志著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這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正式成立,使植物新品種保護跨越國界。該公約經過1972、1978、1991年三次修改,逐漸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目前生效的有1978文本與1991 文本[9]。
(一)UPOV聯盟成員發展及履行文本類別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促使新品種保護快速發展,如圖1所示,UPOV聯盟由1999年的44個成員,發展至2009年68個成員。植物新品種保護已覆蓋四大洲,在現有的UPOV成員中,75%的成員來自歐洲和美洲,亞洲成員列居第三位,非洲成員僅有4位。UPOV成員逐步履行1991Act,至2004年,履行91Act成員首次超過78Act并不斷擴充。2009年UPOV聯盟中45個成員履行91Act,22個成員履行78Act,比利時仍履行由1972修改的61Act。歐洲除挪威、法國、愛爾蘭、意大利和葡萄牙以及亞洲除中國的所有成員均履行91Act,而美洲除美國、哥斯達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均履行78Act。非洲加入UPOV的成員國甚少,摩洛哥和突尼斯履行91Act,肯尼亞和南非使用的是78Act。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分別加入91Act和 78Act的行列中[10]。

圖1 UPOV成員及履行文本類別(個)
與78Act相比,1991Act最根本的區別表現為保護領域和保護范圍(特別是進出口)的擴大,農民自留種,實質性派生品種概念的引用及其商業化的規定①實質性派生品種的商業開發需要得到原品種權擁有人的授權。,四個方面。尤其是在第(1)款《與繁殖材料有關的活動》中規定:涉及受保護品種繁殖材料的下列活動需要育種者授權,生產或繁殖,為繁殖而進行的處理,許可出售,出售或其它市場銷售,進出口或出于上述目的的貯存。以及在第(2)款《與收獲材料有關的活動》中規定:從事出售或其它市場銷售,出口,進口以及出于上述目的的貯存等活動,涉及由未經授權使用受保護品種的繁殖材料而獲得的收獲材料,包括整株和植株部分,應得到育種者授權,但育種者對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機會行使其權利的情況除外[11]。
(二)UPOV聯盟成員海外品種權申請概況
極投身國外市場,促進了育種技術交流與種質資源共享,推動了植物新品種保護的全球化進程。如圖2所示,自1999-2008年,UPOV聯盟中非本土品種權申請量由3312件增至4379件,整體呈現曲線上升勢態,申請比重約在33.12%-37.64%上下波動。
2008年,UPOV成員海外品種權申請6698件,獲海外授權5157件。如表1所示,UPOV成員有效力品種權擁有量前十強也是品種權海外申請的主力軍,美國、歐共體、日本、荷蘭、澳大利亞等國
以發達國家為首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日益受到世界各國育種單位、科研院所、地方高校及企業研發部門的高度注視,各育種機構加大育種創新投資,逐步實施跨國界、跨區域申請戰略。發達國家研發機構在致力于本土品種權申請的基礎上,積兼顧品種權的國內申請與海外申請,而法國和德國將品種權申請的工作重心傾向海外市場,如法國2004、2005和2008年國內品種授權量均為0件。而UPOV前十位成員中,俄羅斯、韓國和南非品種權的海外申請仍處于起步階段,其海外申請與授權量屈指可數。此外,丹麥、瑞士、以色列、新西蘭、比例時、西班牙、阿根廷和波蘭也積極推動了品種權的海外申請。

表1 UPOV成員前10強海外品種權申請授權量匯總(2008年)

圖2 UPOV成員海外品種權申請量及占申請總量的比重(件)
(三)國際種子市場的競爭動向
1.全球種子貿易趨于集中化。世界種子貿易主要集中在大田作物和蔬菜作物上,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全球63個主要種子出口國出口種子70.64億美元,其中大田作物種子占70%份額。如表2所示,全球種子出口呈現集中態勢,以美國為首的10個國家2008年種子出口額占63個主要種子出口國的77.27%,其中荷蘭、美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五家是蔬菜種子的主要出口國,約占71.3%的份額。
同期,全球種子進口也呈現集中態勢,但是種子進口國明顯多于種子出口國。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全球97個種子進口國共進口種子66.90億美元,其中大田作物種子占67.3%。如表3所示,美國、法國為首的10個國家2008年種子進口額占97個主要種子進口國的59%,其中美國、荷蘭、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家為蔬菜種子主要出口國,約占45%的份額。

表2 種子出口國前十強的種子出口情況(2008年)

表3 種子進口國前十強的種子進口情況(2008年)
2.全球種業經營趨于集中化。在全球植物新品種保護格局下,全球種業發展已形成由少數跨國種業所壟斷的格局。如表4所示,全球前十強種業2007年銷售額總計達147.85億美元,占全球商業化種子市場份額的67%,呈高度集中態勢。其中以孟山都和杜邦種子公司所占份額最大,兩者占全球商業化種子市場份額的38%。此外,全球前十強種業主要集中在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瑞士和丹麥等六個國家,其中美國3家大型跨國種子公司銷售額達91.81億美元,占全球商業化種子市場份額的52%。

表4 全球前十強種業銷售情況(2007年)
二、對我國品種權保護現狀及種子貿易的分析
1997年3月我國頒布《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標志著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走上法制軌道。該條例明確植物新品種概念、特征,積極鼓勵培育植物新品種,為種子市場公平競爭提供了法律保障[12]。1999年4月23日,我國正式加入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成為第39個成員國,履行78Act。
(一)現階段我國國內外品種權的申請情況
1.國內品種權數量可觀,但保護形式以大田作物為主。農業部植物新品種保護辦公室先后頒發并施行八批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名錄,共涵蓋5大類80個種屬,即大田作物18種、蔬菜24種、花卉20種、果樹15種和草本類2種。其中最近一次為2010年3月頒發并施行的蓮、蝴蝶蘭屬、秋海棠屬、新幾內亞鳳仙花等6類商品價值高的花卉種屬[13]。同期,我國植物新品種權在數量上也取得長足進步,至2008年底,我國擁有有效力的品種權1898件,列居全球第11位,占全球品種權量的2.33%。如表5所示,至2010年6月,我國品種權申請量總計7062件,其中大田作物的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占總數的86%和92.76%,同比蔬菜、花卉、果樹、牧草等其它作物品種權的申請與授權均甚少。
且在我國大田作物品種權的申請上呈現出集中的勢態,主要為玉米、水稻、普通小麥、大豆、棉屬和甘藍型油菜五大作物,其申請總量占大田作物品種權申請總量的96.69%,其中以玉米、水稻和普通小麥所占的比例最大。而蔬菜類作物的申請主要以辣椒屬、普通西瓜、普通番茄、大白菜、馬鈴薯和黃瓜為主,花卉類和果樹類作物的申請分別以菊屬和梨屬為主。

表5 我國品種權申請授權量匯總(1999-2010年6月)

表6 我國海外品種權申請量匯總(1999-2010年6月)
2.我國海外品種權數量少,且多以花卉、果樹為主。從1999-2010年,我國曾先后向荷蘭、日本、美國等14個國家提交品種權申請,總計達462件,其中有59件獲得授權,目前只獲得來自荷蘭、日本、美國、韓國和新西蘭五個國家的授權,授權品種主要集中在荷蘭與日本兩國。如表6所示,我國海外品種權申請涉獵的種屬絕大多數為花卉和水果,大田作物只有水稻、玉米、大麥三個種屬,對于蔬菜品種權我國只向法國提交過馬鈴薯的申請,但至今未獲得授權。
(二)我國種業集中度測算
我國品種權保護制度的實施促進了我國種子企業由分散、小規模逐漸向集中、規模較大的方向發展,大規模的并購整合有助于種子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資源配置,增強種子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種子企業規模小,種子產業集中度偏低[14]。
CRn指數是最重要也是運用最普遍的絕對集中指標,它是指行業內規模最大的前幾位企業有關數值占整個市場或行業的份額。這一數值可以是產值、產量、銷售額、員工總數或資產總額等。它一般是以產業中最大的n家企業合計的市場份額占整個產業市場的比例來表示的,其公式為:


圖3 CR4與CR10集中度測算
其中X為整個產業的總銷售額,Xi為第i個企業的銷售額,Si第i個企業的市場份額。通過對種子行業上市公司數據的調查匯總,結合實地調研數據,本文得出種子行業中銷售額前四位和前十位企業的數據。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年報中主營業務的收入除了包括種業收入以外,往往還包括其它主營收入,因此,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與合理性,在統計數據時,本文剔除其它主營收入,僅計算種業收入。最終得出CR4和CR10的集中度,結果如圖3:
可以看出,我國種業絕對集中度不論是CR4還是CR10,雖然基本上是在不斷提高的,但仍然十分分散。到2007年,我國種業集中度CR4僅為7.38%,銷售額僅為23.05億元人民幣,遠遠小于發達國家水平,我國種業市場化發展水平依然十分弱小,種子行業為典型的分散競爭市場結構[15]。
(三)我國優勢農產品及種子貿易情況
發達國家出于保持農產品競爭優勢以及保障國家經濟戰略安全的考慮,紛紛采用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來壟斷優勢技術并尋求全球保護,以控制國外農產品的進口和保護本國農產品的出口,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面臨巨大壓力。我國蔬菜種子資源豐富,已保存的約有3萬多份,其中生產上主栽的品種或一代雜種有1000多個。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的實施有助于我們掌握品種資源的所有權,依靠優良種質資源,提高植物品質,應對國外的技術壁壘[16]。同時,利用農產品貿易契機為我國品種權走出國門提供良好平臺。
1.我國蔬菜貿易優勢明顯。蔬菜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我國的優勢產業,具有較大的增值、增收潛力。1995年,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生活需要,我國政府開始實施“菜藍子”工程,蔬菜面積和產量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發展至今,我國國內蔬菜市場已經處于飽和狀態,為進一步提升我國的蔬菜產業,政府鼓勵實施出口帶動戰略,對促進農業發展、農村就業和農民增收具有重大意義。
近年來,我國蔬菜貿易發展迅速,蔬菜已成為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優勢產品。本文選取的蔬菜指食用蔬菜,包括鮮式冷藏的蔬菜、冷凍的蔬菜、暫時保藏但不適于直接食用的蔬菜以及干蔬菜四類,但不包括脫莢的干豆和鮮、冷、凍或干的含高淀粉或菊粉的根莖等。通過對海關統計年鑒數據整理,如圖4所示從2000-2007年,中國蔬菜出口額高速增長,連年呈現高額順差且出口目的地呈多現多元化趨勢。2009年,我國蔬菜出口額高達34.12億美元,進口額僅為0.31億美元,實現貿易順差33.81億美元。

2.我國蔬菜種子貿易增長迅速。據不完全統計,2000-2007年,我國共與全球139個國家進行植物種子貿易,總額達15.93億美元。涉獵蔬菜類、大田作物類、花卉類、果樹類及其它類等46種植物種子、果實及孢子,以紫苜蓿子、其他飼料種植種子、草本花卉植物種子、蔬菜種子、種用秈米稻谷、其他種用苗木、種用西瓜子貿易為主,其中蔬菜類種子貿易所占的比重最大,超過種子貿易的25%。按我國品種權劃分,本文的蔬菜類種子主要包含蔬菜種子、種用西瓜子、種用甜瓜子、種用馬鈴薯、種用豌豆、種用蕓豆、種用扁豆。同期,我國與49個國家進行蔬菜種子貿易,其中與韓國、荷蘭、美國、日本的貿易最為頻繁。如圖5所示,除2001年外,我國蔬菜種子無論是出口額還是進口額均呈現高速增長的趨勢,且出口額增長的趨勢明顯高于進口額。
(四)我國品種權應實施選擇性地走出去戰略
通過對我國品種權海內外申請情況概述,對我國種業集中度及我國優勢農產品貿易情況簡要分析,我國品種權海外發展應采取選擇性的走出去戰略。我國人多地少,保障糧食安全是長期以來乃至未來發展所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對此黨和政府在十五和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指出保障全國耕地面積,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并通過“種子工程”等措施提高糧食單產、品質和生產效益,因此我國國內品種權仍需將大田作物的申請作為重點。而對于我國品種權的海外申請,應結合我國優勢農產品產業,如充分利用蔬菜、果樹和花卉及其種子等貿易,將其作為我國品種權走出國門的一個有利平臺。
三、我國品種權海外發展的戰略框架及對策分析
在我國品種權海外發展的戰略中,政府相關部門和國內種子企業任重而道遠。政府職能部門與企業必需緊密合作,如圖6所示,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充分發揮職能,為種子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外部環境,具體職能如下:

圖6 我國品種權海外發展的戰略框架圖
1.以科研機構為后盾,充分運用基礎性研究成果。科研機構以基礎性研究為主,政府通過某種利益連接機制,使種子企業有償使用科研機構的基礎性研究成果,避免基礎性研究重復進行,減少資源浪費。
2.扶持優勢產業中的優勢企業,鼓勵企業從事品種研發。一方面,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創立企業育種創新基金,鼓勵企業培育經濟性作物,尤其是我國具有出口優勢的作物品種。同時鼓勵優勢農產品行業中具有雄厚資金的企業與高校強強聯合,共同完成經濟作物優良品種的開發;
另一方面,減免企業自主研發產品稅收。如企業銷售或出口自行研發經濟作物的繁殖材料或收獲材料,對企業相關產品實施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提高企業從事經濟作物品種研發的積極性。
3.促進種業兼并、重組。全球種業未來發展方向的雛形已十分明顯,在少數大型跨國種業的牽引下,全球種業正在向規模化、國際化和集中化趨勢大步邁進。Maskus和Penubarti(1995)指出,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里市場勢力表現的比較突出。目前國內種子企業數量多、規模小,銷售假、劣種子,實行價格戰等非正常交易手段時有出現。加之培育新品種消耗時間和金錢,但復制一類新種子的模仿成本基本為零。對此政府職能部門,一方面應加強種子管理,嚴禁劣種子、假種子進入市場,對嚴重擾亂我國種子市場秩序的經濟人給予嚴厲的經濟和刑事處罰;另一方面,加強種子行業管理,提高種子企業進入行業的門檻。明確種子企業組織機構中人才隊伍的比例,強調育種研發部門和研發工作者的重要性,淘汰不具有優勢的種子企業,逐步提升優勢種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促進我國種業的集聚。
4.建立海外申請品種權的服務機構。加強品種權海外申請的機構部署,實現海外本土化研-產-銷。充分借助我國具有優勢的農產品貿易及具有較強實力的種業巨頭,對我國優勢農產品及種子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進行詳細研究,在此基礎上到部分國家建立品種權海外申請服務機構。一方面,在品種權海外申請機構的部署國,深入研究當地種植的主要作物,對外開放的品種以及市場的潛在需求;另一方面,在當地為我國種子企業或個人提供有償的育種場地,技術指導及相關手續辦理等服務。利用我國大型跨國種子企業,與當地研究機構或是大學合作,共同開發適宜本土化的新品種,以達到真正的本土化管理。
另一方面,種子企業加速調整企業內部研發投資比例,完善研發部門的建設,擴充研發隊伍。最終形成以新品種權的開發、形成、保護、轉移為主鏈條,以科研機構為后盾,以種子企業為先鋒,以育種創新為核心,各類資源一盤棋的格局,逐步促進我國育種結構的變遷,引導種子企業成為我國第一大育種主體。
[1]MASKUS K E ,PENUBARTI M.How Trade-Related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39:227-248.
[2]AL-MAWALI N.Bilateral Intra-industry Trade Flow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First Empirical Evidence[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5,12:823-828.
[3]CATHERINE Y C.Do Patent Rights Regimes Matter[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12:359-373.
[4]FALVEY R,FOSTER N,GREENAWAY D.Trade,Imitative 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6,145:373-404.
[5]PERRIN R K.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ing Country Agriculture[J].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9,21:221-229.
[6]蔣和平,孫煒琳.我國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的現狀與對策[J].農業科技管理,2001,20(6):12-18.
[7]周宏,陳超.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對農業技術創新的影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1):13-17.
[8]羅忠玲,凌遠云,羅霞.UPOV聯盟植物新品種保護基本格局及對我國的影響[J].中國軟科學,2005,(4):37-42.
[9]陳超,展進濤.轉基因技術對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的挑戰[J].知識產權 ,2006,16(6):44-47.
[10]UPOV.States Par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Z].Geneva:UPOV,2009.
[11]黃發吉.UPOV1978文本與1991文本比較[J].中國花卉園藝,2004,(15):8-10.
[12]閆書鵬,翟印禮.并購與種子產業發展[J].商業研究,2007,(9):111-115.
[13]農業部植物新品種保護辦公室.植物新品種保護基礎知識[M].北京:藍天出版社,1999.
[14]陳超,展進濤,周寧.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對我國種業的經濟影響[J].江西農業學報,2007,19(7):134-137.
[15]李寅秋,陳超,唐力.品種權保護制度對我國種業集中度影響的實證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2):35-39,53.
[16]陳超,林祥明.論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J].農業科技管理,2004,23(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