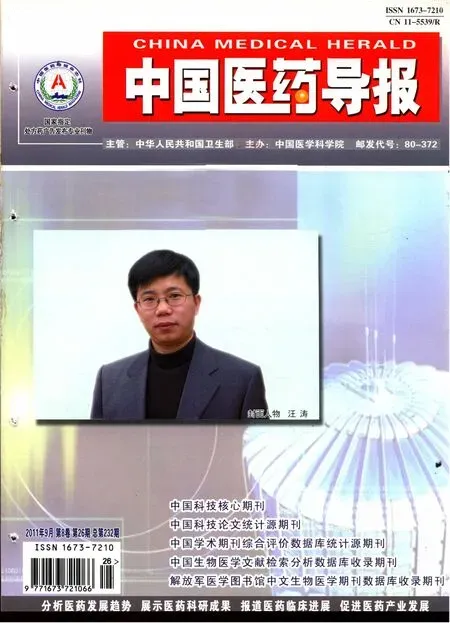肝脾破裂術中自體血液回輸32例臨床分析
張文彥,張宇飛,張明昌
遼源礦業集團公司總醫院普外科,吉林遼源 136201
肝脾是最容易受損傷的腹部器官,占腹部閉合性損傷的40%左右[1]。隨著人們對肝脾在人體免疫功能的逐步認識與研究,現代肝脾外科在治療肝脾外傷時保留肝脾及其免疫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同時術中自體血液回輸的應用價值也得到了體現[2]。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1月采用血液回收機對32例肝脾破裂術患者進行了自體血液回輸手術,效果良好,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32例中,男20例,女12例;年齡11~73歲,平均42.5歲;肝破裂10例,脾破裂20例,肝脾復合傷 2例;致傷原因:交通事故20例,高處墜落6例,刺傷4例,撞擊2例;失血量 600~4200 ml,回輸血量 450~3600 ml。 受傷時間為0.5 h~3 d。主要臨床癥狀為腹痛,3例患者均有腹膜炎體征,4例患者有頭暈、眼花、惡心、口干、心跳加快等休克表現。入院血壓為 70~110/40~60 mm Hg(1 mm Hg=0.133 kPa)。 1 例患者合并肺挫傷及肋骨骨折。按Call和Scheele分級:Ⅰ級8例,Ⅱ級20例,Ⅲ級4例。
1.2 方法
本組所有患者采用自體血液回輸治療:采用M9W-3000P3000P型血液回收機,把患者創面上血液回收到血液回收機內,注意在回收血液時應將連接在吸引管上的抗凝藥吸入吸管內與血液混合,以防血液凝聚。在血液回收的同時,應將肝素15000 IU加入500 ml生理鹽水內。血液在血液回收機內經多層過濾后,積極應用大量生理鹽水進行沖洗—分離—清洗—凈化處理等流程,反復為之,然后將抗凝劑、清洗液、抗游離血紅蛋白、脂肪顆粒、血小板廢棄,清洗離心后的洗滌濃縮紅細胞排入血液袋內回輸給患者。
1.3 觀察指標
對本組所有患者術前紅細胞(RBC)、血紅蛋白(Hb)、血小板(PLT)和術后24 h的靜脈血進行血常規和凝血酶原時間(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和纖維蛋白原(FIB)進行檢查。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術前、術后參數的統計分析做配對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組平均每例患者回輸血1150 ml,最少350 ml,最多4000 ml。死亡2例,均為嚴重失血性休克時間過長,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本組未發現全身感染、血紅蛋白尿、凝血異常等情況,血液回輸效果良好。住院時間9~16 d。平均10.5 d。術前及術后24 h血常規檢查見表1。由表1可知,RBC、Hb、PLT 都有了明顯改善(P<0.05)。 凝血三項檢查見表2。由表2可知,PT和APTT術前與術后24 h比較,均達到了正常水平,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組術后FIB平均值顯著高于術前(P<0.05)。
3 討論
肝脾是腹腔內最容易受傷的臟器,關于肝脾外傷的處理:無休克或容易糾正的一過性休克,經影像學檢查證實脾破裂傷比較局限、表淺,無其他臟器合并傷者,可在嚴密觀察血壓、脈搏、腹部體征、血細胞比容及影像學變化的條件下行非手術治療[3];觀察中如發現繼續出血或合并其他臟器損傷應立即中轉手術,而在術中,合理選擇血液是重中之重[4]。自體血回輸的優勢:①自體血回輸能提高肝脾破裂危重患者搶救成功率,為搶救肝脾破裂患者爭取到寶貴的時間,可使60%~70%的患者避免異體輸血[4]。②自體血回輸技術可以解決血源不足問題,還避免了醫源性傳染問題[5-6],同時細胞的活力較庫存血好,運氧能力高[7]。③自體血回輸操作簡便,術前準備快,無需化驗血型與交叉配血[8-9]。本組結果顯示,RBC、Hb、PLT都有了明顯改善(P<0.05);凝血酶原時間(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術前與術后24 h比較,均達到正常水平,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組術后纖維蛋白原(FIB)平均值顯著高于術前(P<0.05),顯示了良好的治療效果。
表1 患者治療前后血常規檢測結果(±s)

表1 患者治療前后血常規檢測結果(±s)
時間 例數3232術前術后P值RBC(×1012/L)3.82±0.853.53±0.710.025 Hb(g/L)112.93±24.12106.86±21.380.012 PLT(×109/L)218.57±108.6192.35±80.340.036
表2 患者治療前后凝血三項檢測結果(±s)

表2 患者治療前后凝血三項檢測結果(±s)
時間 例數3232術前術后P值PT(s)12.52±1.2412.65±1.283.362 APTT(s)29.23±5.3428.79±5.841.232 FIB(g/L)2.54±1.643.41±1.530.021
總之,自體輸血是血液保護的主要組成部分,對于急診創傷性手術患者,既可提高搶救成功率,又可減少輸注異體血造成的經濟負擔與不良反應,且對患者的血常規與凝血指標有很大改善,值得推廣應用。
[1]杭燕南,莊心良,蔣豪.當代麻醉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1345.
[2]周志浩.延遲性脾破裂17例診治體會[J].中華現代臨床醫學雜志,2009,2(2):146.
[3]戴朝六,許永慶.肝脾外傷分級與外科治療的選擇[J].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09,24(12):711.
[4]廖芝偉,田發琳,翁皖,等.脾外傷非手術治療38例報告[J].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09,24(12):739.
[5]梁建峰,林良輝,張茂忠.外傷性脾破裂診治體會[J].創傷外科雜志,2010,2(2):102-103.
[6]王國友.外傷性脾破裂的外科治療[J].中國當代醫藥,2010,17(20):20-21.
[7]張洪光,張和眾.非典型肝血管瘤CT診斷[J].中原醫刊,2004,31(5):51-52.
[8]李平,于益芝.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小鼠模型[J].國際流行病學傳染病學雜志,2008,33(6):392-395.
[9]盧圣愛,徐昌清.重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醫院感染及其預防[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9,15(7):790-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