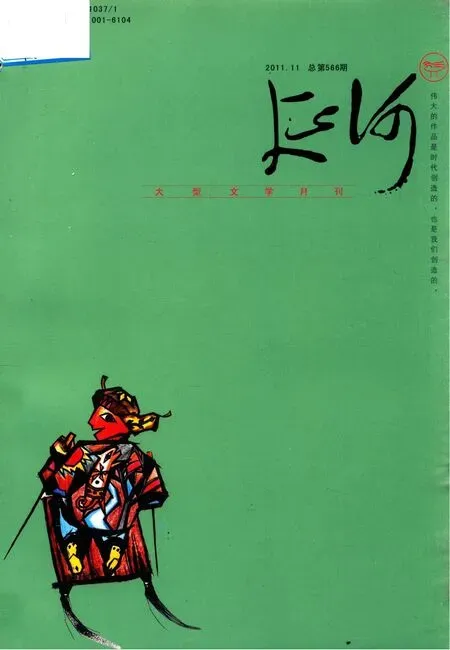奧斯特的敘事遁形術
包慧怡

保羅·奧斯特 著 包慧怡 譯 《隱者》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

人民文學出版社
保羅?奧斯特的第十五部小說《隱者》有一種表面的輕盈:更加生脆、洗練、從容的文字,更清晰的敘事框架,更多可讀性——太好讀,以至于你會疑心它不夠好。這種具有欺騙性的輕淺正是冷靜自律的結果。《隱者》不是那種可以令人掩卷時長舒一口氣的作品,也絕不是一部精致版的《羅生門》。它是一條咬住自己尾巴的長蛇,你找不到圓環的起點;它那漩渦狀的敘事有一個安寧的臺風眼,所謂“隱者”,恰恰棲居在這看不見的中央。
一如奧斯特的其他幾本小說,《隱者》書中有書,故事里套著故事。故事的核心部分是由三個敘事者相繼講述完畢的:《春》中的亞當?沃克(第一人稱),《夏》中的亞當?沃克(第二人稱),《秋》中的吉姆?弗里曼(第三人稱,由吉姆根據此時已去世的亞當留下的手稿改寫而成),《冬》中的——不,沒有《冬》,冬是隱形的,只有冬的寒意長存于冰冷單調、永無休止的擊錘聲中——第四部分中的塞西爾?朱恩(第三人稱)。其中《春》、《夏》、《秋》合起來便構成了亞當沒能寫完的回憶錄《1967》,那些隨亡者逝去的秘密則由塞西爾在日記中補充完整。或許應該在“亞當”、“吉姆”、“塞西爾”上打引號?第四部分伊始,吉姆就告訴我們,《1967》中所有的人名和地名都已經過了篡改。隨著故事的不斷展開,我們腳下自詡為真實的臺階被一級一級抽空,我們對每一個敘事者的信任也逐一瓦解,直到我們被拋入一扇反轉之門,一座迂回的鏡宮——究竟誰是真正的隱者:那個不是亞當的亞當?不是波恩的波恩?不是吉姆的吉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假名替代、蒸發、成為幽靈,實相化作影像,場景化作蜃景,人人都是說謊者,人人都是勾引家,人人都躲藏在一個故事/一本書的面具之下,奧斯特似乎在不無反諷地暗示著,惟有在陰影幢幢之地才可能稍稍接近真實。

蔣子龍 著 《農民帝國》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8
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本書以改革開放三十年為背景,以郭家店的發展變化為藍本,以郭存先的經歷為線索,細膩而深刻地描寫了一群農民起伏變化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錢、欲望、權力對人性的沖擊。一代梟雄,從農民到農民帝國之巔到階下囚,經歷了怎樣的人生大起大落和靈魂蛻變?作家在不動聲色的描述中,帶給人們的是強烈的情感碰撞和無盡的思索。也使作品在一如既往的硬朗中,又添幾分滄桑與深厚。
和奧斯特前幾年的某些小說不同,結構上的匠心并未使《隱者》顯得文勝質,書中人物也并非用來試驗作者種種認識論立場的樂高玩具,而是真正傾注了作者的感情,真正與作者情同此心——《隱者》中幾乎每個人物都是如此,連波恩也不例外。事實上,亞當在寫作《夏》時遇到的“作家阻塞癥”很可能是奧斯特本人再熟悉不過的,而通過嘗試吉姆“改變人稱”的建議,亞當和奧斯特拯救了各自的寫作。
“通常,被阻塞的情形來源于作者思考中的一個缺陷——也就是說,他不完全理解自己想要說的東西,或者,說得委婉些,他對主題采取了錯誤的處理方式……用第一人稱來寫自己時,我壓抑了自己,使自己成為隱形人,因此就無法找到所要尋找的東西。我需要把我從我自己身上分開,后退一步,在我和我的主題(也就是我自己)之間雕刻出一塊空間,于是我回到第二部分的開端,開始以第三人稱書寫。”在這一意義上,《隱者》又是一本關于小說寫作的元小說,和這一文類中的許多作品不同,《隱者》讀來毫無學究氣,那些把它歸為智性小說的評論家其實低看了它,《隱者》首先是通過血肉勻停的故事打動我們的,正如奧斯特永遠首先是個說故事的能手。
“隱者”——直譯為“看不見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奧斯特沒有采用粗俗的點題法,而是將一幅閃光的地圖剪碎,看似漫不經心地拋擲在敘事的湍流中。開篇不久,亞當如此描述波恩的臉:“一張尋常的面孔,一張在任何人群里都會隱形的面孔”;給吉姆的一封信中,亞當稱奧克蘭和伯克利的族裔居住區里的黑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是“看不見的人”;吉姆在從舊金山到紐約的飛機上回想著1967年的糟糕日子,感到“一個看不見的美國在我下方的黑暗中沉睡著”;最后,當塞西爾逃離孤島奎利亞上波恩的大本營“月亮山”,她聽見了金屬與石頭冷酷而浮夸的合奏——“每把都以自己的節奏運動,每把都被鎖在自己的韻律中”——卻看不見聲音的來源,即便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后,一只看不見的手也將永遠起落于塞西爾的顱中,永遠叮叮當當地敲鑿著石頭。

郭文斌 著 《農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0
小說以“小說節日史”的方式呈現中國文化的根基和潛流,展示中華民族民間化的經典傳統,經典化的民間傳統,堪稱清明上河圖式的長篇。作者花費12年心血,寫成這部以農歷為名的長篇小說,其中包含的不僅是作者對中國古老習俗和文化的理解和闡釋,更是作者對人心世道的深切關懷。該書三十萬字,以十五個傳統節日為綱,從元宵開始,到上九結束,記述了一整個季節的循環。
而看不見的遠不止這些。亞當在《夏》中對與姐姐格溫的不倫之戀的回憶和格溫本人的回憶完全對不上號,兩人都聲稱自己道出了真相——也許的確如此。我們的記憶是個慣于擅自篩選的黑洞,我們無從了解它運作的機理——為何保存這些,屏蔽那些,又自動改寫那些——它卻使我們成了無動機的撒謊者,并且各自問心無愧。這個塵世的萬花筒啊,不要輕易搖晃它,別把眼睛迫切對上那許諾了確定性的窺孔。
假設亞當在《夏》中寫出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奧斯特仍通過亞當的寫作活動對自己和所有小說寫作者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我們該如何書寫生命中重要的故人——同時又不書寫他們?該如何訴說一個秘密,但秘密還是秘密?那些最初促使我們提筆寫下故事的人,那些如今早已淡出我們生命的鬼魅,只要他們尚在同一個世界上呼吸著,我們又怎可能避免遭到誤解,我們的作品怎可能不被看作單方面對真相的修正、對共同經驗的重新闡釋、自我辯解、個人潛意識的外化?我自己從未能解決這些問題,它們像一掛濕漉漉的蛛網,纏住寫作者的心智,令我瞻前顧后,躑躅難行。而奧斯特通過書中之書《1967》提供了一種苦澀的慰藉: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寫下就是暴露自己,寫下,然后被指認——這就是小說家的命運。每個人都只能看見自己想看見的東西,說故事的人對此無能為力。
反過來,對著書者身份的競爭——對講述者、大寫的“我”字的競爭——也一直是貫穿于奧斯特作品中的重要主題,比如《密室中的旅行》里的茫然先生、范肖、特勞斯(Trause,Auster的鏡像?),比如《隱者》里的亞當和吉姆,波恩和塞西爾,當然,還有奧斯特本人。寫作意味著主體性,而成為書中人物就是被客體化,被閹割,被沒收存在權,因為在書頁闔上的剎那,你就被迫噤聲。
回應這一主題的作品可以回溯到喬斯坦?賈德《紙牌的秘密》、博爾赫斯《莎士比亞的記憶》、劉易斯?卡羅爾《愛麗絲鏡中奇遇記》——在鏡子背面的世界里,史上最帥的怪叔叔、蘿莉控、攝影師、數學家、偽童書作者卡羅爾讓紅騎士和愛麗絲爭奪做夢者的身份,因為做夢意味著存在,而被夢見者將隨著夢者的醒來不可避免地銷聲匿跡。當波恩要求塞西爾以小說的形式代寫他的自傳,塞西爾的回答是:“我為什么會對幫別人寫書感興趣呢?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過,誰知道呢,也許被關入白紙也并不那么糟糕,至少那兒存在一種表面的確定性,詞語本身絕非隱者,而言辭之樹常青。一如奧斯特所寫:“作為另一種意識的臆造之物,我們將比創造我們的意識有著更久遠的生命力。”

劉慶邦 著 《遍地月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9
小說寫文革時期的農村生活,“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普通人的戕害:少年黃金種出身于地主家庭,父母遭受批斗死去,金種與弟弟銀種和叔叔黃鶴圖生活在一起。他們生活在屈辱之中,隨時都會被村干部、貧下中農欺侮。金種先后追求村里的兩個姑娘,但是由于出身不好,到頭來只是一場夢幻。換親、逼婚、假扮夫妻,被毀滅的愛情、被扭曲的人生。愛情毀滅了,人生扭曲了,一個地主少年該走向何方?
《隱者》中我最喜歡的人物是將呂柯弗隆的《卡珊德拉》從古希臘語譯成法語的塞西爾。這篇晦澀的長詩也曾出現在奧斯特的處女作、半自傳體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中:每隔一百年左右,神秘的羅伊斯頓男爵會在某人身上附體,把這首寫于公元前三百年的古希臘長詩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一如卡珊德拉瘋狂的預言永遠沒人相信,呂柯弗隆瘋狂的作品也永遠沒人閱讀,“于是這是項無用的任務:寫一本永遠合著的書”。羅伊斯頓男爵的幽靈在《隱者》中附身于一個孱弱、神經質、落落寡合的天才少女,塞西爾身上有種奇特的悲劇性,她平庸的結局比亞當的更令我難過。吉姆如此評價晚年的塞西爾:“盡管她在狹窄的學術研究領域是個成功者,她一定明白她為自己選擇了怎樣一種奇怪的生活:禁閉在圖書館和地窖的小房間里,埋頭于逝者的手稿,一種在無聲的塵埃之領域里度過的職業生涯。”永遠在一盞孤燈下翻閱古卷的現代隱士,這正是奧斯特長于刻畫的那類人。雖然生活在此世,他們的心智更貼近中世紀修院的繕寫室。
一如奧斯特筆下所有那些沉默的譯者——無論是《幻影書》中翻譯夏多布里昂《墓后回憶錄》的齊默,還是《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和中靠翻譯維生的A,或是《隱者》中翻譯普羅旺斯詩人貝特朗?德?波恩的亞當。作為抵御或者維護孤獨的工具,翻譯是一項將我們拉近地面的活動,一種謹小慎微、耐心而謙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能夠賦予我們可貴的安心。
《隱者》是我翻譯的第一本奧斯特小說,也是我最享受其翻譯過程的一本小說。充盈于全書中敘事的暗面、意象的環形山、可能性的滑動門雖然賦予了《隱者》更加輕捷的結構,呈現在其中的卻是一個變重了的奧斯特,一個和以往不一樣的奧斯特。但愿讀到這里的人們會如我一樣地喜歡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