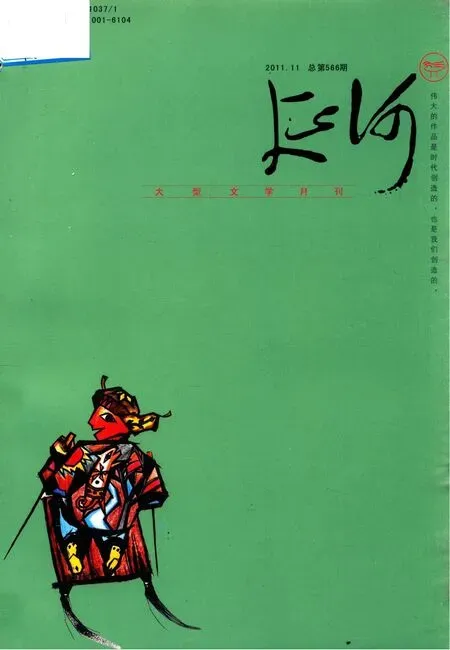《三國的戰爭》序
一
我對三國的研究,緣于一次偶然的機會。大約是前年冬天,我的老朋友、北京電視臺副總編輯,同時兼任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董事長的張強先生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幫忙看一看《赤壁大戰》的劇本。其時,這部由著名華人導演吳宇森先生執導的電影大片,雖然尚在籌備階段,但已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北京電視臺作為投資方之一,亦在造勢上推波助瀾。張強先生是影視圈中名人,他策劃的“紅樓選秀”活動,使得大型電視劇《紅樓夢》在開拍之前,就已懸念迭起,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出于友誼,我不能推托張強先生的請求。劇本很快發到了我的電子郵箱。仔細看了一遍,我給張強先生回電話說:“吳宇森先生的這部《赤壁大戰》,給觀眾帶來的是一個藝術的三國,若以歷史真實的標準來衡量,則還有一段距離。”張強詢問我,能不能就一些歷史真實問題給出具體的意見。我說這不大好辦。因為從劇本中我看出吳宇森先生的創作意向,他要用好萊塢大片的敘事方式來取悅于當下的觀眾。他是用美國的胃口來消化中國的歷史。若一定要用“歷史真實”這一命題去要求,則這部電影可能沒有拍攝的必要。
我以為這次談話之后,這件事情就算了結了。誰知過不多久,大約是去年春節之后,張強先生約我來到北京面談,提出他們出資,請我做一部關于三國的紀錄片。這讓我頗費躊躇。因為,這時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國》自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播出后,已經紅透全國。我再做一件與他相同的事,不但意義不大,而且頗具風險。因為,我沒有易先生那樣的口才,若再步其后塵,豈不是東施效顰?
但張強先生卻另有一番道理。他說,易中天是講三國,這屬于談話類節目,與專題片完全是兩碼事。專題片是要盡可能拍攝所有的三國遺址,既讓人有現場感,更讓人體味歷史的滄桑感。見我猶豫,張強進一步說:“你這部專題片,是配合吳宇森的《赤壁大戰》而做的。關于這部紀錄片的定位,我想好了兩句,即‘吳宇森告訴你一個藝術的三國,熊召政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三國’,你覺得怎么樣?”
我能覺得怎么樣呢?還是用那一句老話吧:恭敬不如從命。
二
我本是研究明代歷史的。一下子跳到東漢,初始有一點物是人非的感覺。不過,心里頭雖起了隔世之嘆,卻并不感到陌生。這乃是因為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三國的這一段,在民間的普及率永遠是高居榜首。
在我的孩童時代,我不知道朱元璋、朱棣,但我知道曹操和劉備;我不知道劉伯溫與宋濂,但我知道諸葛亮與龐統;我不知道徐達與常遇春,但我知道關羽與張飛。從這一點上得出判斷:我研究明史是長大成人后理智的選擇,而知曉三國則是民間對我的歷史啟蒙。
歷來,嗜史者有兩種,一在廟堂,一在江湖。居廟堂者,執掌機樞,心存社稷,須得從歷代興亡衰變中汲取經驗教訓,尋找可為當下所用的政治智慧。所以,他們關注的歷史人物,大都是扭轉乾坤、治難興邦的政治強人。而江湖中人,大都以民間視角,從道德與生活兩方面,去衡量與欣賞往古的忠臣孝子、才子佳人。至于對英雄與智士的推崇,則是廟堂與江湖共同的立場。基于這一點,三國時期的歷史與人物,便能夠受到一代代國人的研究與喜愛。
不過,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時下國人津津樂道的三國,多半是源于小說《三國演義》而并非史著《三國志》。像大家耳熟能詳的《捉放曹》、《溫酒斬華雄》、《借東風》、《空城計》等故事,都不是真正的歷史而是小說家言。所以說,很多人喜歡三國,是喜歡羅貫中先生編撰的三國故事而不是陳壽先生著述的三國歷史。
大約成書于明朝嘉靖年間的《三國演義》,應視作為當時統治階級服務的一部主旋律作品。明代以忠孝立國。《三國演義》宣傳的便是忠孝思想。基于此,小說中將劉備政治集團塑造成忠孝代表,以曹操集團作為反襯。這樣一來,便顛倒了歷史。數百年來,羅貫中的歷史觀一直左右著國人對三國的認識與判斷。
在作了幾個月的案頭準備工作之后,從去年的八月份開始,我便帶領包括導演與攝像在內的九人攝制組,用了近五個月時間,走訪三國遺址。我們先后到達遼寧、河北、山西、河南、陜西、四川、云南、湖南、江西、安徽、湖北、江蘇等省份,行程萬余公里,凡與三國有關的名勝古跡、戰場遺址以及人物故里,都一一參訪。
雖然,這段歷史已過去一千七百多年,但是,其遺址之多,實在讓人驚訝。在我走過的近千處遺址中,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三十處,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數百處之多。對這些遺址進行考察,可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也可糾正許多以訛傳訛的史實。當然,也有不少遺址真偽莫辨,它們多半是明代之后由當地政府或民間集資修建的紀念性建筑,其根據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部文學作品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這在中外文學史上,亦屬罕見。
此一趟三國遺址之旅,大大豐富了我的三國知識。采訪歸來,有同行不無羨慕地說:“自古到今,你是第一個走完全部三國遺址的人。”
三
在研究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走訪了全部三國遺址之后,我便與張強先生商量怎樣進行這部紀錄片的撰稿工作。因為,這部紀錄片的起因是緣于吳宇森先生的電影《赤壁大戰》,為了遵循與影片互動的原則,我提出用貫穿三國的四大戰爭,即官渡、赤壁、漢巴、夷陵來作為敘事的契機。張強先生同意了我的構想。
但在寫作過程中,我就發現講述戰爭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其因是:第一,人們不喜歡戰爭。因為戰爭是毀滅生活的工具。除了瘋子和狂人,沒有人愿意毀滅自己的生活。所以,三國的眾多古跡,旅客最少的地方便是戰場的遺址;其二,關于三國的史書,從《三國志》到《九州春秋》等等,對戰爭的記述都極為簡單,甚至語焉不詳。像一直為后人津津樂道的赤壁之戰,在《三國志》中,只有寥寥數語。這就為完整的描述一場戰爭增加了困難。而且,由于年代久遠,可供拍攝的場景實在太少,這亦是紀錄片的大忌。
經過幾次摸索與調整,最終決定以戰爭為線索,著重表達戰爭中的人。這樣一來,便引出了許多令人感興趣的話題。所謂話題,即史實中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人和事。如袁紹與曹操為何從摯友變成仇敵、歷代盜墓賊為何奉曹操為祖師爺、劉備為何一打仗就丟老婆、諸葛亮的《隆中對》是不是書生之見,等等。將這樣一些話題找出來加以稽核與剖析,便覺得生動有趣。析微索隱,征聞有據,一一道來,便覺得三國離我們并不遙遠,發生在三國人物身上的事情,如今仍在我們自己的身上不斷發生。
雖然,這部書仍以四大戰爭為主線,但這根藤上,結著的不再是刀光劍影下的冤魂而是生命樹上的話頭。禪家啟悟智慧,洞開心靈,曾有一種方法,叫參話頭。我在三國歷史中旅游了兩年,便為讀者留下了這一本話頭,它首先是找出來的,然后是參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