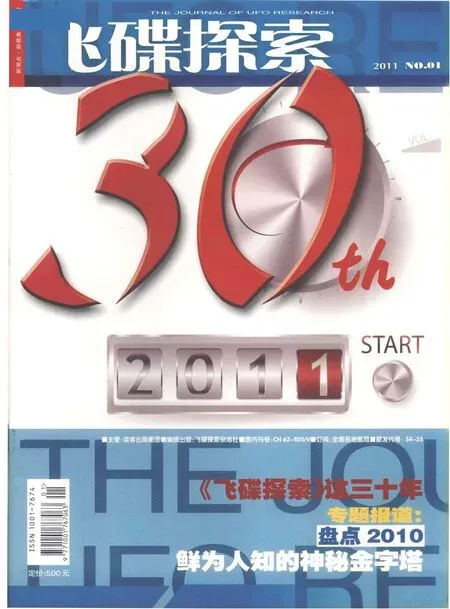為什么要這樣了結自己?
■ 尹傳紅
日本《產經新聞》2009年11月28日報道說,為防止自殺現象蔓延,日本政府的“緊急戰略小組”制定了“百日防自殺行動計劃”,準備在100天里集中力量進行相關的調查和預防工作。文章披露:截至2008年,日本的自殺人數已連續11年超過3萬人。由于就業形勢惡化,政府擔心年末自殺的人數可能增加,因此決定采取緊急對策。
關于自殺,多年來我一直記得有一個諧趣而又不乏悲情的說法:這是對一個暫時性困難的永久性解決。這也是人們基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做出的關于自己生命的決定。對研究人類行為的心理學家而言,自殺一直是個難解之謎。如果說,自我保護是人類最強烈的本能之一,那么,促使人們走上自殺這條不歸路的動機一定更為強烈。
進化理論告訴我們,繁殖是進化過程的動力,而生存則是繁殖的必要條件。從進化心理學的視角來看,當個體實現其自身內在適合度的能力急劇下降時,自殺行為最有可能發生。能力急劇下降的指標包括預感自己未來的健康狀態不好、慢性疾病、丟臉或失敗、對成功的異性戀愛關系不抱希望,而且感覺自己成了家庭的負擔。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在上述條件下,個體要想將其基因傳播下去,較好的方式莫過于讓其親屬有更好的繁殖機會和條件。如果一個人成為其家庭的負擔,那么,其親屬的繁殖和他(她)自己的適合度都可能因他(她)的存在而受到損害,假如他(她)死了,該個體的基因或許會有更好的機會被復制。現有的證據表明,人類有可能已經進化了對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機制,用于評估自己未來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為家屬帶來的凈代價。一個世紀前,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和奧地利精神病醫生及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對自殺這種行為做出過一些籠統的解釋。迪爾凱姆認為,所謂自殺,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其根源在于社會因素,譬如說個體沒有融入社會等等。弗洛伊德則認為,自殺是受人的本能所驅使(特別是他所說的“死本能”)。自殺的意念本來就存在于人的精神結構之中,這是指向自己的無意識的敵意,是向自己發泄憤怒。
后來的一些解釋趨向于把自殺和精神抑郁、絕望及感情痛苦聯系在一起。但這些理論都無法成功地解釋一個有關自殺最基本的問題:為什么在看似相同的環境中,有些人會自殺,另一些人卻不會自殺?現在我們所了解到的情況是,大多數自殺者均有精神障礙,幾乎都是由于腦部疾病或心理病理因素造成的。比如抑郁癥、焦慮癥、精神分裂癥、厭食癥、邊緣性人格障礙、雙極性失調或其他心情不適。其中,抑郁癥和躁狂抑郁癥患者自殺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精神病人或醫學上的高危群體都大得多,生活中遇到的難題只是加速了這一事件的發生而已。

有研究者指出,抑郁癥狀、心智敏銳和緊張、憂慮不安行為的結合尤為致命。在高度緊張的情緒主導下,一個人走向自毀的內心沖動逐漸增大,并達到摧毀其自我防衛機制的程度,悲劇就發生了。針對30項研究的一份綜述表明,有平均1/5的躁狂抑郁癥患者自殺身亡。從一個相差無幾的視角看,自殺者中至少有2/3都被發現患有抑郁癥或躁狂抑郁癥。國外一項大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沒有精神障礙史的人一生中企圖自殺的比例為1%,而在那些患有重度躁狂抑郁癥的人中,這一比例竟然高達24%。
不止于此。導致自殺的幾種危險因素通常是文化因素、個性因素和個體境況因素。一般而言,各種危險因素在一種特定的自殺行為中存在交叉重疊和相互影響的情況。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較早從社會學角度揭示,社會因素對自殺這種高度個體化的行為構成了一種根本性的影響,失范便是其中之一(涂爾干把某些令人困擾不安的境遇稱為失范,這是一種由現代社會生活所激起的茫然感和絕望感)。他查看了法國官方的自殺記錄,發現某些類型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自殺,例如:男性中自殺的人比女性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富人比窮人多;單身者比已婚者多。在每種情況下,都是更具個體主義色彩的社區有更高的自殺率。
他還注意到,戰爭期間自殺率較低,而當經濟處于變革或不穩定期時,自殺率較高。基于上述發現,涂爾干得出結論:外在于個體的社會力量影響著自殺率。他認為,個體如果與社會群體充分整合,其欲望和抱負受到社會規范的調控,就不大可能會自殺(比如婚姻可以把個人整合進一種穩定的社會關系中,從而避免自殺)。致力于自殺的預防和干預工作的二位美國學者諾曼·法貝羅和埃德溫·施奈德曼提出,自殺意圖一般會以下述四種主要方式表達:直接的言語(比如“如果你離開我,我就自殺”)、間接的言語(比如“沒有愛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生活”)、直接的行為(比如囤積安眠藥片)和間接的行為。
而最后一種方式是有跡可尋的:一是,放棄珍視的所有物,立遺囑或專注于其他最后的安排;二是,突然和極端地改變飲食習慣或睡眠方式;三是,伴隨著抑郁情緒,回避朋友和家人或改變其他重要的行為;四是,學業表現或工作表現發生變化;五是,性格改變,比如緊張不安、容易上火或不顧健康、不修邊幅;六是,濫用藥物或酗酒。人們向來都把自殺作為社會現象來分析。法國作家、哲學家阿爾貝·加繆在其隨筆《西西弗斯神話》中提到,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歷,這本身就是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所有其他問題一概都是居于自殺之后的次要問題。西班牙哲學家米格爾·烏納穆諾也在其名著《生命的悲劇意識》中講過,理性主義的生命終結將是自殺。對此,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說得很清楚:“純粹思維方式存在的結果就是自殺……我們不贊揚自殺而只贊揚激情。思想家是一種好奇的動物,在一天當中的某些時刻,他是非常聰明的;但是在其他大部分時間里,他跟平常人毫無相似之處。”
今天,我們對于自殺,恐怕不能只看作病理、心理問題,更要從生命意識缺失的角度,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癥結所在。早有教育工作者感慨:在這個技術宰制一切的時代中,教育封閉了通向靈魂的大門,對生命的異化和遮蔽使其迷失了方向,越來越遠離生命的原點。許多人不懂得生命的寶貴,更不懂得珍惜生命、呵護生命的意義,這使得他們的生命出現一片無知的空白。一個以人為本時代的到來,呼喚教育回歸生命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