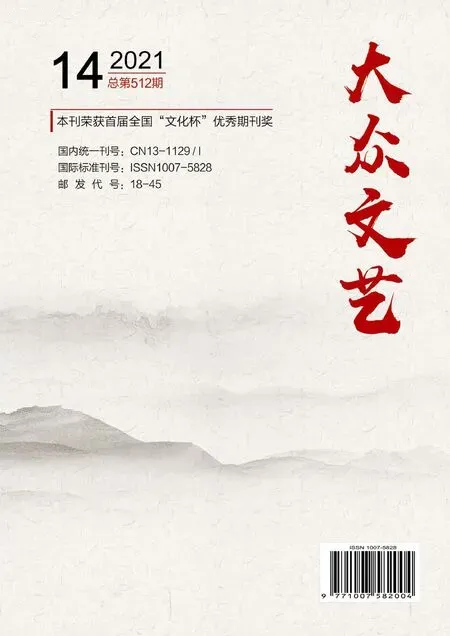普契尼與柳兒的情愫
丁 苑(南通高等師范學(xué)校藝體系 江蘇 南通 226000)
《圖蘭朵》作為普契尼最后一部未竟的“天鵝之歌”,代表著作曲家各種風(fēng)格要素的全面綜合展現(xiàn)。這部以中國(guó)題材創(chuàng)作的歌劇作品,讓人領(lǐng)略到東西方音樂(lè)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柳兒作為劇中重要的女性人物形象之一,從她身上映射了普契尼氣質(zhì)女性的縮影——她們往往天生麗質(zhì),柔弱而善良,無(wú)論精神上還是肉體上承受多大的痛苦或煩惱,卻最終無(wú)法擺脫死亡的悲慘命運(yùn),但也正因此贏得了觀眾的同情與喜愛(ài),比如《藝術(shù)家的生涯》中的咪咪、《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及《修女安杰麗卡》中的女主角。的確,在《圖蘭朵》中,恰恰是這個(gè)身份卑微的“女仆”給觀眾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
一、柳兒的角色塑造
歌劇《圖蘭朵》中,普契尼對(duì)柳兒的精巧刻劃可以說(shuō)是費(fèi)盡心機(jī)、無(wú)可挑剔的。她的死與蝴蝶夫人、托斯卡、修女安杰卡一樣,都是為了愛(ài)情。為了能促成卡拉夫與圖蘭朵公主的愛(ài)情,柳兒甘愿犧牲自我,在這一點(diǎn)上,她與蝴蝶夫人選擇了同樣的道路,性格發(fā)展也驚人地相似。通過(guò)對(duì)巧巧桑、咪咪這些同一類型女主人公的成功塑造,使得普契尼能駕輕就熟地塑造出柳兒。這種似曾相識(shí)的角色特征,體現(xiàn)出作曲家一貫的創(chuàng)作習(xí)慣與固定模式。
但作為普契尼人生的終曲,他又試圖努力擺脫以往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束縛。他使柳兒在劇中擁有著雙重性格:一面是溫柔、謙卑與善良;另一面則是為了愛(ài)情把生命置之度外的剛毅與勇敢。通過(guò)兩種截而不同的性格反差,增強(qiáng)人物性格在戲劇性上的沖突。此外,又將柳兒的真誠(chéng)善良與圖蘭朵的冷酷殘忍形成強(qiáng)烈對(duì)照,就算柳兒的死,也成為促成圖蘭朵人性復(fù)蘇和性格轉(zhuǎn)化的強(qiáng)大內(nèi)因,正是這種精神之愛(ài)再結(jié)合卡拉夫的實(shí)體之愛(ài),才最終化解了千古的仇怨。與咪咪、巧巧桑相比,柳兒這一人物形象無(wú)論從性格還是劇情安排上都顯得更為豐滿,更具有一種強(qiáng)烈的內(nèi)在精神力量,而她的悲劇性也成為《圖蘭朵》最震撼人心的動(dòng)力。
二、柳兒的音樂(lè)描述
“音樂(lè)作為歌劇藝術(shù)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衡量一部歌劇是否成功的決定因素。”[1]歌劇與其它藝術(shù)形式(話劇、電影、舞蹈等)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它主要憑借音樂(lè)的一切構(gòu)成因素和各種表現(xiàn)手段來(lái)刻畫人物形象,推動(dòng)劇情發(fā)展,展現(xiàn)戲劇沖突。普契尼對(duì)待柳兒這樣一個(gè)對(duì)愛(ài)無(wú)限忠貞,雖遭受折磨仍不為所動(dòng)的“小人物”的音樂(lè)描述,并沒(méi)有拘泥俗套(給她安排固定音調(diào)),而是傾注了滿腔熱情,全劇精心設(shè)計(jì)安排了三首詠嘆調(diào)。
第一首來(lái)自于第一幕的《主人,請(qǐng)聽(tīng)我說(shuō)》,這是對(duì)柳兒內(nèi)心情感進(jìn)行細(xì)膩刻畫的抒情性詠嘆調(diào),整首歌曲從力度的分配上,出現(xiàn)最多的力度標(biāo)記是p或pp,即便是全曲的最高潮也未出現(xiàn)一個(gè)f,甚至mf。用弱的音量來(lái)暗示柳兒特殊的身份與地位,抒發(fā)源自心靈深處的悲痛和絕望,顯示出作曲家的獨(dú)到之處。之后的兩首詠嘆調(diào)都出現(xiàn)在第三幕,一首《隱藏在心里的愛(ài)比痛苦更堅(jiān)強(qiáng)》與《主人,請(qǐng)聽(tīng)我說(shuō)》具有類似的音樂(lè)風(fēng)格。另一首《你那顆冰冷的心》柳兒死意已決的終曲,這首詠嘆調(diào)的伴奏中,似乎有一個(gè)醞釀著不幸厄運(yùn)的音樂(lè)動(dòng)機(jī),又仿佛是死神腳步的臨近,柳兒雖然未死,但送葬的內(nèi)在感覺(jué)已經(jīng)初步展現(xiàn),并貫穿全曲的始終。隨著柳兒為愛(ài)獻(xiàn)身,這首極為動(dòng)聽(tīng)、肝腸寸斷的哀怨詠嘆調(diào),又在之后的葬禮場(chǎng)景中進(jìn)行了充分的音樂(lè)處理和發(fā)展,并將這一幕推向了情感迸發(fā)的最高點(diǎn)。而頗耐人尋味的是,偉大的作曲家在寫完該段之后,也永遠(yuǎn)地離開了我們,使該劇成為歌劇史上永恒的遺憾。
三、柳兒演唱處理
柳兒在劇中最經(jīng)典的詠嘆調(diào)《主人,請(qǐng)聽(tīng)我說(shuō)》,出現(xiàn)在全劇的第一幕,深愛(ài)著卡拉夫的柳兒試圖打消心上人去冒險(xiǎn)求婚的念頭。由于社會(huì)階級(jí)地位的懸殊,使得她對(duì)卡拉夫的愛(ài)慕之情只能深深地埋藏心底,正式這種內(nèi)斂的、發(fā)自心靈深處的絕望與哀求,對(duì)表演者提出了較高的演唱要求,不要過(guò)多地追求音量,要在保證氣息連貫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細(xì)膩柔和而富于變化的音色,詮釋主人公的痛苦與無(wú)奈。
曲式結(jié)構(gòu)上看此曲是一個(gè)單段體的樂(lè)曲,降G大調(diào),詠嘆調(diào)以柔板(Adagio)開始,沒(méi)有前奏只用一個(gè)和弦作為調(diào)式的提示。在總共只有20小節(jié)的旋律中,就分別在第5、第7、第15以及第18小節(jié)出現(xiàn)了四次“漸慢地”(rit rall)速度標(biāo)記,這樣的藝術(shù)處理生動(dòng)再現(xiàn)了柳兒的焦慮與悲傷,演唱時(shí)要注意速度的控制與把握,做到張弛有度。
第一句“Signore,ascolta!”中聲區(qū)“i”的母音,演唱時(shí)要利用頭腔共鳴的高位置,聲音在控制的基礎(chǔ)上弱而不虛,將后面幾個(gè)音慢慢拉開。接下來(lái)的“Liu non regge piu”盡量用內(nèi)在的聲音演唱,以表現(xiàn)柳兒萬(wàn)分痛苦的內(nèi)心情緒。“Ahime”后咽壁要立起,“cuor”到“ahi”的過(guò)渡要輕松、自然。接下來(lái)的一句出現(xiàn)了三連音與兩個(gè)四分音符的連接,對(duì)于這兩個(gè)節(jié)奏型演唱時(shí)要區(qū)分明顯;“col tuo nome nella nima”一句要漸慢地演唱;“col nome tuo sulle labbra”要更加漸慢地演唱,表現(xiàn)的很夸張。三句連起來(lái)應(yīng)形成“漸慢——再漸慢——更加漸慢”的趨勢(shì),表現(xiàn)出柳兒越來(lái)越激動(dòng)的思想感情,但卻不能因此而拖沓。
緊接著的三句速度上恢復(fù)原速,情感上卻要逐漸激動(dòng)。頭一句“Ma seil”堅(jiān)定而充滿力量,“sti”的高音a2及前后兩音要唱得連貫;接下來(lái)一句氣息進(jìn)一步拉寬,配合與歌唱旋律相一致的伴奏,情緒表現(xiàn)更加激動(dòng);再往下的一句,要特別注意幾處小的音符連線,演唱時(shí)切不可忽略不計(jì),運(yùn)用氣息的支持與控制,表現(xiàn)女主人公內(nèi)心更為激動(dòng)的情緒。這三句的情感表現(xiàn)應(yīng)是“激動(dòng)——再激動(dòng)——更加激動(dòng)”的趨勢(shì),與前面“漸慢——再漸慢——更加漸慢”形成鮮明對(duì)比。
下面逐漸轉(zhuǎn)入詠嘆調(diào)的高潮部分,力度標(biāo)記卻是pp,“Ei perdera suofiglio” 演唱時(shí)運(yùn)用軟起音,“e”到“i”母音的過(guò)渡要注意位置的統(tǒng)一。下一句同樣用柔和、連貫的語(yǔ)氣演唱,但第二句須唱得更加內(nèi)在、含蓄,速度上逐漸放緩。因?yàn)榱鴥寒吘怪皇莻€(gè)侍女,在中國(guó)古代的倫理關(guān)系下,要顯得尤其謙卑,特別是表露自己的愛(ài)慕之情時(shí),似有遮掩。“Liu non reggepiu!”速度由Adagio轉(zhuǎn)為L(zhǎng)ento。音高上存在八度的跳進(jìn),并且高音落在小字二組降A(chǔ)的位置,緊接著的“Ah,pieta!”同樣存在八度大跳的問(wèn)題,隨即在小字二組的降B音上結(jié)束,這一句要用p的音量來(lái)表現(xiàn),無(wú)疑對(duì)演唱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它需要演唱時(shí)將腔體充分打開,在保證高位置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橫膈膜對(duì)氣息的支持與控制,將后咽壁拉緊,發(fā)出細(xì)膩、柔和而富有張力的聲音,表現(xiàn)柳兒對(duì)心上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祈禱與哀求,將人物的內(nèi)心情緒推向戲劇沖突的最高點(diǎn)。
《圖蘭朵》作為普契尼告別人生的絕筆之作,它代表著作曲家不斷嘗試拓展自己藝術(shù)表現(xiàn)領(lǐng)域的頂點(diǎn),是普契尼一生藝術(shù)追求的綜合展現(xiàn)。縱觀普契尼所創(chuàng)作的歌劇詠嘆調(diào),雖其創(chuàng)作的時(shí)代背景、內(nèi)容不同,但都反映了曲作者在特定時(shí)期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與特色。他擅長(zhǎng)運(yùn)用傳統(tǒng)意大利式優(yōu)美流暢的旋律,賦予詠嘆調(diào)、宣敘調(diào)以極強(qiáng)的歌唱交響性;同時(shí)又注重借鑒、吸收外來(lái)一切優(yōu)秀的藝術(shù)文化,如《蝴蝶夫人》中的“日本風(fēng)情”,《西部女郎》中大量美國(guó)鄉(xiāng)土音樂(lè)的渲染,《圖蘭朵》中在“中國(guó)元素”的運(yùn)用方面,更是融合了拍子、節(jié)奏及各種伸縮性速度的表現(xiàn),讓觀眾仿佛置身于心曠神怡的東方異國(guó)情調(diào)中,恰到好處地塑造了人物形象,揭示戲劇沖突,推進(jìn)劇情的發(fā)展,使得普契尼歌劇的音樂(lè)煥發(fā)出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
[1]居其宏.《歌劇美學(xué)論綱》[M].安徽文藝出版社, 2003年
[2]楊燕迪.《圖蘭朵》的中國(guó)版解謎[J].人民音樂(lè), 2008,(04).
[3]樊其光.普契尼歌劇女高音詠嘆調(diào)的藝術(shù)特色及其演唱處理[J].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1995,(04).
[4]馬驊.論普契尼歌劇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刻畫[D].上海音樂(lè)學(xué)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