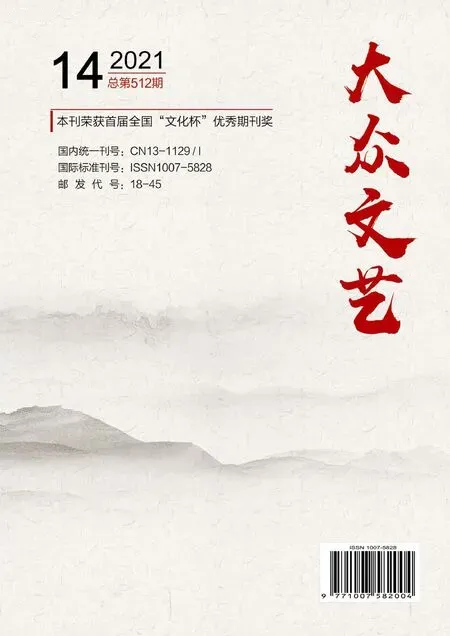明妓詞人創作題材探析
歐陽珍(河池學院 中文系 廣西 宜州 546300)
妓女作詞自唐五代開始,歷經宋、元,至明代,出現了一個詞人群體。這個群體共存詞三百多首,與前代相比,在詞人詞作數量上均達到了高潮。言為心聲,這么一個特殊的詞人群體在她們的詞作中想要表現的是什么呢,這是本文擬以探討的。
筆者以為,在明代妓女詞人的筆下,有一個貫穿的主線,那就是對愛情的渴盼,對命運的悲嘆。可以說,她們的創作基本都是圍繞著這一主線展開的,不論是寫景感時、臨別贈言,還是詠物賦情、自我描繪。愛情、命運,就如一曲詠嘆調,在她們的詞句中跳躍。
當然,愛情、命運,這自是被排除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的古代女性在文學創作中不可脫離之范疇,然則相較閨秀詞人而言,妓女的創作空間更是牢牢維系于此。閨秀詞人的婚姻是極其順理成章之事,而且無法自己選擇男子,因此更多表現的是對婚姻的一種期待,對婚姻生命的一種希望,主要是對一個男性注入更多的期待(含有一種無可奈何,只能有他的一種感情期待)。而妓女詞人沒有丈夫可托情,沒有家人可慰懷,沒有子女可寄意。因此,與閨秀詞人相比,妓女詞人寫詞時就更多表現了對愛情的渴望。而妓女身份決定了她們極難獲得一個穩定的家庭生活,因而年華逝去何去何從的無歸宿感時時叩擊她們的心扉,表現在詞中便是對命運的感嘆與悲鳴。
一、傷時篇——愛與命運的交織
古代女子多被困于狹小的生活空間,而文學是生活的反映,故她們文學創作的內容也由此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相思、傷春憫秋便成為古代女性創作始終堅持的主題。然而,就妓女詞人來說,傷嘆暮春的落花芳草,傷怨美的零落,傷怨自己華年的流逝較其它女性詞人則更為敏感,因為她們是從事著以色事人的職業。身世飄零、美人遲暮,往往在她們的筆下更是流連:
春到人間能幾日。愁過清明節。陌上正繁華,裊裊游絲,杜宇聲啼血。茫茫山水經年別。感事歸心切。無計可留春,陣陣楊花,吹起漫天雪。(卞賽《醉花陰?春恨》)
這是一首惜春詞。通過杜鵑啼鳴,楊花飛絮來表現春歸,表現寂寞生活中傷春惜春的情懷,形象而又具體,可感可觸。詞人以細心來體驗時序變遷,觀察周圍景物,抒寫內心感受,都很精致細膩,既無華艷的詞藻,也不用凝煉含蓄的筆法,而是在淡淡的描繪中讓人感到春光逝去的無限的惆悵。
面對春天的美景,女主人公感受到的卻是“春到人間能幾日”的憂愁,縱使是在這樣的景致中游玩歌舞:
蹋踘場前,笙歌隊里,是處風光任君取。金罇送人不忍去,高樓漫系青驄尾。景無邊,情無畔,恨無底。人共留春春不許。我試問春春不語。過卻清明尚余幾,堤邊柳垂千萬縷。新鶯欲倩風呼起,綠蘿煙青,麥浪梨花雨。(張麗人《千秋歲引?春游》)
春季,萬物復蘇,百花盛開,一片如詩如畫的美景。春游,本是從古至今人們最為賞心悅目的活動。可是,詞人在這樣一個本該開心的春日里卻不能忘憂,而是感嘆“人共留春春不許”。清明一過,春天就將逝去了,現在的美景何時才能再見到呢?末幾句寫景,美麗而旖旎,卻讓人徒增美景難留,歲月空逝,情懷何在的悵惘。
春恨如此,秋愁更甚,春天鶯飛草長、明花照水的美麗的景致都能引發詞人的滿懷惆悵,秋天萬物凋零、衰颯凄涼的景象更能激起詞人心中的悲苦。崔嫣然的《謁金門?秋思》中道:
風蕭瑟。猛聽霜砧搗急。應念征鴻無信息。教人愁似織。無限驚心透骨。都在眉頭堆積。明月梧桐清露滴。蛩吟聲唧唧。
這首詞寫秋夜懷人,那情郎似征鴻一般杳無音訊。“明月梧桐,清露滴,暗蛩吟敗壁。”蕭瑟的秋景,正是作者凄涼心境的外化。而尹春的《醉春風》寫秋日懷人,把相思與愁融為一片:
池上殘荷盡,蘺下黃花嫩。重陽還有幾多時,近近近。曾記舊年,那人索句,評香品茗。望斷蕭郎信,懶去勻宮粉。蝦須簾外晚風生,陣陣陣。雙袖生寒,一燈明滅,博山香盡。
這首詞不論寫景還是寫人都很真切,情中寓景,景中含情。“殘荷”“黃花”“一燈明滅”“香盡”,在在寫出詞人心中的愁苦與思情,而“曾記舊年”三句,寫狎客簡直呼之欲出。
二、寄贈篇——愛的表白與相思
低賤的身份,被人賞玩的命運,超出一般女子的姿色、技藝和才智,使妓女們得到了名門閨秀難以得到的與士大夫文人廣泛接觸,并由此產生知己般愛情的機會。但妓女的身份,文人的游宦和官吏職務的高升,常使他們之間的戀情不能始終。所以妓女們的愛情,總是面臨著別離。于是在她們的筆下,愛情就更多表現為離別與相思之苦:
曉鶯啼罷,起來多少愁緒。鉤簾飛絮,水流花落,銷魂時節,拋人歸去。玉鞭門外路,和淚看人,更無言語。燕釵燭冷,云鬢花欹,倦臨繡戶。愛風流、幾許賺人句。恨此生,卻似海棠開無主。佳期難據。怕魚沉雁杳,尋伊何處。況多病多愁,怎禁零落,這番春暮。空閨今夜,夢魂深銷,半窗煙雨。(方是仙《女冠子?別懷》)
這首詞,寫的是一個妓女行將與意中人離別時的痛苦。通過“飛絮”、“落花”寫出離別的時節正是暮春。而“和淚看人,更無言語”,用形象勾勒了內心深處難以明言的痛苦。為什么如此悲痛?下闋告訴我們,她擔心意中人那些恩恩愛愛、白頭偕老的話不過是:“愛風流,幾許賺人句”。而從此一別,恐怕就:“魚沉雁杳”,只有慨嘆“尋伊何處”了。全詞把暮春凋零景象與對前途不可捉摸的心情融為一體,婉轉低回,凄涼悲切,令人傷楚。
再有馬守貞《蝶戀花?天香館寄陳湖山》:
陣陣東風花作雨。人在高樓,綠水斜陽暮。芳草垂楊新燕語,湘煙剪破來時徑。腸斷蕭郎紙上句。深院啼鶯,撩亂春情緒。一點幽懷誰共語?紅絨繡上羅裙去。
春日的黃昏本來就是引人遐思的,再加上落花陣風、逝水斜陽,高樓上的佳人必會有所感嘆和期待。然而,詞人胸懷的是一種無處傾瀉的、受阻以至混昧的哀怨。哀怨青樓生涯中沒有特定的“蕭郎”,也哀怨自己的才貌抵不住時光的流逝。詞人無“眼前人”可以愛憐,所以只能寄懷于故人,在春色里寄懷一種自己也難以捕捉的愁緒。《眾香詞》中贊其“詞如花影點衣,煙霏著樹,非無非有而已”,[1]甚當。
花謝了,明年還會再開;燕子去了,明年還會再來;只是心上人兒離別了,在悠久的時光里,再也聽不到有確切的歸來的日子,如何能不憔悴、如何能不感傷呢:
一種情懷不自由,怎禁風雨釀春愁。慵拈針線倚妝樓。楊柳傷心腰困舞,桃花無語淚空流。那人何日去心頭。(梁玉姬《浣溪沙?寄遠》)
分別的時候,離愁讓人消瘦了面容,亂了心緒,魂也依依夢也依依,風雨釀了春愁,連楊柳、桃花也自“傷心腰困舞”,“無語淚空流”,情寓于景,更讓人黯然神傷。這首詞不僅是寫出別后的孤獨與相思的痛苦,更是寫出“一種情懷不自由”而產生又恨又憶的思想矛盾,為何不自由,只因那人呵!所以要問“那人何日去心頭”?寫得如此真實大膽、情意切切!
明代妓女詞作中題為寄別之作就有近50首,她們為愛所苦,為愛所盼,亦為愛所悟,為愛而大膽地訴說著自己的相思。
三、詠懷篇——愛與命運的悵罔
古代女子的生存空間極為狹窄,雖然作為妓女,較閨秀所受到的禮法約束較少,能有一定的社交活動,但其主要的生存格局仍然不出妓院。以院墻為有形的圍欄,以行規為無形的天網,遮蔽著她們頭頂廣袤無限的藍天,阻隔了她們眺望遠方的目光,她們只能在封閉的圈子中彷徨,在孤獨與寂寞中煎熬:
孤燈半滅愁無數。河外清蟾涼印戶。閑庭露草亂蟲吟,似共離人分泣語。玉樓杳隔湘江浦。黝黝離魂尋得去。夜半沉鐘落遠聲,短枕驚回忘去路。(呼舉《木蘭花令愛?夜坐》)
這首詞寫夜晚孤燈獨坐的情形。詞人夜坐難眠,是因“紅顏可逐春歸去”的憂慮、“去也終得去,住也應難住”的相思,還是“一點幽懷誰共語”的哀怨、“難得有心郎”的失落與傷感?總之,孤單悵惘之心緒無法言說,無處可落。詞以“亂蟲吟”來喻“離人分泣語”,比喻新奇又形象。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這是唐代女冠魚玄機的詩句,可這豈止是她個人的感慨,實際上概括了所有娼妓在戀愛與婚姻問題上的痛苦。娼妓,即使是名藝俱佳的名妓,在所謂有身份的人們看來,總是倚門賣笑的“賤貨”。她們不過是那些有錢有閑階層的男子性生活的伴侶,逢場作戲可以,明媒正娶不行。因此,一個女子一踏進煙花巷,就意味著被剝奪了愛情和婚姻的正當權利,被剝奪了雙飛雙棲、“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正常生活,就意味著她們必須“享受”的是背棄,是孤獨:
清夜無眠,湘簾下,瀟瀟雨打蕉窗。聽秋聲一派,攪碎心腸。何事玉郎不至,情索莫。偏覺更長。燈花落,枕屏斜倚,睡鴨銷香。思量。舊歡團扇,只等閑拋卻,莫遣情傷。數樓頭征雁,影去瀟湘。隔院吹來玉笛,聲咽咽,漸入宮商。桐露滴,金風陣陣,冷透羅裳。(馬如玉《鳳凰臺上憶吹簫?秋夜期亙史不至》)
這是一首慢詞,詞人層層鋪敘,將敘事、寫景、抒懷融為一體,寫秋夜孤寂索莫的心思。正是夜涼如水的秋夜,瀟瀟雨打芭蕉,叩動窗欞,更是將詞人等待無至的心攪得粉碎。思量又思量:“何事玉郎不至”,莫非是“舊歡團扇,只等閑拋卻”?隱約的玉笛聲傳來,嗚嗚咽咽,恰似心頭傷。露重風寒,冷了衣衫,亦冷了心腸。這首詞道盡秋夜等待無望的哀傷,言下無限凄楚。
四、詠物篇——愛與命運的嗟嘆
在明妓詞人存留詞作中共有26首詠物詞,所詠之物有花草和其他雜物。以花草為吟詠對象,其實許多便相當于妓女詞人們的自畫像。她們詠花草,其實就是在吟詠自己的不幸身世與不屈人格:
剪彩自成叢。朵朵嬌紅。一枝斜倚玉壺中。別有芳心開爛漫,不倩東風。寶鼎篆煙濃。香隱丹衷。年年長傍繡簾櫳。歷盡嚴霜并烈日,難減芳容。(頓文《賣花聲?詠像生花》)
裊裊亭亭半碧柯。柔枝百尺掛煙夢。風翻殿角霞裁錦,雨潤天心月擲梭。香霧重,曉煙多。仙云冉冉下嫦娥。卻憐未傍蟾宮桂,空號凌霄奈若何。(李無塵《鷓鴣天?詠凌霄花》)
這是兩首分別以像生花和凌霄花為對象的詠物詞。詞一中,詞人寫到“朵朵嬌紅”的像聲花中“別有芳心”的一枝,有香“隱丹衷”,雖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日復一日地挨著日子,但“歷盡嚴霜并烈日,難減芳容”。整首詞實際上是象征著自己雖然遭受不幸的命運沖擊,但依然有著不屈的人格與精神。詞二先是對凌霄花的風姿意態進行描述,“風翻殿角霞裁錦,雨潤天心月擲梭”用比喻形象地寫出了凌霄花的富貴與風華,仿似月中嫦娥下到人間。但末二句卻道出了世事的無情,只落得“空號凌霄奈若何”的無奈。詞人以凌霄花自喻,說明自己雖有絕代風華,但在這樣的社會里,有著這樣的命運,留下的只能是聲聲哀嘆。
在所有的詠物詞中,最優秀的當為柳如是的《金明池?詠寒柳》:
有恨寒潮,無情殘照,正是蕭蕭南浦。更吹起、霜條孤影。還記得,舊時飛絮。況晚來、煙浪迷離。見行客、特地瘦腰如舞。總一種凄涼,十分憔悴,尚有燕臺佳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縱饒有、繞堤畫舫,冷落盡、水云猶故。憶從前、一點東風,幾隔著重簾,眉兒愁苦。待約個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
詞人所塑造之寒柳形象其實就是自己感懷身世、感傷愛情的動人形象。整首詞顯示出時過境遷后那種難以回首的空寂與冷落,而又于“失落”的存在狀態中挺起自己那不愿意甘受屈從的驕傲頭顱,亦柳亦人,寫得凄怨低回,情感深摯,悽惻動人,因而成了歷代詞人詠柳詞中的優秀作品之一。
以花草自喻,大凡詞作,并不少見,然而在明代妓女詞人看來,就是最普通的睡鞋與尺子也寄托了她們對于命運的嘆息:
自愛風頭能窄小,踏青斗草剛填。綺窗徙倚最嫣然,只堪蓮上步,卻懊酒中傳。豈是飛鳧仙子舄,到今零落人間。無端拋擲若人嫌。球場荒踘蹴,柳線罷秋千。(徐驚鴻《臨江仙?詠睡鞋》)
針線日為鄰,花剪常相遇。一段紅牙數帶星,點點分明處。羨爾太公平,玉指隨時取。量盡筐中百疋綃,長短由他主。(范翩《卜算子?詠尺》)
第一首詞以古代女子的睡鞋為吟詠對象,整首詞也是頗具象征意味的。古代女子纏足,“三寸金蓮”代表了一種美,那鞋自然也是小巧玲瓏,別有風味。詞人以鞋自喻,用滿是憐愛的口吻訴說著“它”的身世與遭遇。本是該在蓮花間翩翩起舞,可是怎么卻被用去做了裝酒的器具。①它應是“飛鳧仙子”誤落了人間,卻“無端拋擲若人嫌”,再沒有開心快樂的生活。第二首詞也是以很常見的尺為吟詠對象。詞的上片對尺作了很實在又很形象的描述,下片寫出了尺的作用與意義,末句則以象征手法寫出了自己命運的不由自主。
五、生活情狀的描繪——愛與命運的呢喃
正當花季時期,誰家少女不懷春,誰家少男不多情。無論生活賦予妓女們如何的折磨與痛苦,使她們的生活唱著悲苦灰色的主調,然則這本又是一群心思爛漫、最為甜美動人的女子。世事的多乖,命運的多舛,并沒有讓她們停滯追求美好事物與美好情感的歡快的腳步:
姊妹相攜來斗草。賭罷欺儂小。偷看合歡書,豈料儂知,欲向人前道。頻搔粉頰含糊笑,低首羞還惱。私許贈鮫鮹,再回叮嚀,休向人前告。(薛素《醉花陰》)
山正曛,涼早早。青海月兒洗澡。花叢誰識幾多花,只覺幽香重遶。玉露猶輕人已悄。各各深情精巧。盡從花里捉流螢,一半醉眠芳草。(楊宛《滿宮花?暑夜與諸女郎同外家宴》)
第一首詞從姐妹們相約做斗草游戲生發開來,描畫了兩個少女形象,一個世事未曉,活潑可愛;一個情竇初開,含羞帶怯,直寫得俏皮有趣,輕巧活潑,顯示出了詞人獨特的藝術構思。第二首詞則寫一群正當年華的女子在夏夜里的相聚,那種姿態、那種風情,那種若隱若現的心思,在在讓人的心境也隨之歡悅起來。
當思愁太苦,感慨太深時,她們的生活,卻是另一番景象:
蕭蕭庭院暮春天。花帶淚,柳含煙。云窗霧閣,笑語十三載。回首床空香鈿冷,人已去,夢猶連。當時爭羨共娟娟。明月下,曉風前。秋千踘蹴,攜手并香肩。可事狂風吹一夜,摧粉墮,把脂捐。(沙宛在《江城子?哭姊》》
耳鬢斯磨十三載的姐妹卻驟然而逝,人走床空,維系的只有夢。昔日的歡樂猶在眼前,突來的暴風驟雨卻是那么猛烈,那種哀痛是天地也為之失色、花鳥也為之帶淚的,且在悲痛之中隱含著對自身的隱隱的焦慮。妓女處于社會最底層,生活大多是悲慘的,她們要忍受的是身體與心理的雙重折磨,強顏歡笑背后往往是滿腹心酸與無奈。我們不可知此詞中的“姊”是因何而逝的,然我們可猜想其逝之時必還年輕,這是那個社會制度的罪惡。我們還可猜想,如此的生活感受在明妓筆下必不少,然而因作品的散佚,我們只可見到這一首。
綜觀明代妓女詞作,雖然仍不脫離一般女子的傳統題材,但與明之前的妓女詞作內容相比,已是豐富了許多,而且從詞作情感的反映可看出她們的寫作已走向了有意識地、自覺地追求,從而使詞這片園地里盛開了她們這一群特殊而又燦爛的花朵。
附注:
①古代女子纏足,小小鞋口正好放入酒杯。把酒杯放在妓女的鞋口里在酒宴上巡行勸飲叫妓鞋行酒。古代文士以妓鞋行酒的并不少見,宋代文士已開始有這種做法。
[1](清)徐樹敏.錢岳.眾香詞[M].上海.大東書局.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