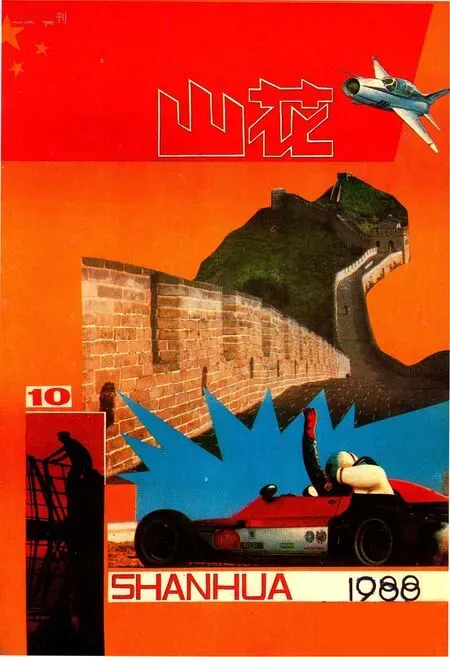現代文學經典闡釋的文學人類學向度
王小平
現代文學經典闡釋的文學人類學向度
王小平
經典闡釋首先是經典閱讀,重釋經典必定是重讀經典,因此,閱讀在現代文學經典闡釋中占據的是先在的位置,對閱讀現象的關注是現代文學經典闡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進一步來說,盡管文學是虛構的,但它在何種程度上向我們揭示了人類自身天性中的虛構化傾向。值此新一輪現代文學經典闡釋大潮,沃爾夫岡·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思想有助于我們反思現代文學經典闡釋的研究理論,確立新的文學人類學進路。
一、文學人類學:一種反思性的危機理論
作為接受美學創始人之一,伊瑟爾后期走向了“文學人類學”研究。在歐美批評理論界,盡管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轉向”并沒有贏得比肩于美學的贊譽,但其理論關注在歐洲,特別是德國,卻激起持續的回響。以“文學與人類學”命名的特別研究項目在康士坦茨大學聲勢浩大地開展著,幾位當代批評家也向伊瑟爾這樣的“人類學”批評頻頻示意。特里·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就訓誡道:未來的批評將聚焦在這樣一些事情之中,即我們作為人類,“必定滑向關于我們自身的詳盡道說”。
伊瑟爾提出文學人類學思想之際,文學正面臨著眾多媒介的侵蝕與挑戰,業已失去其理所當然、無所不包的地位,逐漸淪為眾多媒介之一種。于是,各種文學終結與死亡的話語繼起。伊瑟爾認為,“這一事實意味著:不是文學本身終結了,而是善待文學的觀念已經終結了”。
文學面臨的危機,核心是種種功能的喪失,特別是各種新興媒介的活躍,其娛樂、休閑等功能被取而代之。值此危機時刻,伊瑟爾提出“文學批評的人類學面向”,[3]意在澄清這樣一種立場:文學總是伴以闡釋和批評,長期以來,各種闡釋總是將文學視為現實功能的體現,比如歷史材料、文獻檔案、意識形態戰場、娛樂消遣等,這些需求總是一定時代“主導性需求”的反映。問題在于,一旦時代變化,時代主導性需求亦隨之變化,文學闡釋和批評緊跟其后也會發生變化。這是造成今日文學及文學批評頹勢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旦主導性需求發生變化,文學的使用價值也就發生了改變。最終,使文學抵達了今天這樣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突出表征,即是文學在現代社會中的邊緣化,文學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之物。
伊瑟爾獨具慧眼地洞悉,正因為我們的批評闡釋膠著于時代主導性需求,放棄對文學更為本質功能的尋求,才導致自身的隨波逐流,以及文學真正的悲哀:它一直被闡釋,但從來不曾成為它自己。“因為任何文學效用無疑都伴以特定歷史需要的話語,于是就出現了深層困境,只要效用等同于文學的本體,這種困境就依然隱匿其中。給文學披上現實目的的甲胄,甚或視之為現實目的本身,似乎是一種直接抵擋開放社會日益增長的復雜性的防御機制。”
從追問文學存在的人類學動因出發,伊瑟爾建立了自己的文學人類學思想。文學何以存在,并且依然存在?人們何以需要閱讀?文學作為虛構的語言織體,必定滿足了人類的某種天性。在伊瑟爾手里,文學變成了一支魔杖,勘測出我們的性情、欲望、傾向,最終是我們全部的天性。由此,伊瑟爾強調虛構化的重要意義,他認為虛構化是人類自我呈現和超越的基本需要,經由文學虛構活動,人延伸了自己,展現出人類自身的可塑性。在此過程中,他還主張超越現實與虛構的二元對立,建立現實—虛構—想象“三元合一”的文本觀,最終將文學視作一種人類學表演,這一表演貫穿于整個文學活動,包括文學創作、文學文本與文學閱讀與闡釋階段。
二、文學人類學:拓展現代文學經典闡釋的進路
相較而言,現代文學比古典文學更深刻地體會到文學的危機狀況與邊緣處境,現代文學闡釋與批評,也切身實感受到時代主導性需求的強大向心力和迷亂癲狂,同時也更深地浸染了二十世紀主義盛行的風氣。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壇整風、文藝指示和文化革命,以及一而再地重讀、重寫文學與文學史之呼吁與實踐中,百年現代文學,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著實熱鬧。
因此,與特定時代主導性需求緊密聯系的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與批評,總是陷入某種怪圈之中,那就是,主導性需求的急遽變遷,帶來整個文學闡釋的合法性危機和有效性解體,伴隨舊的主導性需求為新的主導性需求所取代,文學闡釋在理論與方法上亦不斷地尋找出路,謀求與新的主導性需求合拍,于是,新的闡釋與批評層出不窮。此種現象,一方面營造出文學闡釋繁榮的虛假現象,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文學的工具性特征。兩種結果都無助于文學的良性生產與本位歸宿的確立。前者留戀于破除、丟棄與營造之樂,使文學闡釋變成無盡的增殖活動,后者則赤裸裸地將文學變成特定時代話語的論證材料,使文學淪為笑容可掬的“幫襯者”。當前,“紅色經典”的熱火現象即是一例。紅色經典將記憶消費與意識形態動機有力地整合在一起,商業價值與意識形態訴求找到了極佳的結合點,于是,充塞著意識形態的政治革命話語與商業時尚話語的紅色經典,借助影視傳媒的力量,在現代文學經典闡釋的大舞臺上拔得頭籌。但是,一旦意識形態訴求發生變遷,商業資本逐利的本性就會暴露無遺,紅色經典熱潮就可能猛然消退,殘留下一大堆失去背景的孤零零的闡釋文本。
值此新一輪現代文學經典闡釋大潮,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思想應該可以為我們提供啟示性意義,幫助我們拓展研究進路。
(一)現實—虛構—想象“三元合一”文本觀的確立,有助于超越“文史之爭”,在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尋得平衡。
傳統思想將現實與虛構對立起來,而文學文本乃是虛構與現實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與想象事物之間的糾纏、彼此滲透的結果,在文本中,現實與虛構的互融互通的特征遠甚于它們之間的對立特征。因此,伊瑟爾建議我們拋棄將現實與虛構對立起來的舊觀念,代之以一種現實、虛構與現象三元合一的觀點。現實指文學文本中彌散著大量的具有確定意義的事項,它們是從現實社會或者某些別的文本現實中精心選擇出來的。但是這種輸入文本的純粹的現實本身,對文本并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它們并不是為了追求現實性而呈現于文本中。“實際上,在文本產生的過程中,作者的意圖、態度和經驗等,它們未必就一定是現實的反映。這些意圖、態度和經驗等,在文本中更有可能只是虛構化行為的產物。”虛構與想象是一對很容易混淆的概念,一般來說,想象常常以一種彌散的形式呈現自己,它以一種瞬息萬變的方式把握對象,并且,想象沒有具體的固定形式,往往轉瞬即逝、蹤影全無;而虛構是受主體引導和控制的行為,它賦予想象一種明晰的格式塔,這種格式塔不同于幻想、心理投射、白日夢以及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胡思亂想。因此文學文本被視為現實、虛構與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滲透的結果,文學文本是現實—虛構—想象三元合一的共生結構。
對現代文學批評而言,三元合一的文本觀有利于超越闡釋與批評中存在的“文史之爭”。所謂“文史之爭”,即重視文學之文學性研究的進路與強調文學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意義的研究進路之間的拉鋸戰。前者執著于文學性、詩性的探究,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受西方文論影響的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和結構主義批評為代表;后者則膠著于文學背景和社會語境的展示,文學一直被視作某種證詞,范圍從詩人生活的例證到反映社會的鏡子,其代表是重視史料的社會歷史研究法和知人論世的傳記研究法。在文學史觀方面,也體現出這樣兩種趨勢:其一強調文學作品與活動在實際歷史時空的指涉關系;其二則著重文學本身形式內容的變革興替。
文學具有現實性因素,現代文學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更是關懷現實的革命與啟蒙進程,道德與人倫建設,并以道義上的使命感為其重要旨趣,夏志清稱為“感時憂國的精神”。[6]但是,文學此一現實維度并不能將文學降格為歷史史料或社會學文獻,甚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意識形態“武庫”。三元合一的文本觀,消除了現實與虛構的對立,淡化了文學批評中文與史的分歧,將之統領于現實—虛構—想象的共生結構中,以虛構化行為強調文學文本的獨特性,在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將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統一起來。
(二)強調文學虛構對人類自身可塑性的拓展功能,可以極大開拓文學闡釋和批評的空間。
作為一種書寫媒介,文學使那些憑借其他方式難以實現之物在場,所謂“可狀難狀之景如在眼前”。在文學許多先前的功能已經被別的媒介接管的時刻,文學的虛構性特征為文學獲得了展示人類自身可塑性的獨特功能。
在伊瑟爾看來,虛構化是一種越界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跨越疆界的行為。在虛構化過程中,虛構將已知的世界進行編碼,把未知的世界變成想象之物,由想象與現實重新組合的文本世界,呈現給讀者一片新天地。文學的虛構化,一方面使得作者以文學形式介入現實得以可能,它是作者面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姿態;另一方面,使得讀者作為人類“延伸了自己”。在閱讀文本時,讀者關注那些在現實中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就現代文學經典闡釋而言,強調文學虛構對人類自身可塑性的拓展功能,可以極大地開拓文學闡釋和批評的空間,突出文學“間域”的塑形過程。人類對虛構的需要,實際上是一種對“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狀況的迷戀。這種狀況就是,一個人既要以自己的面目出現,但同時又想以另一個面目出現——這是人類的一個基本需要。文學虛構以不同的方式滿足了這個需要。“入乎其內”與“出乎其外”之間廣闊的空間構成一個“間域”,文學虛構的魅力就在于不斷填充、開拓和豐富這一間域。文學虛構“能使人類以不斷展開自我的方式走出自我,毫無羈絆地利用多種文化手段全景式地展現人的各種可能性,因而是一個自我塑造和創造世界的范式,這正是文學虛構的人類學意義所在。”
(三)突出文學闡釋的表演性特征,有助于確立“文學為人類”的觀念。
“對表演的需要是以公然對抗認知拆解的雙重性為標志。一方面,表演允許我們至少在幻想中過一種迷狂的生活,走出我們被束縛的現世,以另一種方式為我們自己打開被阻隔的生活;另一方面,表演讓我們深思一度斷裂的總體話語,以便我們可以通過其他可能性以穩定的形式對自己言說。”可見,表演可以將人從認知性活動的羈絆中擺脫出來,充分展露人的雙重性,開啟可能性的生活。
在伊瑟爾的理論中,人類的闡釋行為也是一種人類學表演,具有表演性品質,而文學闡釋是這種人類學表演的絕佳場所。“闡釋不是如此這般的解釋說明,而是一種表演:它讓某些東西顯露出來。這提出一個終極問題:為什么我們如此執著地熱衷于通過闡釋達成某些事情。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在我們的人類學天性中為之尋求可能的答案。”[8]經由闡釋,我們將各種隱秘的熱情、欲望、想象、記憶、夢想,以及價值期待、審美偏好和道德訴求、意識形態傾向等一并托付給某個闡釋對象,而后,在對象世界中馳騁想象,借助理論話語將種種隱秘熱情轉化為合理性表述,建構出自身的意義世界。
文學闡釋的表演性特征,有助于確立“文學為人類”的觀念,將現代文學“為政治”到“為藝術而藝術”的脈絡延伸到“為人類”的視點上。
文學史書寫是文學闡釋的重要場所,黃修己曾指出:現代文學史的最初書寫主要為了論證無產階級政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學科建立初期體現了學術為政治服務的突出特征,所以這一學科與生俱來有著歷史時間短促、視野狹窄的“痼疾”。可見,現代文學史長期出于“為政治”的外在目的,而渾然忘卻文學的審美屬性,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性”訴求的彌漫,又導致所謂“能指狂歡”游戲,證明“為藝術而藝術”的內在視野依然難掩其弊端。因此,我們提出“文學為人類”的觀念,將文學不獨視作“為政治”的外在目的或者“為藝術而藝術”的內在鎖閉,而是強調文學作為人類學表演的舞臺,不斷拓展人類自身的可塑性,為自我的呈現、完善和超越服務。
總之,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思想對于現代文學經典闡釋具有啟發意義,有利于研究進路的拓展,在文學闡釋與批評中平衡文學性與歷史性,極大地開拓文學闡釋和批評的空間;同時,有助于確立“文學為人類”的觀念,將現代文學“為政治”到“為藝術而藝術”的脈絡延伸到“為人類”的視點上。
[1]Ben Bruyn.The 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 ofWolfgang Iser and Hans Belting[J].Image&Narrative,2006(15).
[2]Iser,Wolfgang.Prospecting:From Reader Response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M],Baltimore:JohnsHopkinsUP,1989.197,208.
[3]Iser,Wolfgang.The Act of Reading: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M].Baltimore:JohnsHopkinsUP,1978.ix.
[4]Iser,Wolfgang.The Fictive and the Imaginary[M].Baltimore:The Johns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93.2.
[5]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M].北京:三聯書店,2003:316.
[6]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357.
[7]汪正龍.評沃爾夫岡·伊瑟爾的文學人類學[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10).
[8]Iser,Wolfgang.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M].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0.303,xv.
[9]熊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十屆理事會二次會議綜述[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03).
王小平(1974—),男,四川德陽人,講師,四川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國古典文獻與文藝理論。工作單位:四川理工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