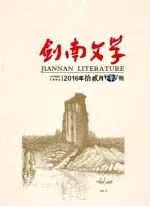近代安徽災荒頻仍原因試析
羅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610064
近代安徽災荒頻仍原因試析
羅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610064
近代安徽災荒頻仍,既有種類繁多、發生頻繁的天災;又有 局勢混亂、戰爭不斷的人禍。兩者互相作用,共同成為滯緩安徽近代經濟發展的重大因素之一,其中教訓發人深思。
近代安徽; 災荒; 原因
近代以將,安徽災荒頗多。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根據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變遷》對安徽省歷代災荒狀況的考察,發現安徽自然災害更是連年不斷,“越是近代,人為與自然的災荒越發嚴重”①。不僅如此,人為的災害也是頻頻發生,長期不絕。如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時,清政府對安徽省經濟最發達的沿江地區和江南一帶,進行了最殘酷地鎮壓;繼而在皖北發生了持續十年的捻軍起義;民國時期,軍閥派系對立,長期相峙在這一地區,從1912至1930年18年間,省政府首腦換了二十多次②,等等這些都深刻反映了近代皖省災荒頻仍、政局混亂的歷史背景。
是什么原因致使災荒的頻繁發生呢?個中原因是值得深思的,下面從兩方面原因及其不良的影響來分析。一方面,天災:自然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繁;另一方面,人禍:社會局勢常混亂、戰爭不斷。
一、天災:自然災害種類多、發生頻繁。
翻開人類歷史的諸多篇章中,可以發現自然災害是伴隨人類發展史的每一腳步,可見自然災害時客觀的難以根除的,但我們還是可以做好前期的警備及后期的救扶工作,以把損失將到最小,顯然那時候的政府還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動力和體制。
自然災害,主要有水災、旱災、疫癘、蟲災、風災、雹災、地震等。在近代安徽,這些災害無一程度不同、時間不一、區域不定地存在。綜合來看,自南向北,水旱災害是愈來愈多,沿江一帶大約每隔兩年出現一次水旱災害,江淮地區每隔一年多出現一次水旱災害,而沿淮地區則每隔一年或不到一年就出現一次水旱災害。其他自然災害,如風災、霜災、雪災、地震,雖在這段歷史時期的安徽災荒史上并不十分突出,但也在局部小范圍對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造成了一定的損害。其發生, 也與一定的氣候、地質特征有關。災害,“是對人類社會造成物質財富的損失和人身傷亡的各種自然社會現象的總稱。”③民國時期安徽災害最直接、最顯著的特征,便是其危害的程度十分慘烈。以水災而言,民國37時間內,安徽共發生大小水災27次。其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房屋倒塌、田產毀滅、財富喪失、難民產生、人口死亡。
自然災害的發生有時很難預料,比如地震;但有很多自然災害還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比如亂砍亂伐導致的山洪、泥石流之類。不管哪種自然災害,只要發生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后續的賑災,幫扶救助,人類是可以戰勝自然災害的。那時的政府雖也在局部范圍對災害有一定程度響應,但相比實際需求仍是很微弱的聲音。
二、人禍:社會局勢常混亂、戰爭不斷。
近代中國的各類戰爭、軍閥的橫征暴斂、土匪的掠奪以及繁重的苛捐雜稅等,進一步加重了天災的嚴重程度,人禍的同時往往會帶來不盡的天災,二者是有密不可分的聯系的。
首先是戰爭導致的混亂社會局勢,直接對水利政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國內政治混亂,內爭迭起,對于天災之預防補救,絕不注意,故水、旱、風災,亦成為農民之最大痛苦”④。比忽視天災預防與救災更為嚴重和痛心的問題是為軍事目的而破壞掉原有堤壩的行為。例如:1926年7月21日蕪湖堤壩被破壞時,周邊一帶耕地及人畜生命受害頗大⑤。1938年6月6日鄭州花園口大堤遭到破壞時,造成淮東地區洪水泛濫,皖北18個縣被洪水淹沒,光是恢復就用了9年時間②。正所謂“大兵之后,必有兇年”⑤。這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給予安徽社會經濟以沉重打擊。
其次是活動在安徽境內的從事暴力行為的土匪,其主要活動在巢湖周圍和淮北、泗縣、天長等地區。據報道:“巢湖一帶就有三股土匪,近三千人槍,經常攔劫商人,打家劫舍,有些匪股多達萬人,明目張膽地打家劫舍,殺害人民。”⑥軍閥和土匪們的暴行,破壞了行政與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破壞 給水利行政和水利建設等方面,帶來惡性影響,人為加重自然災害影響。
上述人為因素成為比自然因素誘發更大災荒問題的原因。因政府根本不重視,在當時的背景下也實難以重視對人為因素的控制和預防,這勢必惡性循環,導致更嚴重災荒,造成更慘重的社會損失。
三、影響。
近代以將,安徽災荒的頻繁發生,它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是多方面的,也是難以確切統計和估量的。當然也有一些其它
其一,造成人口的死亡和流移。據1935年調查,在離村的總人數中因自然災害而離村的即占50.9%。⑨況且,“離村的農民,不只局限于向省內城市遷移,同時也向鄰省的發達城市或開墾活躍的地區轉移。”①這樣,直接導致災區的農業勞力減少,從而嚴重影響到災后生產的恢復和家園的重建,也導致了城市人口的畸形發展。
其二,引發物價,特別是糧價的上漲。災荒發生后,容易造成物質相對匱乏,一些地主及商販趁機囤積居奇,哄抬糧價,他們從中大發其財。政府的不加控制,甚至從中漁利,更加劇了百姓苦難。
其三,導致田地的嚴重荒蕪。據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對安徽二十七縣的調查,1934年二十七縣荒地面積達1800余萬畝,占當時全省耕地面積的25%左右。1935年與1913年相比,全省人口增長了15.3%,但耕地卻不斷減少。1927年至1937年,包括安徽二十七縣在內的十四省八十九縣,開墾荒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8.9%,而耕地荒廢卻占耕地總面積的10.64%。②
天災和人禍緊密相連,共同對社會經濟產生巨大不利影響,成為社會發展的重大制約因素。這些災荒嚴重影響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從而破壞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造成整個近代安徽經濟秩序的紊亂。自然災害還為土匪和各種非法組織的出現提供了一張溫床,數以萬計無以為生的災民組織或參與的土匪及非法社會組織,嚴重危害了正常的社會秩序。
總之,災荒頻仍是鉗制近代安徽經濟發展,滯緩近代安徽城市化進程的重大因素之一。當然其中一些客觀影響,如災民的空間流動和心理變動也是值得思考的。其中很多經驗教訓今天看來仍有很多積極的借鑒意義。
[1][韓]金勝一:《近代安徽地域性災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為例》,《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2]程必定編:《安徽近代經濟史》,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第210、37、312、241頁.
[3]鄭功成:中國災情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2頁.
[4]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第617、886、886頁.
[5]《向導周報》164期,東京大安社影印,1926年7月21日,第16、27頁.
[6]《大公報》1931年1月3日,1932年7月5日.
[7]洪回:《安徽省水災查勘報告書》,民國20年第9頁.
[8]周文彬:《本年幾種農民糾紛的研究》,《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三輯,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第194頁.
[9]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上海:三聯書店,1957,第892、8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