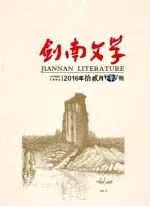周立波現象的“文化解碼”
谷寧 譚德晶 中南大學文學院 湖南長沙 410012
周立波現象的“文化解碼”
谷寧 譚德晶 中南大學文學院 湖南長沙 410012
2008年底,梳著小分頭,穿著得體西裝的周立波因創作以上海話為主、普通話為輔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我為財狂》等走紅全國,接下來他因拒上春晚、《壹周立波秀》在全國掀起了“周立波”現象,如何在文化領域對這一現象進行解析,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內容。
周立波;現象;文化;解碼
周立波,一個聲稱“我只適合在吃大米的地方立足,不適合在吃饅頭的地方立足”“我只是上海人民的小菜,趙本山才是全國人民的水餃”的上海男人,在 2008年底,因其創作以上海話為主、普通話為輔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我為財狂》等走紅全國,2009年底更因其拒上春晚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在2010年的《壹周立波秀》里他改變風格,以普通話為主,在幾個電視臺輪番播出,掀起了一陣陣收視高潮。
對這樣一個人,大眾褒貶不一,有人說他敢說真話,敢批判現實,是上海人民的驕傲,有人卻說他只是在嘩眾取寵,這就是所謂的“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但無論對周立波這個人持何種態度,誰也不能否認目前此人在全國的“火”,“周立波現象”在全國的風行。在文化領域,這種現象是大眾文化的代表、表現,因此在大眾文化領域對此現象的流行進行探討是很有價值的。
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悠久,其內容也必然復雜,但其中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中心,那就是千方百計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眾的思想與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則,則視為離經叛道。其典型代表就是古代的“文字獄”、當代的“文革”。從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有意或無意沒有與官方思想或者說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而受到迫害。但是近二十年以來,這種現象有了很大改觀,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思想也逐漸解放,官方在一定程度上賦予大眾一定的話語權和一定的言論自由。可是這些權利和自由都局限在一定的范圍內,誰也不能超越。人們并不能真正做到“心口如一”,特別是一些處在特殊位置上的人。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話、空話、套話。如我們每天所聽所見的CCTV等電視臺、人民日報等報紙上的各種聲音、各種文章。評論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個人,他們都是站在官方意識形態的立場,代表的都是黨中央和廣大群眾。而正是他們口中所謂的廣大群眾對這些人、這些節目、這些文章已經麻木,這些東西激發不了大眾的興趣。雖然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更多的人能在網絡上自由發表意見、評論,但這畢竟是在網上,而不是在現實生活中,從而少了一份真實感與認同感。另外,在網上也不是絕對自由的,被“和諧”的東西也不少。埃塞俄比亞有句諺語,“當偉大的統治者經過的時候,明智的農民會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建國60年來,從餐桌圍爐,到手機網絡。譏諷時政,調侃領袖的笑話,就是糧食斷絕的時候,也從未斷絕過。但在舞臺上,錢越多,趙本山們就越嘲諷弱者,不嘲諷強者。范偉們就只忽悠江湖,不指向廟堂。久而久之,人們迫切希望有個公眾人物能站出來,能公開傳達一些與眾不同的信息,敢于表達一種不同的聲音。“時代造就英雄”,和諧社會需要有人給現實一些諷刺和針砭,周立波順應時勢站了出來,因而成為了“英雄”。他從嘲諷弱者,轉向嘲諷強者;從媚俗,轉向刺秦;從忽悠百姓,轉向針砭時弊;從央視的形式主義方言,轉向舞臺上的地方主義本位。
周立波用笑來突破言論禁區,以娛樂的幽默軟化僵硬的政治,他調侃毛澤東、江澤民、溫家寶等領導人,也觸及文革、雷鋒,甚至是共產黨和臺灣問題。發表“領導怎么會無知呢?當然大多數無知的都是領導,這就叫大智若愚!”“對于倪萍的不反對不棄權,周立波建議她參與政治協商時至少要假裝討論”,“先謝國家再謝爹媽,雷焦人民,這位提案者肯定是官腔打多了,想讓全國老百姓跟他一起打官腔”,“兩會代表思想過于天馬行空,兩會代表兩種出路,要么和群眾打成一片,要么被群眾打成一片一片”這樣“大不敬”的言論。這些行為、言語是絕大多數公眾人物不敢公開表達的,卻也是深得民心的。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中國,“官”,特別是“大官”的軼聞軼事是廣大群眾最為喜聞樂見的。若有人能對這些“大人物”進行調侃、諷刺,即便這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和當前執政者對著干,他的這種言語也能迎合大多數人的心理,受到大家的歡迎。因而也就有上海學者李天綱所說的,趙本山可以不談政治,周立波不能不談政治。周立波要是不談政治,他就很難成功了。
“大眾文化這樣看來,就是一種不要思想,只要感性;不求深度,只求享樂,而且是坐享其成,不要觀眾動腦筋參與的逃避主義文化。”觀眾坐在電視機前,就能感受到周立波帶來的種種歡樂,被空話、套話蒙蔽的空虛的心靈得到了暫時的滿足,內心的各種不滿、不平衡情緒在表面上得到了宣泄。“事實上這是逃避現實。我是一個現實的人,我知道現實是不同的。有時候我真想同他們一道嚎啕痛苦一場。為什么不?這樣我其他那些久被封閉的情緒可以有個發泄口。”阿多諾認為電視的欺騙手段主要是一種“偽現實主義”,絕大多數人其實知道周立波這樣做的真正目的是追求收視率,追求經濟效益,現實并不會因為他這幾句話而發生改變,但聊勝于無,沉醉于這樣一種“偽現實”能帶來心靈的暫時解脫,能讓自己活得輕松點,獲得一種心理上的短暫平衡,何樂而不為呢?周立波自己也曾坦誠說,他不是學者,他的職責是讓大家笑。于是周立波火了,追捧他的人越來越多了,他的演出場場爆滿,甚至還有人不遠萬里坐飛機赴滬去看他的表演。
周立波的走紅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他自己及他節目本身的魅力。他的節目“及時性”非常強:白天股市跳水,急煞股民,晚上一定成為周立波的笑料;小布什白天被記者扔鞋,晚上就被周立波調侃;南韓前總統盧武鉉自殺,晚上周立波就作點評;金融海嘯的原因,什么叫次貸危機,被他演繹得既透徹又輕松。在他引發的笑聲中浸透的不僅是快樂,還有對社會現象、對社會事件的回味和反思。他以自己特有的思維,提供給觀眾新的、多視角的思考。
周立波給人們帶來了歡笑,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逄增玉甚至認為周立波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文化生態,有利于喜劇文化生態均衡。但按照阿多諾的觀點,這“是一場騙局,它的承諾是虛假的,它提供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虛假的快樂,它是用虛假的快樂騙走了人們從事更有價值活動的潛能。”馬爾庫塞也認為這是虛假的需要,“表面上看是投其所好,實際上卻是束縛了大眾的創造力和辨別力,使人們無以發覺自己是身患痼疾,從而錯過治療,終而是沉溺在郁郁寡歡之中。”周立波把民間輿論搬到了舞臺上,說出了大眾不敢在公共場所說的話。從感官上會讓大眾有一種“痛快”的感覺,不過也只是暫時痛快,很多人是一覺醒來繼續回歸麻木。他并沒有給人們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也沒有呼吁大眾一定要行動起來去反抗一些不合理的現實。相反,他導致了一些沒有判斷能力的大眾沉溺在那種虛假的快樂中,他是用虛假的需要和解決辦法代替真實的需要和解決辦法。
但其實很多觀眾除了收獲快樂外,也能透過歡樂的表層體會到其中蘊藏的某些深意,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大眾觀眾并不純然是無意識的,并非麻木不仁,對銀幕上的東西不作分析全盤接受。”徹底麻木的人肯定存在,但只是少數。更多的人還是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鑒賞能力,也有對國家、民族的危機感、使命感,他們希望通過周立波表達自己內心的渴望,也希望通過周立波多多少少改變中國一些不合理、不利于國家長足發展、不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最起碼能給某些人敲敲警鐘。無論他們的愿望能不能實現,有這些期盼總比一味沉迷于虛假的快樂要好。因此,周立波的走紅,周立波現象的風行,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在當前這個商業社會,面對經濟利益高于一切的現實,我們不能要求過高,更別說苛求了。周立波能起到一點啟發作用,大眾也應該滿足了。
有些人奇怪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力提倡和諧的國家,周立波怎么還沒被“和諧”掉呢?畢竟他的很多言語行為已經觸及到官方意識形態的痛處了。倘若周立波是生活在古代或者“文革”時期,他應該已經受到處置了。但時代不同了,人們看問題的方式改變了,統治者也不再那么死板了,何況周立波的所說所為相對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是無傷大雅的;而且他這種模仿肯定是有思量的,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自己心中不要尖刻,要坦蕩。我學領導人,有人就為我擔心,有的就斷章取義,我一點都不怕,說你把原始資料調出來看。因為我對整個語言、語氣的把握,包括上下文、深淺,應該是拿捏得很準的。”因此他并沒有觸怒當局。溫總理知道周立波在觀眾喜聞樂見的演出中模仿他,并沒有動怒,反而在一個會議場合,他說上海有一個周立波,把我調侃了一把,而我也心平氣和的接受了。中共中央常委李長春到上海調研時也指示:周立波現象值得研究,對中國的文化發展要進行反思。上海有關部門還專門組織了研討會來討論周立波現象,各方反應都很正面。
周立波沒有被封殺的原因除了以上幾點外,最根本的就是當前中國文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控在官方手中,而根據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霸權之廣被接受牽涉到社會中的主導集團對他的下屬階級作出的一系列讓步和妥協,只要讓步不對它大一統的支配構成威脅。”既然周立波的言行沒有對這種領導權構成威脅,領導者又何必找他的麻煩呢。更何況這正好又在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中國領導者的肚量、政治的民主、氛圍的寬松。這會讓人們感覺到身心的自由,更加擁護當局統治了。可能周立波也是察覺到了這一點才會這樣“放肆”吧。但同樣根據這個理論,也可以預知周立波不會有更加驚世駭俗的話語舉止出來了。他只能做到在一定程度上調侃政治、諷刺現實,再進一步,領導者們不會同意了,他們之前的妥協是因為周立波沒有威脅到他們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的至尊地位以兩種方式展現自身,其一是‘支配’,其二是‘知識和道德領導權’。”無論是誰,只要霸權即領導權受到了惡意的挑戰,領導者們絕對會作出反應。周立波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經歷了那么多,他深諳領導者的心理,他完全知道接下來他應該做什么,有哪些是他絕對不能做、不能說、不能觸碰的。除非他想消失在這個舞臺上,否則他不會做出危及到自身及自身利益的事。其實周立波早就說過:“這個不能學了,再學就被抓進去了。”但因為他的語氣,他接下來的行為,以及當時舞臺上的那種氛圍,很多人將這句話視為了玩笑話,可這真切地體現了他的心里。
周立波是一個充滿了爭議的人物,由他所帶來的這種現象在大眾文化領域還是一個挺新的話題,但他的流行完全可以在大眾文化理論中得到解釋,對他這種現象的“文化解碼”還在進行中。
[1]南方人物周刊.
[2]陸揚.《大眾文化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8頁.
[3]同上,第97頁.
[4]同上,第45頁.
[5]同上,第48頁.
[6]同上,第55頁.
[7]同上,第66頁.
[8]同上,第64頁.
谷寧,(1987.5--),性別: 女, 籍貫:湖南湘鄉,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譚德晶,(1954--),男,籍貫:湖南常德,中南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