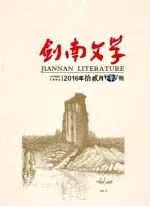美麗與悲哀
——論沈從文與川端康成小說的死亡主題
孫艷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
美麗與悲哀
——論沈從文與川端康成小說的死亡主題
孫艷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
“死亡”是沈從文與川端康成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共同主題之一,川端康成三分之一的作品都蘊含濃烈的死亡色彩,而沈從文的小說,也多次寫到死亡,沈從文和川端康成作為20世紀的著名作家,在他們描寫死亡的作品中,共同詮釋了他們對人類生存與死亡這一問題的理解與思考,但由于文化的差異,個人情況的不同等又使他們以各自的表現方式來書寫那形形色色的死亡故事。
沈從文;川端康成;死亡;美
從理論角度出發,死亡是我們每個人認識世界乃至自身的必然途徑;從情感角度出發,它又是一種美麗與悲哀的情愫;然而,從現實出發,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們對死亡懷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可是,在沈從文和川端康成的小說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對待死亡的淡然。川端康成的童年,父親、母親、祖母和姐姐相繼離世,十六歲的時候祖父也離他而去,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在《獨影自命》中處處流露著孤兒的悲哀之情。也許正因為對死亡的印象過早地印于腦海,讓他得以在日后的小說創作中對死亡這一個主題的把握較為自如,情感表現方面較淡然。川端康成經常引用古賀春江的一句話,“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來說明他認為“藝術的極致就是死滅”,他的作品總是把死亡意識轉換成審美體驗可能把握的藝術對象,并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情感邏輯去闡釋和表現。沈從文少年時期,也是經常看到死人的,小時候,他和父親到街上看到了一大堆血污的人頭,15歲從軍后,殺人場面對沈從文來說已是司空見慣,這些死亡印象深深地刻在他童年的腦海中,也許是對生命的毀滅見得較多,沈從文在小說中可以比較自然地談論死亡。
沈從文和川端康成的很多小說都是在較平和的敘述中來個突轉事件,而這種突轉常是以死亡為契機的,這些死亡又帶有極大的不可測性,并以此推動情節發展,與欣賞者的期待結果相違背。如沈從文的小說《邊城》中天保突然溺水而亡,老船夫生前的愿望尚沒有實現就在一個雷雨交加之夜默默地死去了。川端康成的小說也是如此,《雪國》中美麗、單純的葉子就那么靜靜地“落”了下來,《睡美人》中老人在與睡美人共度良宵時突然死亡。但不同的是,沈從文的作品中,沒有刻意表現出來人物為什么要死,是怎樣死的,而是以隨意淡然的表現形式告訴我們死亡具有很大的不可測性和偶然性,表現出那人物頭上的不可抗拒的看不見的神秘力量,即命運。因此,他的作品中常常是沒有既定情節模式的,悲劇造成的原因很大一部分與命運扯上了關系,透出一股悲哀和憂郁。如《三三》中單純可愛的少女三三那羞澀的夢隨著城里來的白面少爺的突然死亡而被打破,一切又恢復到原來的樣子,雖然生活依然是那樣平靜,然而卻著實透出一種淡淡的哀情。讀沈從文的小說,給我的感覺是美中帶有哀愁,而川端康成的小說給我的感覺是悲哀中帶著美。
美中帶著悲哀和悲哀中帶著美是不一樣的感覺,沈從文先生面對死是悲憫的,盡管他在對死亡的探尋中,發現了存在虛無的一面,但他并沒有放棄對生命意義的追尋,意欲在有限中追尋無限,從而使生命意義得到升華。沈從文以客觀的描摹態度和冷靜的敘述風格,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死亡故事,其目的正是想通過死亡來傳達出對人生的擔憂和對存在的思考。在他這里,死亡成了開啟生存這個隱藏體的一把鑰匙,最終的指向仍是存在,因此,我認為沈從文先生的人生基調總的來說是樂觀的。而川端康成的小說中呈現出來的死亡意識表現出獨特的藝術格調和美學韻味,正是這種對美與藝術的狂熱追求,不僅影響了他的創作傾向,也制約了他的人生態度,最終他以含煤氣管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人生。大和民族似乎對死亡存在著一種隱在的向往,日本武士有辱使命往往選擇死亡,在日本人的審美目光中,死好像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流轉的生。川端康成是一個深深迷戀古典的作家,在他這里,死亡是一種美的極致,他筆下的人物,死亡似乎是美好的,川端康成本人也曾在《我在美麗的日本》的講演中聲稱:“有思想的人誰不想到自殺。”在川端康成的《雪國》中,死即美的意識表現得淋漓盡致。如作品中寫深秋的蛾子死后,掉落在地,“島村撿起來一看,心想,為什么長得這樣美呢?”在《千只鶴》中,太田夫人的死使她所有的“罪”都洗清了,就像她的女兒文子所說,她的母親死后,遺容好像更美麗了。而沈從文作品中的死亡卻不如川端康成的人物那么從容,死亡也不是一種美,而是一種無奈,伴著淡淡的凄涼。《月下小景》中兩個相愛的人為了守住永恒的愛情而雙雙殉情,《媚金.豹子.與那羊》中,媚金因為自己的心上人豹子爽約,而認為他背叛了愛情,以死殉情,遲到的豹子悔恨不已,也自殺,無奈中透出一股凄涼之情。
沈從文與川端康成的小說中死亡往往與愛欲糾纏在一起。《月下小景》式的苗族傳奇,《阿黑小史》、《爹爹》式的鄉村故事,在敘述者淡淡的感嘆中,完成了愛欲與死亡的交錯,這種糾纏既在血緣親情中流淌出來,也在男女之愛中清晰地浮現出來。川端康成的小說中也出現了這種愛欲與死亡的糾纏。《日兮月兮》中的朝井,在妻子與人私奔后,曾多次向女兒表明,雖然不阻攔女兒去看望自己的母親,但自己絕不原諒妻子。但事隔幾年,同妻子相遇后,劇烈的情緒波動卻引發了腦血栓死去,可見,朝井對妻子的愛從沒有消失,正因為愛的深刻才產生了強烈的恨。川端康成與沈從文的小說中愛欲與死亡的糾纏有著不同的意義指向,沈從文先生的小說,愛欲與死亡的糾纏表達的是一種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對人生價值的渴求。就像是《月下小景》中的男女主人公,他們深愛著對方,但卻受古老、粗陋的風俗的阻礙無法在現實中達到愛情靈與肉的高度統一 ,因此他們選擇了在月下相擁而亡,死亡升華了他們的愛,實現了他們一直堅守的永恒愛情的價值。但在川端康成的小說中,死亡阻斷了愛欲,又使愛欲以曖昧的方式轉化并且延續,這種延續并不是互愛的雙方對所愛者的癡癡不忘,通常是一方以記憶的方式將自己的情感移植,因此這種被移植的愛也就帶有了強烈的單向性,甚至成為一個人對愛的狂熱追求。
沈從文與川端康成的小說死亡與愛欲的糾纏恰恰也表現出他們二人共同的愛的關懷,他們重視人物內在愛的價值。在沈從文與川端康成的筆下,死亡的人物通常只是小人物,他們要么突然死去,要么為自己死,為愛死,基本不存在為他人犧牲的情況。他們小說中的人物沒有耀眼的光芒,是那么的真實,即使死,也是安安靜靜的,就像當初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一樣。沈從文和川端康成注重真實的人性,他們肯定人的自然欲求,他們小說中的人物自然不受太多束縛,為自己活著。如沈從文《野店》中黑貓從不掩飾自己的欲望,她需求的是“暴風雨后”的酣暢。但是,沈從文人性觀的格調可以說是追求“性美”的,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沈從文比川端康成來得更率真,更健康,更有活力,而川端康成作品中部分人物展現給我們的頹廢變態性心理遠不及沈從文作品中對人性的張揚給人的純美的遐思更健康活潑,更富有情調。盡管沈從文對那些被世俗惡化的情欲,根本不打算作倫理的衡量,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同意其筆下的人物去制造紊亂的性愛,從小說人物人性深處涌出的真情中,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在有意忽略的倫理衡量中卻實有倫理的自覺,這或許仍是中國傳統的一些思想在影響著他。不管怎么說,川端康成與沈從文這種大膽寫生,大膽寫死,執著于人性真實的精神是令我十分佩服的。
[1]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M].葉渭渠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2]沈從文.沈從文精選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3]川端康成.睡美人[M].葉渭渠,唐月梅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4]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5]沈從文.沈從文選集(第11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
孫艷,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2009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