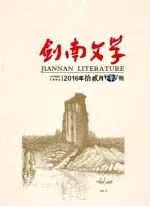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雜史可廢乎?”
——對《一士類稿》的重新體認
崔亞強 四川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 四川成都 610064
“雜史可廢乎?”
——對《一士類稿》的重新體認
崔亞強 四川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 四川成都 610064
近代名士徐一士所著《一士類稿》,內容多屬掌故雜史。但通過該書,對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能有更新更深的認識,對史料學的發展和歷史研究范圍的拓展也起到啟示作用。
徐一士; 《一士類稿》; 史料
《一士類稿》作者徐一士(1890——1971),原名仁鈺,字相甫,號蹇齋。出身仕宦之家,祖籍江蘇宜興。該書以記載清末掌故為主,所記人物有文壇學界名宿如章太炎、陳三立等人,有靖港之役、咸豐軍事史料等,多為作者親身見聞。其子徐澤昱觀之,其書“寫人物,除廣集翔實資料,詳加剖析,去偽存真之外,對臧否人物極為慎重,堅持客觀嚴正公平態度,決不妄立一家之言,妄加褒貶”。更如孫思昉序中所言:“宜興徐君一士,當世通學也。從事撰述,多歷年所,先后分載雜志之屬。凡所著錄,每一事必網羅舊聞以審其是。每一義,必紃察今昔以觀其通。思維縝密,吐詞矜慎,未始有毫末愛憎恩怨之私凌雜其間。于多聞慎言之道,有德有言之義,殆庶幾焉。而有清一代掌故,尤所諳熟。”通觀該書,對當下的歷史研究亦能開辟一新視角;再者,該書對清末民初政界、學人記述頗為翔實,或可對時事時人有些新的認識。
一、掌故之于史料,可取乎?
掌故常見于筆記一類的散集,這是中國史學中的一大特產,不僅可以補充所謂正史之不足,而且還可糾正正史中某些錯訛。但因其不登大雅之堂,在歷史研究中也處于尷尬的地位,但這類掌故筆記體裁的著作更能“貼近生活”,往往更能反映當時活著的社會狀況。
掌故是歷來筆記的一種,以談政治風俗文化為主,后人多視為野史類的史料,很少專門稱之為學問的。對于掌故的定義與內容,清末名士瞿兌之曾在為《一士類稿》一書所作序中論說到:“通掌故之學者是能夠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要達到這種目的,則必須對于各時期之活動任務,熟知其世系淵源,師友親族的各種關系,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于許多重復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所以既稱治掌故,則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對。”
可見,掌故實為歷史研究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只是需有超乎常人的甄別眼光,才能從林林總總雜亂無章的材料中發現真實。史料是認識歷史的基礎,歷史研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所使用的史料的。因此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費弗爾認為,在歷史研究中“必須利用人類一切創造物——語言、符號、農村的證據、土地制度、項圈、手鐲——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葛兆光也曾言到:“意識形態的壓力,價值觀與感情的好惡,思想與方法的偏好,時勢與政治的需要,歷史資料的缺失和殘存的偶然性都會影響歷史的敘述,不在場的陰影始終籠罩著在場的書寫者。”
王笛在《街頭文化》中就充分利用了一些大眾化的材料,“明清以來的地方諺語、民間文學、地方戲曲以及詩詞等,都可以作為史料來使用”。在研究下層民眾和大重文化時,我們完全可以在資料問題擴展我們的視野,并換一個角度來考慮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或許是史家自身認識的逐漸深刻,或許有西方史學思潮的沖擊,當今的史學界已明顯轉為“眼光向下”。但傳統史學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拓寬史料的發掘與利用范圍,《一士類稿》或許就是其中一例。
二、《一士類稿》對歷史人物的另面認識
作為當時聞名賢達而又有深厚史學功底的徐一士,《一士類稿》中涵蓋了各方面的社會顯達,如王闿運、李慈銘、章太炎、陳三立、胡雪巖、吳汝綸,還有像陳夔龍那樣的“勝清之顯宦,民國之遺老”,有“清季詞臣中著淹雅之譽”的吳士鑒,也有民初武夫段祺瑞、孫傳芳等,以正確甄別的眼光研之,必能發現正史所難以見之另一面歷史。本文選取該書記述左宗棠與梁啟超等人的文段進行研讀,試圖對這些聞名當世、影響后背的巨人有重新認識。
徐一士將左宗棠與梁啟超并舉,“似頗突兀”,而作者另有深意在也。“余以其均為清代舉人中之杰出者,早有大志。對于仕宦,則左氏志在為督撫,梁氏志在為國務大臣,后各得遂其愿。此點頗為相似,故并述之”。左宗棠中舉人后,會試三次不第,即放棄科舉而專治經世之學,知交群推,有名于時。后逢咸豐年間戰局紛亂,居湖南巡撫幕府,用兵、籌餉諸務,實主持之。后曾國藩力保左氏為岳州同知府,而左宗棠則辭曰:“知府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為難,不可為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之大權,殊可展布。”言辭之間,其人之豪氣霸氣暴露無遺。再讀梁啟超之言論,民國肇興之后,國民政府力邀梁氏入閣組建政府。熊希齡組建內閣政府,邀請梁啟超入職,他辭曰:“若梁某人者,除卻做國務大臣外,終身絕不做一官者也。然茍非能實行吾政見,則亦終身決不做國務大臣者也”。
最終二人皆得償所愿。左宗棠由浙江巡撫而升任閩浙總督,次遷陜甘總督,平定西陲叛亂,終成一代功業;梁啟超先入熊希齡內閣之司法總長,后為段祺瑞內閣之財政總長,在國務員之列,亦可說達到其要求了。然而,徐一士對二人的評價卻大不相同。梁啟超“其人不愧為政論家之權威者,筆挾情感,善于宣傳。每發一議,頭頭是道,其文字魔力,影響甚巨。而政事之才,實極缺乏,故必勝之所成就,終屬在彼而不在此耳”。他認為梁啟超無政治才干,但有政論才華。至于左宗棠,徐先生則大加褒獎:“若左宗棠之如愿而為督撫,所自效于清廷者,武略則平靖內亂,戡定邊陲,政謨則盡心民事,為地方多所建設,自另是一種實行家之卓越人才矣。”
《一士類稿》中關于二人的此類言論,是一般史籍所難以覓見的,或可補正史之闕漏,亦可對二人有一新的認識。
三、結語
“對于大多數歷史學家來說,一提及‘史料’,就會聯想到歷史文獻。事實上,歷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也恰恰是建立在對文字史料的研究基礎上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文字史料都是歷史研究最豐富的資源。然后卻不是認識過去的唯一路徑。還有其他類型的史料,我們決不可以忽視,否則,過去——至少部分——就會對歷史科學形成封閉”。很明顯,“凡事能夠對過去的問題作出某種解答,有助于重新和深入認識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史料,都應善加利用”。如《一士類稿》之類的筆記體、掌故體著作,對于歷史研究來說,作為一種豐富的史料資源。在眼光和視角轉換后,或能發現一片歷史研究的新天地。
[1]徐一士.《一士類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
[2]王笛.《街頭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楊念群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