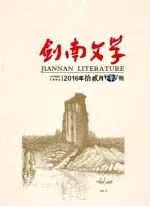蘇曼殊愛情詩的現代審美意蘊
徐旭水 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
蘇曼殊愛情詩的現代審美意蘊
徐旭水 上海財經大學浙江學院
愛情詩是蘇曼殊詩歌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試從文學觀念、創作實踐、詩歌風格、描寫內容、悲劇意識、女性觀念等幾個方面,論證蘇曼殊愛情詩歌的現代審美意蘊。這種現代審美意蘊受時代風潮和作家創作觀念的共同影響,是蘇曼殊愛情詩的顯著特征。
蘇曼殊;愛情詩;現代;審美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蘇曼殊無疑是一位有著特異的魅力與光彩的人物。在他三十五年短暫人生旅途中,約有二三十種作品流傳于國內外。僅就詩歌而言,據馬以君統計,現存五十題一百零三首,確證的三十九題八十九首。 這些詩作中,“言情篇什居十之九”, 如《寄調箏人》、《調箏人繪像》、《調箏人將行,囑繪〈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題〈靜女調箏圖〉》,以及傳誦一時的《本事詩》十首,系為日本藝妓百助眉史而作;《春日》、《有懷》、《集義山句懷金鳳》等是寄給秦淮歌伎金鳳的;《失題》、《過若松町有感》、《櫻花落》等是悼念已故日本情人靜子的;《無題》八首記與上海妓女花雪南的交往;《為玉鸞女弟繪扇》中的玉鸞“大概也是曼殊的女朋友了”, 而《東居雜詩》十九首,則反映了民國初蘇曼殊在日本養病時與國香、阿可、湘痕、真真、棠姬、阿蕉等日本女子的來往。愛情詩在蘇曼殊的詩作中占了很大比重。
抒寫愛情本是中國詩歌的傳統主題。但是,近代中國天崩地裂的歷史背景卻賦予了這一傳統主題以新的時代內涵。作為這個時代的歌者,蘇曼殊身處新舊交替的矛盾漩渦之中,集進步與落后、開明與保守于一身。當他把激情傾注于詩歌創作中,便使得愛情詩呈現出獨特的審美意蘊。這是一種新的審美意蘊,既源于時代風潮的折射,更出于自覺的審美追求,在多個方面都體現出現代性傾向,開掘了傳統題材的新深度,富于現代審美意蘊,進而成為了蘇曼殊愛情詩的顯著特征。
蘇曼殊愛情詩的現代審美意蘊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文學觀念: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
作為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拜倫和雪萊曾經對一代中國詩人產生巨大影響,魯迅先生所謂“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
拜倫出生于倫敦破落的貴族家庭,10歲繼承男爵爵位,成年以后成為19世紀初歐洲革命運動中爭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一名戰士。 1823年初,希臘抗土斗爭高漲,拜倫放下正在寫作的《唐璜》,毅然前往希臘,1824年4月19日死于希臘軍中。雪萊則是與拜倫齊名的民主詩人。出身鄉村地主家庭,20歲入牛津大學,因寫反宗教的哲學論文被學校開除。投身社會后,又因寫詩歌鼓動英國人民革命及支持愛爾蘭民族民主運動,而被迫于1818年遷居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仍積極支持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1822年渡海遇風暴不幸船沉溺死。
蘇曼殊深受拜倫與雪萊的影響。其《本事詩?三》云:“丹頓拜輪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朱弦休為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語誰?”將但丁和拜倫作為自己的師承所在。在《題拜輪集》一詩中,對于拜倫則更有一種同情的理解:“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吊拜輪。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對于雪萊,蘇曼殊也極為推崇,其《題師梨集》云:“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瑯玕欲報何從報?夢里煙波認眼波。”《燕子龕隨筆》又云:“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流麗,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比,其詩格蓋中土義山長吉而熔冶之者。”而柳無忌則說:“他對于拜倫和雪萊這兩個人,雖然偏愛拜倫,但他本人卻似乎更像雪萊——一個展翅欲飛但卻徒勞無功的天使。”
蘇曼殊對拜倫、雪萊的推崇直接影響到了他的文學觀念,他能夠自覺地將西方文化的影響運用于創作實踐,其愛情詩中所彌漫的浪漫氣息與拜倫、雪萊的詩風有著高度的相似之處。熊潤桐在《蘇曼殊及其〈燕子龕詩〉》一文中曾經指出:“曼殊之于調箏人,尤拜輪之于雅典女郎。拜輪集中有《留別雅典女郎》詩四章,幽艷入骨,為抒情詩之杰作;而曼殊《燕子龕詩》里面也有幾首詩是為調箏人而作的,其一往深情,很足以和《留別雅典女郎》詩相頡頏。”從內容到形式,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都對蘇曼殊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創作實踐:資產階級創作自由觀的指導
在《〈潮音〉自序》中,蘇曼殊說:“拜倫和師梨是兩個英國最偉大的作家,兩人都創造同戀愛底崇高情感,當作他們詩情表現中的題目……師梨和拜輪兩人的著作,在每個愛好學問的人,為著欣賞詩的美麗,評賞戀愛和自由的高尊思想,都有一讀的價值。”在《拜輪詩選自序》中,他贊美拜倫“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見蘇曼殊推崇拜倫、雪萊,首先著眼于他們反抗君主專制,追求民主自由,這恰與蘇曼殊投身中國民主革命的追求相同。而拜倫、雪萊追求人類的戀愛和自由的不懈努力,更深入影響了蘇曼殊的自由觀。
蘇曼殊對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愛情詩創作中,表現出了明顯有別于前人的特點。前人所提倡的“獨抒性靈”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從儒佛兩家體系中提煉出來的主觀唯心論,基本上屬于封建主義的范疇。而蘇曼殊所熱烈呼吁的“Love and Liberty”, 則是資產階級自由觀念的產物。正因為此,蘇曼殊的情僧形象,與文人士大夫的狹邪冶游有了本質的區別。他以僧人形象出入于紅塵世界,大膽歌頌那些“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的藝妓,“丈室番茶手自煎,語深香冷涕潸然”的戀人,“露濕紅蕖波底襪,自拈羅帶淡蛾羞”的少女,視傳統道德規范如無物,表現出了沖決封建文藝專制主義在創作過程中的精神桎梏的巨大勇氣。
三、詩歌風格:“清新的近代味”
蘇曼殊的詩歌用詞纖巧,擇韻清諧,郁達夫稱之為“清新的近代味”。 郁達夫所說的“近代”顯然有別于當下意義的“近代”,而更接近于“現代”。他指出了蘇曼殊詩歌在風格上的特點,語言通俗流暢、清新自然,更接近于現代白話。這種詩歌語言能夠跳出宗唐祧宋的樊籬,表現在愛情詩中,多以綺語入詩,一往情深,幽艷入骨,既沒有冷僻的典故,也沒有艱澀的語調和崛峭的結構,與同光體詩人大異其趣;同時,他的情詩色彩明艷,風格纖秀,富有韻致,亦有別于南社諸子大聲鏜錔的面貌。
蘇曼殊的這種詩風,頗為接近他的畫風。蘇曼殊畫桃花,往往直接蘸取女郎唇上的胭脂,所以畫幅上的氣氛,每每凄艷逼人,令人難以仰視。在愛情詩中,同樣涌動著凄艷之情。如《為調箏人繪像》二首:“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沉哀。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后灰。”“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兩首詩中,出現了胭脂、青絲、華髻、梨花等色彩鮮明的意象,更以禪心鏡臺、沾泥殘絮的獨特組合,表現了百感交集卻又無法言說的哀愁,全詩既平易通俗,又含意深遠,于優美哀傷的語言中表現出邈遠悠長的韻致。再如《東居雜詩》之三,寫一位活潑、清純而嬌羞的少女:“羅襦換罷下西樓,豆蔻香溫語不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下學箜篌。”清新自然,風華獨絕,使人聯想起徐志摩的名作《贈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在詩歌的語言以及由此所營造的意境方面,兩詩竟有著如此高度的相似性。其它如紅葉女郎、桃花吟鞭、芒鞋破缽、紅泥僧寺,都是詩人獨創的意境,為他人所難言。
四、描寫內容:大膽真摯的感情表露
就愛情詩所表現的內容而言,傳統詩歌往往將這類題材處理得朦朧隱晦,難以指實,如李商隱的《無題詩》、龔自珍的《小游仙詞》,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且反映個人愛情生活的內容多集中于抒情作品,而絕少在敘事作品中直抒胸臆。
蘇曼殊身世奇特,經歷坎坷,再加以詩人特有的強烈激情,使得蘇曼殊的愛情詩具備了超越前人的容量。如其名作《本事詩》十首,直接以“本事”命名,抒情作品具備了濃厚的自傳色彩。詩歌描繪女子的美貌是“桃腮檀口坐吹笙”,描述自己的傷感是“我已袈裟全濕透”,再如寫與一位女子接吻的“偷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與女子并肩攜手漫步的“蘭蕙芬芳總負伊,并肩攜手納涼時”,俱是直陳其事,言人所難言。蘇曼殊對愛情描寫之大膽,在中國古典詩歌中,除了民歌,十分罕見。
就詩歌所反映的情感而言,蘇曼殊的愛情詩既表現出詩人對于愛情的沉醉與留戀,又反映出僧人對待愛情的無奈和決絕。他時而熱情似火,時而心冷如灰,感情十分復雜。如《本事詩》之六:“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之十:“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寫他對百助的情感,即飽含激情,又充滿愧疚。再如《過若松町有感》:“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庵夜半鐘。我再來時人已去,涉江誰為采芙蓉?”《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悲悼已逝的戀人靜子,感慨物是人非,死生契闊,其情感的強烈程度也遠遠超出了“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詩教標準,表現出了個性解放、情感解放的時代特色。
五、悲劇意識:對無望愛情的追憶與歌唱
悲劇觀的確立,是中國近代文學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有力的沖垮了傳統的“大團圓”的固定模式和“中和”為美的審美理想,反映了中國近代文學審美觀念的重大變革。在蘇曼殊的小說創作中,對傳統大團圓結局的背離是十分明顯的,而在蘇曼殊的詩歌創作中,同樣貫穿著這種新型的悲劇意識。如果說“以死作為結局的愛情至上思想” 是蘇曼殊小說的一大特色,那么深入表現無望的愛情則是蘇曼殊愛情詩的一大特色。
在《題〈拜輪集〉》的詩前小序中,蘇曼殊寫道:“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勖以歸計。嗟乎!予早歲披剃,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桐!爰扶病書二十八字于拜輪卷首,此意惟雪鴻大家能知之耳!”蘇曼殊雖然風流,骨子里卻是和尚,他的詩里雖然艷骨難收,心境又時時皈依禪悅。《寄調箏人》”說:“懺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就是明證。類似的句子還有:“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沉哀。”所以蘇曼殊不是一般的禪僧,準確地應稱之為情僧,情與禪抗顏接席地滲透在他的骨髓里。其因緣在哪里,不能不追溯到他的悟性、他的個性及為人。曼殊從來襟懷灑落,不為物役,加上他早年即悟禪悅,稍長又萬里擔經,漂流異域,病骨支離,真所謂“深抱幽憂之疾者”。所以他的詩一方面油壁香車、紅葉女郎、艷氣四射,一面又悟盡情禪、傾心空門、無限感慨。這正是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了。一則執著,一則逃逸,二者相糾相繞,纏附愈緊,他的痛苦我們不難體察一二。這對于藝術,往往能創造出上品來,蓋因蚌病成珠,憂傷的、感觸萬端的心靈往往釀出藝術的美酒。
蘇曼殊對無望愛情的追憶與歌唱,或觸景生情,纏綿不盡,或睹物思人,別夢依依。如“人間天上結離憂,翠袖凝妝獨倚樓。凄絕蜀楊思萬縷,替人惜別亦生愁。”再如“多情漫作他年憶,一寸春心已成灰”,其對絕望心理的刻畫,對已逝戀情的追憶,往往動人心魄,催人淚下,表現出了強烈的悲劇意識。
六、女性觀念:建立在真誠、平等基礎之上的進步觀念
蘇曼殊愛情詩中女主人公,既有“獨立瀟湘浦”的淑女,也有“粉指印青編”的佳人,更多的是輾轉風塵的歌伎、藝妓。如金鳳,是秦淮歌伎;花雪南,是上海妓女;百助,是日本藝妓。蘇曼殊一視同仁的對待她們,不是俯視她們的不幸遭遇,而是仰視人性的善良、愛情的美好。純真的情感,平等的姿態、彼此的關懷,是蘇曼殊愛情詩迥異于前人的地方。
金鳳的從良,使他感到“盡日傷心人不見”;靜子的殉情,弄得他“無端狂笑無端哭”;百助的他往,叫他痛苦得“日日思卿令人老”;而花雪南的不遇,更令他苦悶到“瘦盡朱顏只自嗟”。蘇曼殊始終抱著同情的態度,設身處地感受她們的痛苦,安慰她們“碧玉莫愁身世賤”,感慨彼此“相憐病骨輕于蝶”。在他眼中,他與這些淪落風塵的女子是彼此平等的,他們的愛情正是建立在平等與尊重的基礎之上。因此,他才會喟嘆“我本負人今已矣”!更為“契闊死生君莫問”而無限傷感。這方面的典型作品,如《東居雜詩》第十九首:“珍重嫦娥白玉姿,人天攜手兩無期。遺珠有恨終歸海,睹物思人更可悲。”感慨攜手無期,佳人不再,其中所蘊含的感情是非常真摯和深沉的。
蘇曼殊給予了這些不幸女性足夠的同情與尊重,當他病重期間的1912年和1913年,這些歌伎也曾兩次到他病榻前探望,給了他一種安慰。1912年12月4日,蘇曼殊在給香港的一個朋友的信中說:“近日小病逆旅,舊友都疏,惟女校書數輩過存。不圖彼輩綴葉飄花,尚有故人之意。” 第二年,他在日記中記得相當具體:“癸丑十年十七日(1913年11月14日)午后二句鐘,周五、雪三、桐華、黛云臨存病榻,余默不一語。” 蘇曼殊愛情詩的女主人公從詩歌中走出,走向蘇曼殊的病榻,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蘇曼殊女性觀與愛情觀的進步色彩。他與這些女性的關系,建立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閃爍著一種新型的愛情觀和女性觀的光芒。
總之,正因為蘇曼殊的愛情詩具備了以上所述的現代審美意蘊,對于處在功利主義與審美價值二律背反之中的近代中國文學而言,蘇曼殊才會顯得如此卓爾不群。他的詩歌融時代風潮、人生經歷、愛情糾葛于一體,賦予傳統愛情題材以全新的時代特色,從而得到新舊文學家的共同喜愛,讓不同時期的讀者由衷贊賞。
[1]《燕子龕詩箋注》 馬以君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中國近代文學作家論》任訪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絳紗記〉之考訂》 柳亞子 中國書店 1985年版.
[4]《摩羅詩力說》 魯迅 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5]《蘇曼殊傳》 柳無忌三聯書店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