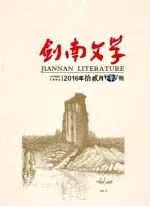淺談狐女意象所反映的蒲松齡女性文化心理
黃婉燕 平頂山教育學院 中文系 河南平頂山
淺談狐女意象所反映的蒲松齡女性文化心理
黃婉燕 平頂山教育學院 中文系 河南平頂山
《聊齋志異》中塑造的紅顏知己是作家在現實情感存在缺憾與科場失意后的自我設計與自我療救。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最重要的是象征著對書生人生價值、學識舉業的認同.蒲松齡創造紅顏知己的原因:一是科場失意后希望知己獎掖的真實心態的反映;二是對現實情感缺憾的藝術補償。
女性文化心理;象征意義; 聊齋志異 ;蒲松齡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通過一個狐鬼世界的建構來敘寫整個現實社會。
《聊齋志異》中的女性風姿綽約、千姿百態,不僅有獨特個性,還成為某個思想符號,某個精神象征,某個情感代表,是聊齋最亮麗的風景。《紅樓夢》用長篇小說的藝術形式創造了數十位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聊齋志異》用短篇的形式創造了幾十個成功女性形象。是中國古代小說人物畫廊的空前收獲。
一
人生難得一知己,這是中國古代文人先哲常有的共同慨嘆,蹉跎的處境,悲涼的情懷最易促使文人士子渴望知己。在《聊齋志異》中用理想主義的藝術手法創造的狐妖鬼魅形象,擔負著為他人彌補人生缺憾的角色。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的那樣“多具人情,和易可親”,人間社會成為這些“異類”的活動基地。并且都有一個愛情模式,翁容先生說:“窮困潦倒而具文才靈氣的書生邂逅一個甚至幾個麗絕人寰的異類女子,兩情歡好后,異類女子不僅讓書生享受到‘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樂趣,還任勞任怨地幫書生操持家務,生兒育女,幫書生度過難關,給他帶來財富、功名或是干脆與他共登仙界。”簡而言之,就是美麗的異類紅顏知己主動下顧貧寒士子。她們身上既有屬于女性獨特的倔強,又有傳統的善良品質,她們每個人都是心靈美與形象美的兼備者。
在蒲松齡筆下的女性雖然覺醒了,地位提高了,男女關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還透出了一些女性主義的光芒,但畢竟是在男性視角的籠罩下,其光芒是有限的,杜桂萍先生也說過:“盡管蒲松齡把這群清標脫俗的女性刻畫的血肉豐滿,但對孤獨的士子來說,她們更多地負載著一種象征意義:她們是一種價值認同、價值實現,惟其如此,眾多士子才會在男歡女愛中獲得心理上的平衡,超越精神上的孤獨感。”
從蒲松齡創作心態來看這些狐女形象,就會發現這些清新脫俗,美麗真誠,不貪戀財富地位,也不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女子,不正是科舉無望、苦悶至極的士子夢寐以求的嗎?同時不也是蒲松齡孤獨而悲傷的心靈深處所期待的嗎?文人士子渴望知己或援之以臂,或同情撫慰。所以像蒲松齡這樣一個懷抱利器渴求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子,科場的成敗決定了他一生的前途與命運,“得之則榮,失之則辱”,可蒲松齡在屢試不第的恥辱和無奈的現實中屢遭打擊而不能自拔,他在作品中大聲疾呼“千古嘆知希”。然而男性與生俱來就具有攻擊性的沖動,將軍、士兵可以把這種沖動發泄在戰場的撕殺、搶劫當中。官宦、貴族可以把這種沖動發泄在爭權奪利和魚肉人民上。書生類男人明顯處于受壓抑的狀態。為療救心靈痛楚蒲松齡只能把這種沖動發泄在文學作品當中,他的“孤憤”需要發泄出來,他需要一種精神慰藉和價值認同,于是他塑造出了狐女這一形象,泄導郁悶。之所以為異類,是因為這些人物可超脫社會固有結構之外而無法以禮教的準則衡量,蒲松齡內心的欲望便會自然而然地活躍起來。
對于眾多的士子來說,傳統的科舉之路是一個遙遠的夢。身邊隨手可得的愛情和美女能夠慰藉心靈,擺脫苦悶,那么棄功名而取愛情是理所當然的。紅顏知己用主動方式讓書生在男歡女愛中超越現實的不公平,得到感情的補償,找到一種與科舉功名截然不同的價值認同。美麗的少女主動追求窮困書生,體現了蒲松齡以及與他一樣的中下層知識分子作為男性的自尊要求和屢遭挫折之后的補償要求。
二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人在精神抑郁時所找的傾吐對象一般是異性而不是同性,異性之間心理互不設防,傾吐才可以“盡情”,在蒲松齡看來,文人落魄相當于英雄落難,都渴求“紅顏知己”的垂青,宋代的辛棄疾就抒發過“ 何人,喚取紅巾翠袖,問英雄淚”表達就是這種心情,當文人從男權世界里敗下陣來的時候就會到女性那里尋找精神的“母體”,獲得精神的再生力量,所以就產生了對女性的精神依戀,女性偶像就是文人的救贖象征,具有詩意的女性往往成為他們精神復合的載體,如俠女、細柳、翩翩具有女、妻、母三種女性的溫情,這樣溫柔持重的女性對落魄文人來說無疑是心靈的避風港,她們的出現主要是以危難性借女性這一載體獲得精神再生,但又最終超越載體成為精神獨立的“斗士”,他們的遇合只是曾經擁有而非天長地久。其實這類女性大多是蒲松齡心中“另一自我”,但是作為傾聽者的女性只是在文人蒲松齡心中“在場”,在現實中仍是“缺席”,其實仍是“得不到”,對女性傾訴欲越強就表明他們在現實中的孤獨之深,知音之稀。所以“孤寂之憤”才得以發。
《聊齋志異》中那些洋溢著青春氣息,活色生香的狐仙女鬼,用林語堂的話說,比現代女護士還要溫柔體貼,她們替“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宅瑟瑟,案冷如水”的落魄書生實現他們的美麗夢想,她們是書生心靈創傷的護理者和療救者,堪稱精神保護神,書生們“秋蟲自熱”對自己命運不服而去自我求證,而“狐仙毛遂自薦、青眼有加,如同昭示天命”,才使書生的“求證”有了質的突破,這對于原本精神委頓的書生來說,無異于重生之母。也就是蒲松齡在“青林黑塞間”去尋找到永恒的知己,也是用來慰藉屢遭打擊疲憊不堪的身心一種虛幻的價值認同,但不管蒲松齡怎樣謳歌美麗的女性和美好的愛情,怎樣表現出一種思想解放的姿態。這些女性形象都是他在男權話語編織的白日夢中充滿男權意識,寄托著無限希望的文化載體。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版.
[2]翁容.《﹤聊齋志異﹥情愛模式的深層意識 》, 明清小說研究(3)1996版.
[3]蒲松齡.《聊齋志異》齋抄本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版.
[4]杜桂萍.《孤憤﹤聊齋志異﹥的精魂》,蒲松齡研究1994年(1).
[5]張燕瑾.《中國古代小說專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
[6]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6版.
[7]馬瑞芳.《〈妖狐神鬼論〉——聊齋人物論 》, 中華書局2002版.
[8]俞汝捷.《<仙鬼妖人>——志怪傳奇新論》,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版.
[9]邁克?彭.《中國人的心理》邱海燕等譯 , 新華出版社199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