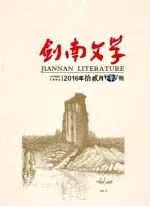從格律和時代精神角度看《愛情小詩》第75首
田艷艷 新航道英語學校
從格律和時代精神角度看《愛情小詩》第75首
田艷艷 新航道英語學校
詩歌的格律是詩歌的本質所在,一首詩的格律特點對詩歌內容的表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詩歌格律也標志著一個時代詩歌形式的發展階段。斯賓塞十四行詩《愛情小詩》第75首詩是一首有著獨特格律和時代精神的精美抒情詩,本文將運用Paul Fussell 的一些理論(如音步、格、韻、頓的理論)對其中的格律現象做淺析,并對其思想內容進行簡析。
格律;時代精神;十四行
引言:
埃德蒙?斯賓塞 (Edmund Speser,1552年-1599年1月13日),英國 文藝復興時期 偉大詩人,是從杰弗雷?喬叟過渡到莎士比亞之間最杰出的詩人,他出生于倫敦一個布商家庭,1569年入劍橋大學文學、哲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畢業兩年后便成為了貴族家的門客,同時結識了以菲利普?錫德尼爵士(Earl of Philip Sidney)為代表的英國創新詩歌的詩人。在這些詩人主張的影響下,他寫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作品.代表作有長篇史詩《仙后》、田園詩集《牧人月歷》、組詩《愛情小詩》、《婚前曲》、《祝婚曲》等,他的詩用詞典麗、情感細膩、格律嚴謹、優美動聽,對后世的英國詩人,包括彌爾頓、馬洛、雪萊、濟慈等都有很深遠的影響,他在詩歌形式方面他一向樂于探索,由于他技巧上用功夫,被后人稱之為“詩人的詩人”。他在組詩《愛情小詩》中他探索出了一種新的十四行格律形式,后被稱作“斯賓塞十四行”。
斯賓塞的愛情十四行至今仍是世界最優美的愛情詩。斯賓塞的愛情十四行是為了慶祝他與伊麗莎白.博伊爾Elizabeth Boyle的婚禮而作。其中斯賓塞十四行詩《愛情小詩》第75首詩在格律方面有一個獨特之處,那就是:它延續了與莎士比亞十四行相同形式結構:三組四行詩節加上一個對句,但它也保留了彼特拉克十四行中的邏輯結構—意義在第九行而不是在第十三行做了轉折;同時與莎士比亞十四行不同的是韻律,莎士比亞十四行的韻律是:abab cdcd efef gg,但斯賓塞十四行詩的韻律為abab bcbc cdcd ee。在思想內容上,斯賓塞的這首詩有個很明顯的特點,帶有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進步思想, 比如對個人追求幸福的肯定,比如認為精神的生命力要遠遠超出世間物質的東西,再如詩人的詩有著賦予世俗事物永恒生命力的信念.同時這首詩歌的主題也是關于當時較為熱點的話題——時間與愛的永生.斯賓塞的這首詩是個人身心的傾訴。本文將分別從這首十四行的格律特點的獨特之處和思想內容兩個方面做詳細的分析。
一、彼特拉克式的邏輯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從形式上來講是一首英國十四行詩,而在邏輯結構方面卻沒有遵循英國十四行的結構,而是遵循了彼特拉克的邏輯結構.我們知道彼特拉克十四行是由一個octave 和一個sestet組成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八加六結構,根據傳統的寫作方式,前四句應當投射主題,而后四句發展或深化主題,然后,也是邏輯上最重要的一點——轉折發生在第九句,也就是說后六句承擔著解決或者說釋放主題的任務。而在英國十四行中,前三個小節都是在鋪墊或者說復雜主題,釋放主題的任務都落在了最后一對英雄雙行句上,因此轉折應在第十三句上。在這首詩中我們看到,它有最后的兩個對句,奇特的是轉折點卻發生在第九句上。最后兩句不是獨立的釋放主題而是作為最后六句的意義延伸。
我們為了分析選了這首詩的一個譯本:
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寫在沙灘
但海浪來了,把那個名字沖跑;
我用手再一次把它寫了一遍,
但潮水來了,把我的辛苦有吞掉。
“自負的人啊,”她說,“你這是徒勞,
妄想使世間凡俗的事物不朽;
我本身就會像這樣云散煙消,
我的名字也同樣會化為烏有。”
“不,”我說,“讓低賤的東西去籌謀
死亡之路,但你將靠美名而永活:
我的詩將使你的美德長留,
并把你光輝的名字寫在天國。
死亡可以征服整個的世界,
我們的愛將永存,生命永不滅。”我們可以看到,前八句是在投射主題,提出問題。詩人一次次的努力被海浪化為烏有,詩人想要愛人成為不朽的愿望也遭到了否定。詩中說道:“你這是徒勞,妄想世間凡俗的事物不朽;”這種觀點直到第九句的時候遭到了詩人強烈的反對,“不,”我說,“讓低賤的東西去籌謀/死亡之路,但你將靠美名而永活:/我的詩將使你的美德長留,從這我們可以肯定本詩在邏輯上的轉折點發生在第九句。而最后的對句:“死亡可以征服整個的世界,/我們的愛將永存,生命永不滅” 也是對后一個sestet中的延伸部分。也就是說主題的釋放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并沒有全部放在最后的英雄雙行對句上。
根據Paul Fussell 對十四行的分析,彼特拉克十四行與英國十四行是兩種在邏輯結構上有很大差別的詩歌形式,在表達詩人情感過程方面自然也很不相同,同時他也主張意義與形式的相互適應。這樣看來斯賓塞的這首詩無疑是一次創新。
二、格律分析-音步、格、韻、頓
這首詩引入了對話的形式,讓讀者感到生動親切,它表達了詩歌具有能使愛情,美麗等美好永存的能力,同時也抒發了自己對真摯感情的執著追求。詩歌清新自然,用韻嚴謹(ababbcbccdcdee),其中每行10個音節,除第2、3行外均有5個重音。全詩70個音步中,有67個抑揚格,2個抑抑格:分別在“shed it”和“it with” 之中。1個揚抑格:在第六句的so to 中。
詩歌第一節表達了詩人希望自己的愛在時間的沖刷下能夠不朽的愿望。他在沙灘上一遍一遍書寫愛人的名字,可海水一次一次的把他的字跡抹去,把他的辛苦全部吞掉了。詩人在此詩節中巧妙的運用了抑抑格,在poetic meter and poetic form 一書中,Paul Fussell曾提到過關于抑抑格在詩歌中的作用,他寫道: “The presentation of a sequence of unstressed syllables can convey an illusion of speed or lightness.”“…the reinforcement of illusion s of rapidity, lightness,or by the use of the pyrrhic foot in substitution, or by any unexpected juxtaposition of unstressed syllables.”總之抑抑格產生的作用簡言之就是“快、輕、易”,所以在寫海浪把名字洗掉第2行中,其中的抑抑格音步加快了詩行的節奏,讓人仿佛感覺到了海浪抹去字跡的迅速與突然。第3行寫詩人又一次把名字寫上,也用了一個抑抑格音步,就讓人覺得詩人好象在與海浪賽跑,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真摯、永恒愛情的執著追求。詩人在第6行使用了一個揚抑格“so to”,根據Paul Fussell的研究,揚抑格在詩歌中有突然強調或改變語調和方向的作用。原文中是這樣寫的:“…trochaic substitution in iambic context is the customary metrical technique for producing the third of our general effect—the effect of sudden movement or of a surprising emphasis or of a change in direction or tone…”斯賓塞把重音放在“so”上,以強調愛人對詩人這種追求愛情永恒方式的可笑與荒謬。此外,詩人在詩歌中融入了古英語詩歌的表現手法——頭韻(第2行三次出現[w]音),生動模仿了海水在海灘上反復漲落的聲音,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在整首詩中,共有19個[ei]音反復出現,使整首詩渾然一體,增強了詩歌的連貫程度和音樂感,讀來優美動聽,回味無窮。
這首斯賓塞十四行前12行押abab bcbc cdcd的韻,再加上英國體十四行詩的結尾偶句,便構成了一種新的十四行詩體。在韻律方面與斯賓塞自己發明的九行詩體類似,顯而易見是采用的連環韻,這樣一來,全詩只有五個韻與英國十四行的七個韻相比減少了兩個,這樣會使詩行更加緊湊連貫,同時也增強了詩歌的音樂性。同時相鄰兩個詩節被相同的韻腳粘和在一起,組成了兩個內部英雄雙行:
But came the tyde and made my paynes his pray. b
“Vayne man” sayd she, “that doest in vaine assay, b
And eek my name bee wiped out likewise.” c
“not so,” quod I “let baser things devise, c
在形式上前12行渾然一體,有給人一張一弛、在循環往復中前進的感覺。沃爾多?麥克尼爾的評價恰到好處:斯賓塞的十四行詩既不像意大利十四行詩那樣在八行詩節和六行詩節中對稱地升降,也不像英國十四行詩那樣循序漸進在結尾偶句中達到高潮,而是在連續不斷的流動中形成內在的邏輯。
頓的使用是這首詩的另一個特點,其中第四、五、九、十和十四句都使用了頓。根據Paul Fussell對于頓的理解,頓的使用有兩種主要的作用,其一,這是強調詩歌表達正式性的一個手段,也就是說為了堅持詩歌語言和口語表達方式不同的一種方法。其二,這是為了向嚴格的、正式的詩歌形式中引入不太正式詩歌元素的一種方法,比如語言中不可預料的暫停或是躊躇。在這首詩中用頓的詩句如下:
4 But came the tyde,and made my paynes his pray.
5 “Vayne man” sayd she, “that doest in vaine assay,
9 “not so,” quod I “let baser things devise,
10 To dy in dust, but you shall live by fame:
14 Our love shall live, and later life renew.”
其中第五句和第九句中的頓是為了引入“vayne man”和“not so”兩個對話式的語言形式。簡短的語言加上有力的頓顯得詩句節奏明快、意義鮮明。而第四、十和十四句中的中頓則詩化了詩歌的語言,讓讀者感到詩歌語言與口語的差距。
三、詩歌中的時代精神
從思想內容上來看,這首詩體現了文藝復興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學思想:文學可以使世間凡俗事物不朽,包括人間一切美好的事物,如真摯愛情,美麗的愛人,迷人的自然界等。詩人們相信只要把這些美的東西用詩人的詩句記錄下來,它們就得到永生了,永遠保持美麗。在《愛情小唱》的第75首中,詩人在一開始就講述有一天他把愛人的名字寫在沙灘上,但海浪卻沖跑了字跡,當他再次寫下時,辛苦又被潮水變成了徒勞,他的愛人說使世間的事物不朽這是徒勞,而詩人卻認為他的詩句可以征服時空,使他的愛人不朽,使愛永存。他寫道:……
“不,”我說,“讓低賤的東西去籌謀
死亡之路,但你將靠美名而永活:
我的詩將使你的美德長留,
并把你光輝的名字寫在天國。
死亡可以征服整個的世界,
我們的愛將永存,生命永不滅。”
這一信念在文藝復興時期很被認同,例如偉大的莎士比亞也曾寫過類似的十四行詩,sonnet 18中就有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的詩句,詩人把自己仰慕的人比成了永恒的夏日,并永遠美麗在他的詩行里。另外,這首詩屬于Amoretti里的一首,譯成英文的意思是Little love poems, 表達了對愛情的向往,對愛人的贊美。這無疑又是人文主義的表現,詩人不但追求愛情、追求自我的幸福感受,而且追求美好事物的永恒。
結語:本文對《愛情小唱》中第75首十四行詩從格律和思想內容兩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從格律方面來說,斯賓塞對十四行詩在緊緊追隨前人留下的傳統基礎上進行了很多創新。在思想內容方面很好的體現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
[1]Paul Fussell, Poetic Meter and Poetic Form, McGraw Hill, 1979.
[2]韓小衛,郭娜. 斯賓塞的十四行詩與“斯賓塞詩體”淺論.《時代文學》. 2008年第四期.
[3]李賦寧.《英國文學論述文集》.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
[4]王佐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