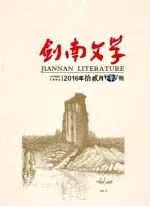淺談中國畫的筆墨
蔡永平 河南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 河南新鄉 453007
淺談中國畫的筆墨
蔡永平 河南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 河南新鄉 453007
新世紀水墨畫壇將出現一個更加開放的前景,為當代藝壇創造一個全新的景觀。不管油畫、水墨及其他,要談的問題是藝術--當代藝術,所有的材料問題與技術問題都在其背后。因此,我們的藝術表達可以不擇手段。關于中國畫前途命運的焦點,目前集中在“筆墨”問題上。但無論是“筆墨等于零”論,還是“筆墨是中國畫的底線”論,都各有其偏執的地方。而對于現代中國畫來說,“筆墨”的地位和價值,主要是其形式意義。通過對“筆墨”的工具屬性、技法屬性、形式屬性的逐層分析,給中國畫“筆墨”的本質屬性以明確的定位。認清“筆墨”屬性,是我們如何對待“筆墨”,并進而思考中國畫“出路”的一個重要前提。筆是中國畫的筋骨,墨是中國畫的血肉,論氣韻先看筆墨,舍筆墨無以談氣韻。
筆墨; 氣韻; 神韻; 意趣
筆墨是中國畫的安身立命之本,筆墨不僅是視覺形式和技術規范,筆墨還是中國畫的精神內容。
筆墨二字,筆在先,用筆是關鍵。黃賓虹以畢生實踐研究傳統筆法,認為“用筆之法,從書法而來”,又說“自畫法失傳,古人用筆,存于篆隸”,故“作畫全在用筆上下功夫”,他還指出,“作畫不求用筆,止謀局部烘染,終不成家”。 以筆入畫,求筆法,見筆趣,有書寫意趣者,當今已找不出多少人。在一個重形式的時代,我們離“筆”越來越遠,這就是今人低于古人之處。筆講力度,后人稱元代王蒙“叔明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又稱扛鼎之筆為“金剛杵”。“金剛杵”三字形象而深刻——刀傷人,取其鋒利;槍傷人,取其尖銳;而金鋼杵致人死地不見創口,五內俱碎,以此喻筆,必力透紙背無疑。清代鄭績在《夢幻居畫學簡明?論筆》中說:“用筆以中鋒沉著為貴,中鋒取其圓也,沉著取其定也。定則不輕浮,圓則無圭角。生怕澀,熟怕局;慢防滯,急防脫;細忌稚弱,粗忌鄙俗;軟避奄奄,勁避惡惡;此用筆之鬼關也,臨池不可不醒。”唐代陸希聲所論的“ 、壓、鉤、格、抵”五字執筆法,使五指自然地發揮各自的作用,分工而又合作,做到“五指齊力”、“指實掌虛”,筆在手中也就操作靈活、進退裕如了。古來大家十分講究用筆,且追求沉厚老辣的境界,對于一般畫家,且不要說達到,能有所領悟也是很難的事情。
南齊謝赫首提“骨法用筆”(《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解釋為“生死剛正謂之骨”。骨是寫的力度體現。在歷代的畫論中,偏于“寫”的拙辣,無疑要高于偏于“工”的巧致,前者重于神韻的發抒和筆墨本身的審美,后者關注外形的效果和視覺的完整。前者為藝而重道,后者為質而重法。黃賓虹用筆“粗頭亂服”乃是至高的“內美”境界,常人是無法領略的。
在筆墨技術上,前人的論述則更多,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筆盡筆法、墨求墨氣”,“筆墨太簡,則失之闊略”,“古人位置緊而筆墨拙,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單然,不貴五彩”。北宋韓拙在《山水純全集》里說:“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這句話被千年以來的實踐所證明。筆是中國畫的筋骨,墨是中國畫的血肉,論氣韻先看筆墨,舍筆墨無以談氣韻。
自古以來,中國先哲們、畫家們十分講究“浩然之氣”。“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藝術表現,“氣韻生動”作為藝術的首要表現,該標準千百年來能夠在中國畫形式語言的運用中流傳不衰,成為共識,其原因很簡單,它與人的現實精神息息相關,從而使這一規律提升到文化精神性的高度,成為形式語言的內在文化標準。“氣韻生動”地把握神韻之境,代表了人的生命勃勃而有生機的發展之前景,主動地把握住這一點,在任何外來的倒行逆施和牽掣面前,人的心神都會舒暢坦然,志向永遠與生命精神的高遠聯系在一起。
古人都知“筆墨當隨時代”,當代人豈能被傳統拴住手腳?時代變了,筆墨也在變。現代科技,日新月異,現代生活,多姿多彩,現代水墨,自然要適應中國畫的經典,歷來講究傳統;中國畫的創新,則強調繼承傳統。那么,中國畫的現代水墨畫應如何創新,我認為即要遠離傳統,又不能夠脫離傳統。傳統是古人智慧和實踐的結晶,今天的創新就是明天的經典。沒有傳統,就沒有中國特色(民族特色);繼承傳統,并非固步自封;而遠離傳統,更不是拋棄傳統,而是要與傳統不即不離,在實踐中創新。即筆墨當隨時代。
為了進一步達到人的心情與自然的脈搏共振,中國畫家筆下的形態是以自己的內在體驗,從時光的流逝、生命的節奏中形成對自然界的深層看法——形成藝術的世界觀,即山山水水應當在畫家的筆下,“春融恰,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秋山明凈而如妝,冬山慘淡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跡,則煙嵐之景象正矣。”(引自《歷代論畫名著匯編?林泉高致》),良好的文化心態,永遠是走向中國畫形式語言掌握的基礎,具有切實把握中國畫精髓的心靈世界,就能獨步于筆墨佳境,自由蕩漾于中國畫精神的高妙之境。中國畫筆墨語言能夠穿過千百年的歷史煙霧走向現代,立身于民族藝術之林的根本,就在于掌握和控制這一形式語言者心靈的偉大。他們以自己超然的人格塑就了永恒的筆墨語言,從而在歷史文化的洪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看到筆墨語言本身的視覺狀態時,人們透過種種筆墨行為看到的是其背后的經典意義。
黃賓虹留下的大量論畫經驗無疑開啟并端正了后人的學畫之路,若說中國畫教育,黃賓虹則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中國畫教育家。由于對傳統各家的深入研究,殊有心得。他又是一位傳統筆墨的集大成者。他的用筆,不但筆筆入紙,而且留得住,提得起,勁健圓渾、力透紙背,是篆籀筆法所形成的金剛杵的感覺。尤其臨終前幾年的用筆,禿筆篆籀,筆筆分明。這種感覺是幾十年錘煉加之對中國傳統畫論的深入領悟形成的,20世紀沒有第二人達到。
中國古典哲學認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循環往復,人體內也是真氣流轉,沒有間歇。觀照筆法,也應是元氣充沛。當外部的環境影響到人的心理和生理時,元氣會產生不穩定的變化,如氣虛、煩躁等等,反映在筆墨上便出現“浮氣”、“躁氣”,也有性格和修養的關系,沉不下心來,當然現出“浮氣”,而一味討好社會,急于求得別人贊揚,常現出“匠氣”。所以,養氣是中國文人畫家的功課,能做到氣脈不斷,筆不困,墨不澀,元氣安穩,神閑意定。“勿促迫、勿怠緩、勿陡削、勿散神、勿太舒,務先精思天蒙,山川步伍,林木位置……以我襟含氣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內,其精神駕馭于山川林木之外。”在這里指出氣韻妙決——心神高遠則筆墨自能深厚,心境曠達則畫境自然高邁,筆墨已不僅是技巧,是心胸、秉賦、氣度、積累的反映,是才情和知識的記錄,更是人格的標志。
中國畫之路,漫長而修遠。“通會之際,人成藝成。”這是中國古代畫論的結論,而通會是非窮畢生精神不能實現的目標。所以,中國畫是生命過程的藝術,它的最大的意義是與人的生命緊緊相連,從而使生命變得更有意義。
[1]王伯敏,錢學文. 黃賓虹畫語錄[M]西冷印社出版社,2009.
[2]中國美術史. 中央美術學院編,2004,4.
[3]美術觀察,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
[4]王伯敏.中國美術通史[M].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5]薄松年,中國美術史教程[M]陜西美術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