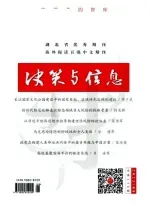關注中國發展道路上的重大理論問題
文/汪仲啟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法治國家建設研討會”日前在古都西安召開。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等130余人出席會議。會議集中就人大制度與民主法治建設、黨的領導與法治國家建設、百年憲政、公民社會與中國發展道路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黨的領導必須通過黨的執政來實現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來,歷經磨難,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任務。1949年成為執政黨后,也走過一些彎路,但黨始終能適時調整自己的領導策略。而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如何發揮領導作用,如何實現長期執政,是迄今尚未完全解決的重大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法學家郭道暉教授說,“馬上治天下,還是法治天下?是以黨治國,還是依法治國?至今有些黨政干部不能說已完全搞清楚”。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應該從依法治國、依法治黨開始。黨章、“黨法”不能與國法有抵觸的地方,“法治建設發展到今天,執政黨要依憲執政,全體黨員,特別是某些黨的官員要成為實施憲法和法律的工具,而不是把憲法和法律當成實現自己政策主張的工具。”
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表示,在我國現行體制下,離開了執政黨的推動,加強憲法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會是一句空話,因此“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從憲法開始,而是否可以考慮從黨章開始”。武漢大學政治文明中心主任虞崇勝教授同樣認為,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執政黨的執政方式是制約該國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問題,只有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執政方式才是值得肯定的。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場景中,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充當了既是領導黨又是執政黨的雙重角色。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在法治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角色錯位,將導致政治體制和政治運作的混亂,因此,“黨的領導必須通過黨的執政來實現”。領導權是政治權威,主要靠政策指導與號召,執政權是國家權力,有國家強制力做后盾;領導權對黨負責,而執政權對人民負責。因此,法律,也就是人民的意志,應該比黨規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和約束力,執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
胡錦濤同志曾指出,“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郭為桂教授認為,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的國家構建逐步恢復到常規的理性化道路上來,群眾路線總體上演化為惠民親民的政策主張,“但為什么中國社會仍然問題不斷,黨群關系依然緊張,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這是因為“群眾路線”本身存在著內在缺陷,當代群眾概念更多地繼承了傳統語境下“民”的概念的消極、被動、受治者的含義,在權力結構中處于下者地位,是被領導、被保護、被關愛、被服務、被尊重的。“作為一項根本的政治路線,缺乏基本的制度依托和機制保障,其運作有很強的隨意性和偶然性,需要上層不斷地警示以求得中下層領導干部的重視和遵行。”中央編譯局朱昔群研究員說,有人認為當前我黨面臨執政能力危機和合法性危機兩大挑戰,黨在化解執政能力危機的時候采取了許多有成效的舉措,但執政黨執政中的合法性危機,如群眾對政府、官員不信任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維持良好的黨群關系,我們不能再靠運動,要靠制度化保持優勢,要實現黨群關系的制度化。
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
陜西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桂維民認為,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而我國憲法實施工作目前存在不少問題,比如許多公民,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的憲法意識還不強,人治習慣根深蒂固,對憲法賦予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保障還不力,強行拆遷、濫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憲法實施的緊迫任務,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憲法實施的關鍵環節。
《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教授表示,當前基層政府一些官員濫用公權力,屢屢侵犯老百姓的人權、生命權、財產權等基本權益,“跨省追捕”,“被神經病”、“暴力拆遷”等蠻橫不講理的做法,擊穿了為政者的倫理底線,嚴重背離了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宗旨。在當前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擺正自己和人民的關系,擺正公權力和輿論監督關系,真正做到胡錦濤同志所說的“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真正做到習近平同志說的“權為民所賦”,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憲政社會主義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在陜西省價值哲學學會會長、西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周樹志教授看來,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經濟極端落后的封建專制主義尚未完全鏟除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因此,即使制定了憲法,真正實現憲政并不容易,中國應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憲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著名憲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許崇德先生認為,憲政即民主政治。危害我國憲法尊嚴及其實施的思潮來自兩個方面:自由化思潮和打著反“西化”旗幟的極“左”思潮,“把‘憲政’片面地定義為資本主義專利,無視我國社會主義憲法,認為實行‘憲政’就會招致西化的觀點,極為荒謬”。憲政是法治國家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一定要明白:“我們的憲政是社會主義憲政,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憲政社會主義”。西北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華炳嘯認為,憲政是共產黨執政興國的合法性基礎,脫離憲政,黨的事業就有脫軌的危險,要實現長治久安,只能走憲政民主與共同富裕之路,也即走憲政社會主義改革新路。如果不能找到解決威權壟斷與貧富懸殊問題的根本對策,高成本維穩只能把一時一地的怨氣轉移和蓄積到更脆弱的時空點上,社會動蕩難以避免。而要避免社會動蕩,就只能走科學發展與全面改革之路,即憲政社會主義改革新路。
人大不應成為政府干部的“養老院”
根據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然而,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如何處理與黨的領導的關系,在操作機制上并不明確,人大自身也面臨著工作機制的不完善問題。中國世界學會副會長、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常士門言表示,人大和黨的關系中存在張力,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或政治建設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反映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存在著雙頭領導且一定程度上的矛盾狀況,“這導致我國政治生活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著有權威而缺少規則,有監督又監督不力的尷尬局面”。
黨和人大到底是何關系,“領導”和“作主”如何能統一?復旦大學浦興祖教授認為,黨的主張對于人大或其常委會而言,只是一種建議而非命令。黨的主張經常能被人大轉變為國家意志,就體現了黨對人大乃至對整個國家的領導(帶領與引導),如果黨的主張不能經常轉變為國家意志,則黨對人大和國家的領導就難以保證。“從理論上講,人大或其常委會可以轉變,也可以不轉變,人大或其常委會是否將黨的某項主張轉變成國家意志,是憲法所賦予的權力。”
四川大學人權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周偉教授則認為,全國人大代表超過3000人,人數過多不便于討論和決定問題;而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169人(第十屆以前150人),人數過少,雖便于討論和解決問題,但又缺乏代表性。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會期較短,議程較多,使代表們的利益表達受到時間限制,難以保障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充分表達意見。周偉建議,將代表人數由3000人左右減少到1200人左右(1954年第一屆人大代表的人數)。除保留各民族、臺灣地區、特別行政區的代表配額外,均按照人口比例產生,約100萬人產生一名代表。增加常委會人員職數,恢復到1949年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人數的600人左右為宜,還可增設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全部擔任常委會成員。
對于專門委員會,廣西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副教授廖原指出,由于工作機制不順,缺乏明確的議事規則,各專門委員會之間工作量差別極大,工作范圍和職責劃分不清晰,人員年齡整體偏大。“以九屆人大專門委員會為例,60歲以上的占73%以上,而50歲以下的則不到7%。在某種意義上,專門委員會起到了安排退休領導干部的作用”。廖原建議,把人大專門委員會建設作為完善人大制度的突破口,除制定專門的議事規則,明確工作職責之外,應重點調整專門委員會的人員結構,“人大工作機關不應成為政府干部的‘養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