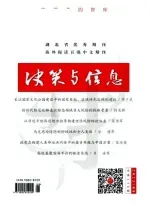明首輔張居正的榮與辱
文/向 飛

在明朝,按法律規定,抄家的罪狀有三條,“一謀反,二叛逆,三奸黨”。張居正生前身居首輔,位極人臣,政令通達,功勛卓著,死時謚“文忠”,極盡哀榮。然而死后不到一年,卻遭到了“抄家”的慘禍,長子自縊,家人被發配戍邊。
他有謀反、叛逆、奸黨的嫌疑嗎?沒有。那么,他的家庭為什么要在他死之后遭此災難呢?對此,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首輔之路
張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今荊州),字叔大,號太岳。相傳他出生時,其曾祖父夢到月亮落在水甕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龜從水中悠悠地浮起。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便順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張居正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他五歲入學,十歲通六經,十二歲中秀才,十三歲時參加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煉幾年,才未中舉。三年后,才高氣傲的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了一名少年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是朝廷的智囊團,人才儲備庫。進入了翰林院,標志著張居正將有一個坦蕩的仕途。他被安排到裕王府,為嘉靖皇帝的第二個兒子朱載講課。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朱載繼承了皇位,是為隆慶皇帝。登基不久,他就將張居正拔擢為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務。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這年,張居正四十三歲。
隆慶六年(1572)五月,意外的機遇降臨了:皇帝病故,遺詔任命高拱、張居正、高儀三名內閣輔臣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同為顧命大臣,輔佐不到十歲的小皇帝萬歷登基。
高拱一向以精明強干自詡,傲視同僚,對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弄權于宮闈極為不滿。他起草了一份旨在削奪馮保權力的《陳五事疏》,以閣臣聯名的方式提交皇帝。在征求張居正的意見時,張居正假意答應了他,暗地里卻把消息傳遞給了馮保。
按照高拱的部署,他的門生故吏一起向馮保發難:什么“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駭人聽聞,措辭毫不掩飾,必欲置馮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條,就是指責馮保雖然是個太監,卻精通房中術,給先帝“誨淫之器”、“邪燥之藥”,導致先帝早崩。僅此一條,就足以要了馮保的命。
當然,馮保也不是等閑之輩,他派親信向張居正討教,張居正告訴他:“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為之。”
原來,穆宗死時,高拱在內閣慟哭時,曾說過“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之類的話。馮保根據張居正提供的線索,改變成一句“十歲孩子如何做人主”,向皇太后、皇上告密。皇太后聽了,非常震驚;小皇帝聽了,也馬上變了臉色。
高拱敗局已定,不過他自己還被蒙在鼓里。
隆慶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宮中傳出話來:“有旨,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高拱滿以為是小皇帝要下旨處分馮保,頗為興高采烈。
當高拱、張居正及文武百官到會極門跪接圣旨時,太監王蓁捧著圣旨高聲念道:“皇太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圣旨:……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
據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描述,當時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張居正“掖之起”,“使兩吏扶攜出”。
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狽。文秉《定陵注略》用這樣的措辭來描繪:“緹騎兵番,踉蹌逼逐”;“囊筐攘奪無遺”;“仆婢多逃,資斧盡喪”;“出都門二十余里,餒甚,止野店為食”。
臥病在家的另一顧命大臣高儀,聽到高拱“回籍閑住”的圣旨,大驚失色,擔心牽連自己,憂心忡忡,病情加劇,嘔血三日而死。
三位顧命大臣,一個斥逐,一個病死,剩下張居正一人,理所當然地成為內閣首輔,擔當起了輔佐小皇帝的重責,同時也開啟了他十年輝煌的政治生涯。
一個成功的改革家
就其業績而言,張居正不只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而且是漢朝以來最成功的改革家。現代學者黎東方先生說,能同張居正勉強相比的只有諸葛亮和王安石。不過,諸葛亮處境艱難,未能施展其經綸于全國;王安石則富于理想,卻拙于實行。
張居正則不然。上有皇太后、皇帝的支持,內有太監總管馮保的呼應,張居正的改革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因而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內政上,他大力整頓吏治,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目標,淘汰了一批冗官,厘清了六部及有關單位的職責,使政令暢通,秩序井然。
在經濟上,他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查出漏稅土地達三百萬頃,使朝廷的稅收成倍增加。在這個基礎上,他又雷厲風行地推行“一條鞭法”,即把田賦、徭役和雜稅等集中起來,折合成銀兩,分攤到田畝上,田多者多出。這不只抑制了強豪兼并,而且切實地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
在軍事上,他任用李成梁、戚繼光等名將整飭武備,邊境晏然。不只東南沿海一帶的倭寇幾近絕跡,連西北一帶的邊患也不再發生。
史家一致認為,萬歷初年,是明朝中葉以來形勢最好的一段時期。張居正運籌帷幄,勤勤懇懇,取得了“海內肅清,四夷營服,太倉粟可支十年,庫寺積金四百余萬”的輝煌業績。
黎東方先生說:“明朝自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張居正能以超人的鐵腕,把政風士習扭轉,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邊境相當太平,國內家給戶足,轉貧為富,化弱為強,真令人心向往之。”
但是,張居正的為人卻有一些致命的弱點。
首先,由于他過于負責和專斷,未免得罪了一些僚屬;而清丈田畝、改革賦稅,又觸動了一些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他辦事雷厲風行,鋒芒畢露,因而也樹敵過多。
其次,張居正善于玩弄權術,縱橫捭闔于宮闈與朝臣之間,他與太監馮保互為表里,建立起來的政治聯盟有效地壟斷了朝廷,不論其用心如何,都為正統的士大夫所不齒。
第三,他生活張揚、豪奢,律己未必甚嚴,在有些人看來,他有貪污、受賄的嫌疑。
當他有權有勢的時候,確乎能形成一派政通人和的假象,而一有風吹草動,他就容易受到無情的攻擊。
“奪情”是他死后災難的一次預演,可惜的是,張居正工于謀事,拙于自保,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
“奪情”風波
萬歷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張居正父親病逝。按明代禮制,內外官吏人等都有“丁憂”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須辭官守孝二十七個月,不計閏月,期滿起復。
但是,如果國事需要,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辭職守孝,繼續留任,則稱之為“奪情”。不過,明朝立國以來,除了直接帶兵打仗的官員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奪情”的。
開始,萬歷小皇帝朱翊鈞給張居正寫了一道諭旨,安慰老師,但是并沒有刻意挽留。
此時的張居正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皇帝年幼,他們母子都離不開他這個老謀深算的顧命大臣;另一方面,他自己推行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一旦離任,后繼非人,后果不堪設想。但如果他戀棧不退,則容易在道德上遭人非難。
正在他進退兩難之際,小皇帝果然下了一道“奪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里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盡管張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卻堅持“奪情”。張居正畢竟是玩弄權術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奪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間,照常給皇帝辦事,不拿薪水。這下子小皇帝同意了。
但是,朝廷也不能讓張先生白干呀!于是,小皇帝命令,光祿寺每日給張先生家送酒飯兩桌,有關衙門每月給張先生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三百支,柴薪二十杠,炭火三十包,到服滿為止。
朝廷對張先生的恩寵,可以說是到了極致。
但是,在以宗法、禮教立國的明朝,父死不守孝是有關天理、人倫的大事。適逢十月初五,天上出現彗星,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詔求言,于是有人把這件事同“奪情”之舉聯系起來。
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這位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卻上了一道《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以為“奪情”既不近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名上疏,奏請令張居正回籍守耕。小皇帝朱翊鈞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四人的矛頭不只是對著張先生的“奪情”,也是對自己權威的藐視。他決定效法列祖列宗,對直言犯諫的大臣施行慣用手法——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各六十棍,被打得死去活來;艾穆、沈思孝各八十棍,刑后收監充軍。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這場淫威所嚇倒的,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他對張居正素無好感,就在四人廷杖的當天,他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結果,鄒元標也被廷杖,遣戍都勻衛。同時遭廷杖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韓,他也上了一道萬言疏指責張居正,被打后發送原籍。
反對張居正“奪情”的斗爭終于被鎮壓下去了,但張居正在士林中的聲望卻從此一落千丈!
身后榮辱萬萬千
萬歷十年(1582)春,張居正病重,久治不愈,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各部刀筆吏,無不設道場為其祈福。有些朝廷命官棄本職工作不顧,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場,甚至在官署中也擺上了香火繚繞的神壇。京官們如此,各地封疆大吏也起而效尤。一時間,僧道云集,烏煙瘴氣,朝野一片混亂。
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五十八歲的張居正病逝。
張居正死后,神宗“愴悼輟朝”,特許京城設祭壇九座,供官、民吊唁,后因赴吊的人太多,又增設七座。追封張居正為上柱國、謚文忠,特派司禮監太監陳政為總管事,由在京的四品堂官、錦衣衛等組成護喪隊伍,護送其靈柩歸返故鄉荊州。夏日炎炎,張居正的靈車及輜重車七百余輛,在三千名軍卒夫役的推擁下,浩浩蕩蕩地沿官道向湖廣方向緩緩行進;這支隊伍前后十余里延綿不絕,沿途路祭的各地百姓更是看不到頭。
同年十二月,朝政格局卻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重大傾斜——神宗瞅準宮內太監總管馮保失去了內閣支持的時機,成功地翦除了這個自幼即掖抱陪伴他的“大伴”。事后,他還故作寬大地假惺惺說道:“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勞日久,故從寬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總算是寬大處理,只查抄了家產,并未為難他本人。
馮保倒臺了,這不啻是個政治信號。反對派們活躍起來了。
率先彈劾張居正的是陜西道御史楊四知,他上疏開列了張居正的十四條罪狀。神宗對此疏的批注含糊不清,模棱兩可。敏感的朝臣們心領神會,于是彈劾的奏章雪片似地飛來。
萬歷十二年(1584)正月,洪競上疏為父申冤,向萬歷皇帝哭訴了張居正指使勞堪害死其父的經過。
前任首輔高拱也送來了《病榻遺言》,揭露了張居正與馮保聯手,把自己趕下首輔之位,并欲置之于死地的過程。
一時間,朝野呼應,上下其手,鬧得群情洶洶,最終導致神宗決定對尸骨未寒的張居正痛下殺手!
萬歷十二年四月,神宗頒發了查抄荊州張家的詔書,由司禮監太監張誠和刑部右侍郎丘舜等人所主持的抄家之舉,把皇帝翻臉不認人的冷酷面目實施到了極致:他們還沒有趕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錄張府人口,封閉府門,一些老弱婦孺來不及退出,門已封閉,餓死十余人,相傳死者“皆為犬所殘食而盡”。
在查抄家產中,張、丘二人更是錙銖必究,大加拷問,窮迫硬索,揚言張家藏有兩百萬兩銀子。其長子張敬修經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指認有三十萬兩銀子藏匿于張居正的親信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里。于是,錦衣衛分頭趕往上述三家,可抄查出的銀子卻一共未足十萬兩。三子懋修實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殺未遂;敬修羞憤交加,自縊身亡。
此番抄查張家所獲,據刑部當時列的清單,計為:黃金兩千四百余兩,白銀十萬七千七百余兩,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兩,金首飾九百余兩,銀器五千二百余兩,銀首飾一萬余兩,另有玉帶十六條等等。這與神宗原先的估計相去甚遠。
張家的財產,后來被運到了北京,共一百一十抬,并沒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有專家估算,若是把他家的總資產折合成白銀,大約只是嚴嵩的十分之一二;而與馮保相比,還不到其十分之一。不知萬歷帝過目之后有何感想,應該多少有點失望吧!
死后清算之謎
張居正是明朝最有權力、最具影響的內閣首輔。他協助十歲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敗、混亂的明王朝治理得國富民安,他是小皇帝不可一日或缺的靠山,是“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他的赫赫功績,堪與商鞅、王安石并立,而被稱為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中期與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神宗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對死去不久的張居正下如此毒手呢?
歷史學家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這是君臣之間十年積怨的總清算。
在封建王朝里,君權和相權是一對相依相克的矛盾。君權過于弱小時,需要強大的相權來支撐;而過于強大的相權,則會矮化皇室,遭到帝王的忌恨。
張居正開始輔佐神宗時,小皇帝年僅十歲,為了穩定政權,神宗母子都對張居正有所倚賴,尊重備至,言聽計從。但是,這位元輔對小皇帝管束過嚴,干涉過多,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已經開始了由親近、尊重向著畏懼、厭惡的方向轉變。這一點,過于自信的張先生并沒有察覺。
張居正以嚴師對待學生的態度對待小皇帝,每天布置功課,如果小皇帝沒有認真背誦或領會,就會遭到嚴厲的斥責。有一次,小萬歷讀《論語·鄉黨》時,把“色勃如也”讀成了“色背如也”。張居正當著眾大臣的面,厲聲吆喝,嚇得小皇帝連忙低頭糾正。平時,如果小皇帝背著張居正做了越制出軌的事,馮保就會嚇唬他:“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辦?”小皇帝聽了,很快就會收斂自己。
但是,小皇帝逐漸長大了,成人了,開始懂得了皇上的權威和分量了。而張居正仍然把持朝政,作威作福,甚至對他的宮闈生活也說三道四,這使得神宗對張居正的態度向著仇恨方向迅速逆轉。
權高震主,是為臣之大忌;張先生卻是自鳴自得,渾然不覺。豈知,他所攬之權,就是神宗之皇權;張居正的高大顯赫,就反襯出神宗的卑微猥瑣;群臣對張居正的恭維,就是對皇上的蔑視。是可忍,孰不可忍?成長起來的神宗必然要扳倒張居正,奪回皇權,一消這十年的積憤。即使張居正不死,這場君權和相權的斗爭也將在短期爆發。
而在封建社會里,權力的天平總是向著君權傾斜,因此,張居正的覆滅和被清算是必然的。
其二,這是走出張居正陰影,一展帝王雄威的大決策。
張居正死了,走了,埋了;神宗皇帝就可以乾坤獨斷,一展帝王雄威了。這就是神宗皇帝充分展示他的大度,極盡哀榮地禮送張居正歸山的根本原因。
但是神宗皇帝沒有料到,張居正雖然走了,卻是陰魂不散,自己仍然生活在他的陰影之中。每有詔令,群臣就會觀望、比較,假如張先生在,將會怎樣決策;每有行事,神宗皇帝也會自我掂量,假如張先生在,將會怎樣評判。張先生的陰影仍然高高地懸立在朝堂之上,俯視著神宗,使他自卑、自疑、猥瑣、狼狽不堪。他的自尊心、虛榮心受到極大的創傷,與此同時,他的逆反心理、仇恨心理也開始極度膨脹。他憤慨、激昂、烈火中燒,不能自已,就像咆哮在火山之下的巖漿,必欲沖破壓頂的山石,一吐胸中之塊壘而后快。
最初,他用溫和的手段割舍他的“大伴”,他感受到了一種無羈無絆的輕松,獨來獨往的愉悅,以及隱秘于心靈深處的邪惡的復仇的快感。這使他驚奇,震動,也受到啟發和誘惑。于是,他決心粉碎這座高立于廟堂之上的偶像,搬掉壓抑在他心靈之中的、掃蕩籠罩在他頭頂之上的陰影。這是一個大決策,大決戰!戰斗必然成功,唯如此他才可以真正成為屹立于萬民之上、天馬行空、受到萬民仰望的皇帝了!
有了這樣的思維,張先生的形象能不被撕裂、不被踐踏嗎?
其三,神宗的貪財好利,也推動了清算的進程。
《明史紀事本末》中記敘了明神宗查抄張居正荊州老宅之前與皇太后的一段對話。
這一年,神宗的同母弟潞王已年滿十六歲,該議婚了,可操辦婚禮的銀子還有一多半沒有著落,慈圣皇太后一想到此事,就感到煩心。神宗聽了,滿不在乎地說:“這事您別著急,我有辦法!現在朝中的這些官兒們都無恥極了,他們一定是看馮公公、張太師權大,把好多錢財珠寶都作為禮物存放在這兩家了。”
太后聽了,心里有了些把握,躍躍欲試地說:“假使查抄他們的家,這些錢財就都到手了嗎?”
“這個馮保詭計多端,那些錢財恐怕都悄悄地轉移了。”
正好這時候,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了一道“已故大學士張居正隱占廢遼府第田,乞嚴行查勘”的疏奏,已廢遼王次妃王氏也奏稱遼王府“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都說得有根有據。再加上馮保抄家,所得巨萬,這位貪財好利的皇帝能不動心嗎?至此,張居正家厄運難逃。
此外,張居正一人獨大,后繼無人,也是他敗亡得那樣迅速、那樣徹底的一個原因。他剛愎自用,偏信偏聽,喜歡阿諛奉承之徒,打擊直言敢諫之士。到萬歷皇帝決心向他清算的時候,大家一呼百諾,奮勇爭先。沒有人敢替他說話,替他伸冤。相反,那些受他提拔、被他重用的新政人物,反倒成了反張居正的急先鋒。張居正厲行的改革,也就因此而壽終正寢了。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初大罵張居正是禽獸,被廷杖致殘的鄒元標,竟然拖著一條瘸腿,為張居正的昭雪奔走呼號,試圖召回失去的新政。
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這座經歷了兩百年風雨的古老的帝國大廈,終于在六十年后,被歷史的巨浪沖擊得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