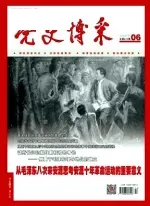“賀龍式”工農武裝割據探析
李孫強
(滁州市委黨校 安徽滁州 239000)
“賀龍式”工農武裝割據探析
李孫強
(滁州市委黨校 安徽滁州 239000)
本文闡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賀龍在湘鄂邊發展人民武裝力量,開辟革命根據地的過程,并分析了“賀龍式”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
賀龍;工農武裝割據;經驗
湘西張家界是世界自然遺產公園。公園里的賀龍園矗立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賀龍的大型銅像。這里是賀龍的家鄉,是大革命失敗后,賀龍向中央提出回家鄉開辟革命根據地的地方。
1927年上半年,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的叛變和陳獨秀右傾錯誤,導致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失敗。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懂得了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極端重要性。于是,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八七”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繼續進行戰斗,并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因此,繼八一南昌起義以后,9月起,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各地又打起紅旗,掀起了暴動。當時真是群雄四起,八方暴動,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強大的反動勢力面前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無數次攻打城市暴動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沉痛的教訓迫使中國共產黨人熱切希望能找出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符合中國革命規律的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曲折的革命實踐中探索前進。
一、賀龍回家鄉湘西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的過程
賀龍參加并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勝利后,部隊南下在潮汕失敗。為了保存革命骨干,中央調賀龍回上海。黨中央原打算派賀龍去蘇聯學習,但賀龍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深感槍桿子的重要,他再三向中央請求,“黨相信我,還是派我回湘鄂西去拉隊伍,或許能搞出一點名堂來”。黨中央同意了賀龍的請求。周恩來找他和周逸群談話,命他們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前往湘西北發動群眾,建立中國工農革命軍,開展武裝斗爭。
1928年初,賀龍、周逸群、盧冬生等同志前往湘鄂邊開辟革命根據地。賀龍等沿江西上,經武漢,于1928年1月中下旬到達湘鄂邊的監利縣境。當時只有“駁殼三支,手槍兩支”。在觀音洲繳了團防(即地主武裝)八支槍,然后會合了“八一”起義后來洪湖地區活動的賀錦齋一支部隊,接著又與石首中心縣委取上聯系,并通過他們集合起兩支農民武裝。其中一支是大革命失敗后保留下來的,在石首、華容一帶活動的吳仙洲部;另一支是湖北省委在秋收起義后組織的,活動于洪湖附近的鄧赤中、彭國才部。前后會合的三支隊伍共有三百多支槍,官兵300余人,組成中國共產黨湖北沔陽工農革命軍第五軍,以賀錦齋為軍長。由賀龍和周逸群直接掌握。這是湘鄂邊前委領導下的最初的武裝力量。
由于大革命失敗,這一帶地主武裝和帶政治性的土匪十分囂張,他們對革命人民和革命組織進行瘋狂地屠殺。為領導群眾反擊反革命的猖狂進攻,工農革命軍參加了地方黨發動的監利、石首、華容、南縣等地的年關暴動,打土豪,鏟除貪官污吏,消滅了荊江兩岸許多團防和土匪,繳獲了一些武器,鼓舞了群眾斗爭情緒,部隊擴展到一千多人。荊江兩岸局面初步打開。賀龍等同志原準備消滅駐監利城內團防,然后根據中央原來意圖前往湘鄂邊創造新的根據地。沒料到,城內突然增加了一個旅的敵人,進攻失利。前委當即決定,把部隊全部留給縣委,賀龍、周逸群等同志仍按中央原定的計劃,率少數人前往湘西北開辟工作。臨走前,前委在普濟觀召集洪湖地區縣、區委的負責同志開會,交待布置了擴大和發展洪湖革命根據地的任務。“并約定半年之后在公安會師”。[1]1928年春,在賀龍的生日(舊歷二月初九)之際,賀龍偕同周逸群等抵湘西桑植縣洪家關家鄉,受到大姐賀民英及鄉親們的熱烈歡迎。
湘鄂西前委所以選擇在湘鄂邊發展武裝,創立蘇區,一是湘鄂邊的反動統治較其他地方薄弱;二是賀龍在湘西一帶很有威望,對這里情況熟悉,他有不少部下在湘西一帶,賀龍可利用這個關系拉起部隊;三是地理條件好,進可以東出湘鄂中部,西入四川,南下貴州,退可以據以固守,生息發展。
賀龍到湘西桑植后,八個鄉的地方勢力都來拜見,八鄉地方勢力都有人槍,各霸一方,有時稱兄道弟,有時又互相火并。賀龍一到這兒,就向他們正式宣布:“大家再不要自相殘殺了。”“我是共產黨,我們要發動群眾,組織紅軍,建立工農革命政權。看你們愿不愿意參加?”此后,賀龍一面收集舊部,一面又對舊軍隊進行改造,廣泛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宣傳革命一定要勝利的道理。經過賀龍的號召、宣傳,到1928年3月,賀龍已組織了三、四千人的武裝。其來源是:一是利用親族關系召集的,其中有賀龍的大姐賀民英(香姑)等部一千多人;二是利用舊的隸屬關系召集的,其中有王炳南、鐘慎吾、李云清等部一千多人。根據中央授意,成立了工農革命軍,賀龍同志任軍長。張貼《工農革命軍布告》。
部隊剛編兩個團,國民黨反動軍隊乘我立足未穩之際就來進攻。由于部隊大多是利用親屬和隸屬關系召集的,內部不純,戰斗力不強,和敵人一接觸,逃散的很多。有的舊式農民武裝各帶各的部隊跑回自己管轄的地區去了。洪家關、苦竹坪兩次戰斗均未能把敵人擊退,部隊本身反而受到嚴重損失。為了縮小目標,周逸群和賀龍決定分頭進行活動,周逸群到沙市,領導鄂西特委,繼續組織荊江兩岸的武裝斗爭,后來和段德昌、段玉才等同志一起建立了紅六軍。賀龍和盧冬升同志則帶領少數人員轉到桑植、鶴峰等縣堅持開展游擊戰爭。這期間,反動軍隊的壓迫雖然較小,但是部隊內部情況非常復雜。有的堅持舊軍隊的作風,有的把親族及其他舊關系與革命軍隊內部關系混同起來,有的則是地主、富農家庭影響。這些人成了貫徹黨的政策的阻力。鑒于這些情況,賀龍為首的前委決定向這些有害傾向作斗爭:首先進行改編,正式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賀龍任軍長。同時加強了黨的領導,大隊以上均設了黨代表,加緊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訓練,在士兵中吸收黨員,對原有部隊進行徹底的改造;對于堅持錯誤、違反黨的政策的人,則給予嚴肅處理和教育。經過這樣整頓,工農革命軍有了新的起色,邁開了革命化的第一步。同時,“擴大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掀起廣大的農民起來斗爭。”[2]
8月20日,接湘西特委轉來湖南省委通告,要紅四軍東進,牽制敵軍對湘東紅軍的進攻。賀龍率紅四軍由桑植向石門開進。8月25日,工農革命軍進駐石門西北鄉之中心區域磨市,后來又轉到澧縣王家廠、大堰垱一帶游擊,鎮壓一批土劣和清鄉委員會,領導農民打土豪、燒契約,號召農民分配土地。湖南軍閥組織上萬兵力分三路向我革命軍進攻。9月7日工農革命軍轉向石門渫陽,翌日拂曉,敵軍左翼奔襲我軍軍部,部隊經所街退到泥沙,又遭敵人攻擊。是役,參謀長黃鰲和師長賀錦齋先后壯烈犧牲。部隊損失較大。賀龍只率200余人經鶴峰的“走馬坪退至桑(植)鶴(峰)交界”,旋又將部隊分散在群山中與敵展開斗爭。[3]
1928年初冬,工農革命軍只剩下一百多人,部隊在湘鄂邊界的高山叢林中,沒有吃的,沒有穿的,傷員沒處安插,彈藥無法補充。面對困難處境,賀龍不斷思考:“黨交給我的任務是搞紅軍,不是搞白軍。但是紅軍究竟怎么搞,根據地究竟怎么建設呢?”賀龍意識到用舊的封建關系建立的革命武裝是經不起風浪的,應該有一套新的做法。到底應該怎么做,賀龍心里還不大有數。賀龍非常苦悶。他想:越在這個時候越應設法與黨取得聯系,得到黨的指示。于是,賀龍派人去找鄂西特委,找周逸群。交通出發了,一直盼了二個月還無蹤影,就在這極端困難時刻,在賀龍家鄉堅持斗爭的姐姐賀民英來了。她送了一批洋布、子彈和銀元,看著面容憔悴的弟弟和疲憊不堪的同志們,賀民英對賀龍說:“過去別人跟著你是為了發財,現在這么苦跟著你干什么?是為了干革命,你們不是有CY、CP嗎?應當更好地組織起來。”賀龍在姐姐的鼓勵下決心整頓部隊(稱堰埡整頓)結果只剩下91個人、72條槍,建立了一個黨支部。這支小部隊人員雖不多,卻都是精華。他們覺悟高,立場堅定,在任何情況下都英勇頑強,不動搖。堰埡整頓后,部隊從堰埡出發,向咸豐的黑洞進軍,進入利川縣境。這一帶經濟文化非常落后,封建迷信甚行。這里到處都有所謂“神兵”(類似紅槍會),是有名的神兵窩。“神兵”雖然是迷信團體,但其成員大都是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為了反對軍閥、反對苛捐雜稅而組織起來的。于是賀龍就設法與之聯絡,結果爭取到二、三百名新兵。此時,部隊由91個人、72條槍,發展到200多人、100多支槍,又編了二個大隊。12月下旬,又攻占建始縣城,焚燒了縣公署的文件稅契,并發布了告工農貧民書。12月31日,又抵鶴峰鄔陽關,與早先派這里的汪毅夫取得聯系。1928年底,部隊攻入建始縣城,繳獲民團槍百余支,同時招收了一批勞動人民參加了隊伍,后來又收編了農民武裝陳宗瑜部200多人,這時全軍共有官兵400多人,步槍、連槍200余支。接著又打開鶴峰縣城,建立鶴峰縣蘇維埃政府,公布蘇維埃大綱,耕田農有法令,并派人四處發動群眾,分配土地,使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
1929年初,前委派出去的交通與黨的組織取得了聯系。周逸群不斷寫信來介紹了洪湖那邊熱火朝天的斗爭情況,傳達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經驗,并陸續派來了不少干部,加強了黨的工作,提高了紅軍政治素質。同時,黨中央也發來了不少重要指示和黨的“六大”決議。黨的指示,使賀龍和大家撥開了重重迷霧,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工農革命軍面目煥然一新。
1929年春,又先后收編土著武裝若干支,紅四軍增至1000余人,槍300余支。1929年6月,桑植城解放后,工農革命就有了二個縣和縣政權。此外還在龍山、宣恩、五峰、長陽、石門邊緣展開了工作,建立了縣、區政權,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也初具規模了。這時部隊的面目也有相當改變,新的建軍路線——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已經開始執行;又接受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連隊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加強了黨對部隊的領導,建立了政治機關,加強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區紅六軍會師以前,又堅決進行了幾次思想、組織整頓,大量吸收貧苦農民參軍。這樣,這支部隊逐漸改造與建設成新型的人民武裝。
7月,國民黨派一個團進犯桑植,賀龍采取誘敵深入,使敵由南岔渡口過河,敵過河后,我軍開始攻殺,迫其背水作戰,將其大部殲滅,并擊斃其團長周寒之。旅長向子云不甘失敗,復親率該部二千余人并一些地主武裝傾巢出犯,工農革命軍埋伏在城外山上大開四門,施了個“空城計”,誘其深入,等敵入城后,埋伏在山上的我軍一齊出動,敵被四面包圍,我軍將敵大部殲滅。向子云率少數人馬向后逃竄,在赤溪河邊,向子云急于逃命,拉著騾子泅水,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沒。這是湘西工農革命軍建立以來的第一次大捷,繳得長短槍1000余支。7月中下旬,在桑植對紅四軍再次整編,大隊、中隊改為團、營。這時全軍擴大到4000余人。8月上旬,中共湘鄂西特委為了打破敵人包圍,鞏固和擴大蘇區,決定由賀龍率紅四軍向大庸、慈利兩縣推進,以拔除桑植四周的團防點。9月上旬賀龍率部又返桑植。
10月下旬,反動派用2萬多人進攻湘鄂邊。鑒于敵強我弱,賀龍帶領部隊主動撤出桑植,轉至鶴峰、五峰、長陽、松滋等地發動群眾,開辟新區工作,以期與鄂西區聯成一片。1930年3月,賀龍領導的紅四軍根據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決議,東下與紅六軍會師。留一部分骨干和一部分游擊隊堅持湘鄂邊斗爭。1930年7月初,紅四軍與周逸群領導的紅六軍會師于公安城,組成紅二軍團。紅二軍團成立,標志湘鄂西革命斗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與湘豫皖、湘鄂贛紅色區域呼應,構成了對敵人統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漢的包圍。
二、賀龍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的啟示
1、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的實踐說明:賀龍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擴大武裝,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極端重要性。
八一南昌起義南下失敗后,賀龍主動提出回湘鄂西去拉起一支隊伍。賀龍、周逸群等1928年初到達湘鄂邊的監利縣境,當時只有二只手槍。在監利會合了賀錦齋領導的一支部隊,又集合了當地的兩支農民武裝,前后會合的三支隊伍,共有三百多支槍,人數更多些。打起了工農革命軍的旗幟。這便是湘鄂西前委領導下的最初武裝力量。接著他們在監利、石首、華容、南縣進行了年關斗爭,鼓舞了群眾斗爭情緒,隊伍發展到近千人。可惜的是,這樣一支在當時已經可觀的一支武裝,“由于當時前委農村根據地思想和政權觀念很模糊”,[4]結果把這支部隊交給地方,賀龍、周逸群、賀錦齋等離開部隊到湘西去了。部隊由于失去領導中心,結果完全失散和垮臺。
1928年3月,賀龍等到湘鄂邊的桑植縣,利用親族和隸屬關系又召集了三、四千人,緊接著在1928年4月國民黨乘賀龍部立足未穩之際,突然派兵進攻桑植城和洪家關,洪家關和苦竹坪兩戰均未能打退敵人的進攻,隊伍反而受到嚴重損失。由于隊伍內部情況非常復雜,舊軍隊習氣嚴重,“一部分軍官只愿拖隊捉肥豬稱土大王,不愿下去暴動,遂蓄意拖槍潛逃”;有個別紅軍領導人競“發表了許多違反黨的政策的意見”[5]事實說明:“用舊的封建關系建立的革命武裝,不經過徹底改造,是經不起風險的”,“依靠群眾建立的革命武裝才是鞏固的。”于是前委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大隊以上均設有黨代表,以幫助并監督軍官的工作與行動”[6]加緊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訓練,在士兵中吸收黨員,以期對原有部隊進行徹底的改造;對于堅持錯誤、違反政策的人,則給予嚴肅處理和教育。經過這樣整頓,工農革命軍才有了新的起色,邁開革命化的第一步。經過1928年冬天極端困難的考驗,1929年初,紅四軍取得了與中央的聯系。1929年3月,周恩來為中央起草的給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紹了井岡山朱毛建軍的經驗:“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隊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營委、團委等組織。因為每連都有組織,所以在平日及作戰時,都有黨的指導與幫助。據朱、毛處來人說,這個組織,感覺還好。將來你們部隊建黨時,這個經驗可以備你們參考。”[7]同時,黨中央也發來了不少重要指示和黨的“六大”決議,于是“紅四軍的行動綱領也明確起來。逐漸擺脫開不利的處境,一步步發展壯大。”[8]
以后,賀龍為首的前委又對工農革命軍的缺點采取:“(一)在農工會執行委員會中,及紅軍軍人中挑選學生一百二十名,開辦軍事政治訓練班,定期三月畢業,……訓練班有了專人負責,故成績尚好,現開學已有兩星期。(二)改造紅軍中黨的組織,并加緊黨內教育工作。(三)設兵士科,很正確地指導士兵委員會工作。(四)設法健全黨代表辦公廳的組織,提高黨的權威。(五)在軍事有相當穩定時,軍隊組織還有一個很大的整頓,……。”[9]湘鄂西前委對工農革命軍堅決實行了幾次整頓,又吸收貧苦農民參軍,這樣就把這部隊伍改造與建設成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裝。
賀龍還在實踐中運用了一套樸素的游擊戰的戰術。如“先發制人”。1929年7月赤溪河大捷中,賀龍運用“誘敵”、“迫敵”、“背水作戰”、“埋伏”、“誘其深入”。[10]8月,敵人20000多人攻湘鄂邊,鑒于敵強我弱,紅四軍主動撤出桑植城,轉自鶴峰、五峰、長陽、松滋等地,發動群眾,開辟工作。“總之,此間游擊的加強,云卿(即賀龍)以二十年施口隊的經驗,隨機應變,今后絕不致上敵人的大當。”[11]這些在實踐中形成的樸素的游擊戰的戰術思想,雖然沒有象朱德、毛澤東那樣進行了理論的科學性的概括,但賀龍這些戰術思想無疑地也是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來源之一。就是這樣,賀龍在曲折的斗爭實踐中摸索出擴大人民武裝、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一套辦法。
2、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亦說明:賀龍極端重視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
賀龍常說:“野雞有個山頭,白鶴有個灘頭。一支軍隊沒有根據地怎么行呢?”所以,每到一處,他都派出干部去做群眾工作,幫助受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即使戰斗頻繁,賀龍也總是抽出時間深入到窮苦人中間,了解老百姓疾苦。經過1928年的冬天,工農革命軍飽償了沒有根據地依托的痛苦,1929年初又得到黨的指示后,湘鄂邊根據地起了根本性變化。到1929年5月,占領了兩個縣城(鶴峰、桑植),此外,還在龍山、宣恩、五峰、長陽、石門邊緣開展工作,建立縣、區政權,摸索出建設根據地的一套做法,“湘鄂邊根據地也初具規模了。”[12]1930年夏,二、六兩軍團合編成紅二軍團后,湘鄂西根據地擴展到十七個縣。
3、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的實踐還說明:賀龍注意把鞏固革命根據地、擴大人民武裝同開展土地革命和根據地政權之建設密切結合起來。
1928年9月,賀龍給中央的報告中講到:“以后有(原文缺)黑洞、狗耳石等處為紅軍根據地(原文缺)極力準備暴動,一有相當基礎即建立蘇維埃和實行分配土地……”,“紅軍則分駐鄉村,掩護農民起來斗爭”,“……吸收其下層覺悟的群眾,成為黨的群眾,對于佃農和雇農分別加緊工作。”[13]1928年12月,工農革命軍打開鶴峰城,建立起工農民主政權,“派人四處發動群眾,分配土地,使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14]1929年舊歷八月八日湘鄂西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報告中又講到:“分派縣委委員及黨的特派員下鄉活動在農村中,建立黨的秘密組織,并限期成立各區區委或支部”“加派較有經驗之……同志下鄉工作,領導各區農運之發展”。在根據地組織一留守委員會,由縣委、蘇維埃政府和紅軍負責人組成。“懲治豪紳,進行沒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15]就在這1929年,白竹坪成立了桑植縣蘇維埃政府,工農兵當家作主人,擴大了紅軍,組織了赤衛隊、打土豪、分田地,窮苦人揚眉吐氣,地主、惡霸嚇跑了,白竹坪人民的革命和生產的熱情象火山一樣進發出來。1929年冬天,有個叛徒賀文志在洪家關一帶危害人民,與蘇維埃政府作對,蘇維埃政府就抓住了他,繳了他的槍。賀文志的叔父(洪家關的豪紳)賀士光知道后,打著“族老”的面子,坐著轎子到縣蘇維埃政府找賀龍求情,賀龍指示蘇維埃公審了賀士光,并發動農民抄了他的家,并打開賀士光家的谷倉,分糧給農民。
三、“賀龍式”與“朱德毛澤東式”工農武裝割據之比較
賀龍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實踐能否可以說賀龍已經確定了農村為中心的思想了呢?賀龍在1928年9月給中央的報告中講到:“紅軍停滯在桑植,于政治的作用太小,俟子彈的補充稍足時,我們必須開到石門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同時須向常德取包圍形勢……”。[16]周恩來于1929年3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賀龍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對賀龍等同志指出:“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17]可推斷賀龍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要占領大的城市。1930年5月,鄂西特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鄂西紅軍的教訓之一就是要“紅軍應當時時刻刻準備進攻中心城市,才能擴大政治影響”。[18]這些事實說明:“賀龍式”工農武裝割據只是從城市中心發展到重視鄉村的階段。即使是發展到這一階段,也是難能可貴的,是花了學費換來的。但還沒有發展到以鄉村作中心的階段。當時,共產國際、黨的六大精神和湖南省委還是“城市中心論”,只有毛澤東為代表的少數同志的思想發展到以鄉村作中心的階段。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長信中,已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各地先后發動多次武裝起義,所有這些起義都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反動統治勢力,擴大了革命影響,為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提供了經驗,奠定了基礎,為探索大革命失敗后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作出了貢獻。但是,把黨和人民在集體奮斗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加以科學的總結,找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性,提出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完整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并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19]賀龍開辟湘鄂邊革命根據地,搞工農武裝割據的實踐為毛澤東所提出的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受到毛澤東的贊美,一同被譽為“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20]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是正確的。
[1][2][3]李烈《賀龍手譜》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P102、P106、P107。
[4][8][10][12][14]賀龍“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爭”《星火燎原》選編之一。
[5][6][13][16]“賀龍同志給中央的報告”《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P32、P33-34、P30。
[7][17]《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P46、P17。
[9][11][15][18]“1929年舊歷八月初八賀龍代表湘鄂西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報告”《中共黨史參考資料》[5]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P585、P581、P583、P595。
[1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3版P9。
[20]《抗戰以前選集》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印第一集P139。
李孫強,(1949——),男,江蘇儀征人,中共安徽滁州市委黨校中共黨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