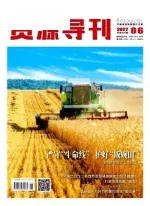杞人憂天我憂地
杞人憂天我憂地
□宋海峰
杞人憂天的故事已經人盡皆知,但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出來的國土工作者,對土地的關愛與生俱來,對土地的關注已成為職業習慣,從目前我國關系國計民生、十分稀缺、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現狀看,難免令人擔憂。
君不見,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化步伐不斷邁進,GDP數字不斷攀升,城市住宅不斷擴張等需大量占用土地項目的建設,有效的耕地面積在日益銳減,人均耕地面積在逐年下降,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壓力在不斷加大,國家糧食安全問題被越來越多的人擔心和關注,這絕對不是現代版的“杞人憂天”。
資料顯示,目前全國耕地面積為18.26億畝,比1996年的19.5億畝凈減少1.24億畝,相當于減少一個大省,每年以1240萬畝的速度減少,人均耕地僅為1.38畝,其中有9個省人均低于1畝,3個省人均少于0.5畝。同時,土地違法案件依然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全國發生土地違法案件2.2萬件,涉及土地面積11.7萬畝,其中耕地4.4萬畝。雖然違法數量和面積比上年有所下降,但是足以使人觸目驚心。
2004年以來,國家在嚴格土地管理,遏制和打擊土地違法案件方面,下了很大的決心,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從2008年開始又在全國范圍開展每年一次的土地衛片執法檢查工作,宏觀政策、查處辦法、問責手段都具備了,多層次、高規格、最嚴厲的執法手段都用上了,但從目前情況看,一些地方的土地違法行為仍屢禁不止,大量的土地閑置依然存在,未批先占、邊批邊占、批少占多、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等違法行為在一些地方和企業仍然有禁不止。
為什么國家先后采取多項措施,用最嚴厲的手段卻制止不住層出不窮的土地違法案件發生呢?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政績考核體系不科學,一些地方政府在“唯GDP”思想指導下,在城市建設工程中追求“大規劃”,為建新城而大拆遷,為上項目而大圈地,導致超量占用耕地,土地開而不發等閑置浪費現象仍然嚴重。二是“喊聲高,問聲低”,問責措施落實不到位。2008年6月1日15號令出臺以來,真正因土地違法受到問責的縣處級以上干部寥寥無幾,僅有幾個也是前邊免,后邊又異地當官,其結果是地照圈、法照違、官照做、職照升,使違法者沒有付出比守法者更高的代價,無形中助長了違法行為,使其更加肆無忌憚。三是利益驅動使一些違法者鋌而走險,一些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顯現政績,一些開發商靠炒地、圈地、倒地發財,一些企業靠多圈地產生效益。利益驅動使一些土地違法者有恃無恐地大量圈占、炒賣土地,稀缺的土地資源成了這些人的“搖錢樹”。四是保護耕地的責任感,土地稀缺的危機感,還沒有在全體公民特別是當權的公民中真正樹立起來,沒有形成違法可恥、守土有責的氛圍,僅靠弱勢群體的呼聲和現行落實不到位的條規的約束,難以和現行畸形權力抗衡。
如果不盡快建立政績考核捆綁機制,從土地財政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如果不進一步加大執法問責力度,真正硬起手來打擊土地違法行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調控發土地財者的利益,18億畝耕地將不再是紅線,13億人口的糧食安全問題將是人人擔憂的問題,“土地危機”的擔心將會彌漫整個社會,這絕非危言聳聽!
三門峽市國土資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