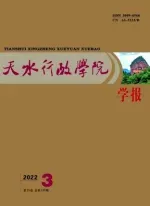企業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研究——以“雙匯”瘦肉精事件為例
史慧明
(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企業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研究
——以“雙匯”瘦肉精事件為例
史慧明
(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研究道德資本的經濟邏輯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種新型經濟價值觀和經濟倫理秩序,即德福一統,擁有道德資本的企業和個人將獲得更多的收益,反之,德福分裂的經濟價值觀必然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德福一統;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
一、問題的提出:“雙匯”瘦肉精事件的倫理反思
2011年3月15日上午,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播出了一期名為《“健美豬”真相》的3·15特別節目,披露了河南濟源雙匯食品有限公司收購用瘦肉精喂養的“健美豬”豬肉。此新聞一出,引起了全國人民關注,作為業內世界第三、亞洲和國內第一的雙匯集團深陷食品安全丑聞。3月31日上午,雙匯集團在漯河市體育館召開“雙匯萬人職工大會”,參會人員包括雙匯集團所有管理層、漯河本部職工、經銷商及新聞媒體,集團董事長萬隆再次向消費者致歉,并稱雙匯因“瘦肉精”事件受損超過121億元。
對“雙匯”瘦肉精事件的倫理反思,讓我們又重新回到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關于市場經濟的“邏輯預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家)是預設的“經濟人”,“經濟人”都有一種最大限度尋利的自然沖動,追求利益(利潤)的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理性要求和正當的經濟價值觀。斯密認為人們“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1]斯密的本意為是“經濟人”主觀利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因為利己的行為客觀上會增進公共利益,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倡導樹立利益優先、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價值觀,可以推進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在斯密看來,只要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存在,個人追求利益的動機和行為既促進了公眾利益的實現,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合乎道德的,哪怕是犧牲社會一些階級或者一些人個人的利益。“看不見的手”實際上是市場秩序井然的依據和動因,其作用遠比政府的有計劃、有目的行為更有效[2]。然而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和理性經濟價值觀解釋,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中被無情地推翻,現實的市場經濟中“無形手”的理論在很多領域出現失靈現象,不僅不能導致資源的優化配置,增進社會福利,還造成了市場經濟的痼疾——經濟危機與生產力的巨大破壞。
“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固然是利益主體自身的一種沖動和需要,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是正當的、理性的,這一倡導性的經濟價值觀鼓勵了“經濟人”的逐利行為。經濟事實證明,被鼓勵的個人的理性逐利行為,做出對自己利益最有利的選擇行為,而這種選擇所得來的結果卻是“集體的非理性”、“理性本身的非理性”。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認為,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在于市場機制本身,即市場無法解決公共物品供給、外部效應存在、信息不對稱、壟斷等問題[3];考察經濟人最大化自利行為的深層原因,與斯密倡導的“個人理性”的經濟價值觀有著直接的關聯。現代經濟倫理學認為,這種逐利沖動往往被兩種基本的社會要素所規制,那就是道德與法律強制。如果法制不健全、法治不成熟,就會出現不用付出代價或承擔少量代價便能使這種被壓抑甚久的沖動得到滿足的機會,而其他踐行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的主體相對來說卻是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能滿足自身的利益需要。具體地說,“雙匯”企業對成本—收益的考慮正是一種社會博弈方式,這種方式一經形成,其強大的外部制約力量會約束企業的行為,置身局外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管理層,企業與銷售者之間相互制衡的利益關系決定了,只有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才能促進他們各方的利益。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不能哄騙欺詐消費者,不能銷售偽劣商品,也不能與別的企業惡性競爭,管理者不能敷衍塞責,勞動者不能消極怠工。如果他們違背市場經濟道德的要求,就會損害別人的利益,別人一定會反過來使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就形成了對非道德行為的有效制衡。市場的殘酷競爭決定了企業必須考慮道德資本的存在,企業違背商業道德,就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維護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是離開他們,購買其他企業的商品,違背商業道德的企業其市場份額就會縮小,甚至還可能被虎視眈眈的其他企業所收購,非道德選擇的企業家因此可能失去他多年辛苦,甚至幾代人辛苦撐起的家業。
二、問題的分析:“德福一統”的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的解讀
研究道德資本的經濟價值觀是建立在道德資本作為一種宏觀的社會資本角度來進行解讀的,社會資本在20世紀20年代就被經濟學家提出并作研究,第一位對社會資本進行相對系統的現代性分析的是法國學者布爾迪厄。他在1979年的《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中,提出了三種資本形式: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20世紀90年代以后,社會資本成為一種流行的關鍵詞匯,成為國際機構頻繁使用的概念之一,同時也引起了眾多學者的注意。“盡管對于社會資本,不同的作者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義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存在于社會結構中的個人資源,它為結構內的行動者提供便利,包括規范、信任和網絡等形式。”[4]
道德資本在宏觀上表現為一種社會資本,必然影響和制約經濟制度的確立、變革,為經濟制度的變遷作出解釋。道德資本的概念是王小錫教授在21世紀初提出的富有原創意味的概念,所謂道德資本,從內涵上,它是指投入經濟運行過程,以傳統習俗、內心信念、社會輿論為主要手段,能夠有助于帶來剩余價值或創造新價值,從而實現經濟物品保值、增值的一切倫理價值符號;從外延上,它包括一切無明文規定的價值觀念、道德精神、民風民俗等等。從表現形態來看,道德資本在微觀個體層面,體現為一種人力資本;在中觀企業層面,體現為一種無形資本;在宏觀社會層面,體現為一種社會資本。德福一統是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中國正在經歷著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有其內在的倫理支撐,而道德資本正是通過形成一種共同的經濟價值觀來引導人們對新制度的認同,從而加速新舊制度的變遷。“沒有任何一套制度的建立不是在一定的價值追求和意識形態下實現的;同樣一次制度變遷過程,包括制度變遷的方向、方式,如果同人們關于‘正義’、‘公正’的觀念相吻合,即人們對制度變遷過程具有認同感,人們就愿意參與、支持這一過程,并為此暫時放棄某些個體利益。人們對制度變遷過程的價值認同感越強,愿意暫時犧牲個體利益的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5]道德資本中德福一統的經濟價值觀便是這樣一種共同的經濟價值觀,它要求人們區分“經濟人”與“道德人”,把經濟人與道德人有機統一。事實上,在現時代,“道德人”一定是“經濟人”的道德人,只有通過經濟行為過程和效益,才能體現和說明經濟行為主體的生存境界和行為價值;同時,“經濟人”也必須是“道德人”之經濟人,經濟行為主體只有統一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于一體,才不至于置經濟發展于畸形狀態下,也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要求[6]。
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在《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一書中描述了在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傳統價值觀與戰后現代化理想之間的沖突,列舉了南亞國家的12種“現代化理想”,包括理性、發展計劃、生產率的提高、平等化等以及具體的13種態度,但這些理想不得不與得到宗教支持的傳統價值觀競爭。繆爾達爾認為,要改變阻礙經濟發展的傳統價值觀,“從現代化理想的角度看,所需要的僅僅是消除非理性信仰及有關價值觀的形成基礎”[7]。著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也認為,“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運行依賴于強有力的價值觀和規范系統。”[8]實際上,要想使人們接受或形成某種價值觀念體系,這種觀念體系本身應該具有給予其擁有者或享用者使用價值的特性。道德資本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發揮作用時,與其他有形資本一樣都是滿足人們各種需求的稀缺資源,它的職能在于為人們提供了一套評價行為與學會如何生存、發展的工具。從滿足人類各種需求來說,道德資本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認知世界的價值觀體系。這一價值觀體系將一切事物和行為的價值進行排序,為我們做出選擇提供了極大的便捷,減少了人們判斷決策的代價。從價值層面看,這種對于新制度的價值認同能為個人帶來持續的收益。道德資本具有經濟邏輯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種新型經濟價值觀和經濟倫理秩序,即德福一統,擁有道德資本的企業和個人將獲得更多的收益,正確的道德行為選擇受到正激勵。降低積極倫理選擇行為的成本,建設一種德福一致的監督、賞罰機制,營造一片和諧的倫理氛圍,讓有“德”(這里的德是指倫理道德的資本化)者享“福”(這里的福是指給主體帶來價值的增殖),那么就可能大大普及積極的道德行為。
三、問題的對策:“德福一統”的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的實踐
公共地的悲劇告訴我們,追求私利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發動機,如果沒有德福一統的制度監督和約束,人人都不會采取有利于集體理性的行為,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進步。因為在道德資本的一面是收益,另一面將考慮道德成本。人們在作出行為選擇尤其是作出倫理選擇時,總是基于一定的良心思考,而良心的考量要轉化為現實的行為又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人們最初是選擇了節制的行為,可是當他們與無節制者比較成本與收益時,特別是在沒有監督制度的情況下,往往就會得到負激勵,作出自認為理性的非理性行為。“一個有良心的人,也許在履行道德義務時很少直接去想到回報,但卻不能不考慮成本”,“除了個別品德特別高尚和有堅定道德信念的人,一般的道德主體是很難始終如一地去堅持道德選擇的”[9]。
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種新型經濟價值觀和經濟倫理秩序,即德福一統的制度應注重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1.從主體的狀況來看基本層次的道德立法問題
從以往的道德教化來看,人們總是被要求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道德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義務。道德規范的確立來自于人們的經驗生活和某些超智慧的圣人賢士的反復提煉,人們把規范內化為信念、良心,外顯為道德行為,人在現實的生活中成為純粹的義務主體。而中國目前的生活狀態發生變化,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擴大,城市化進程加速,傳統社會輿論、熟人環境對人們的約束力大大減弱;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也不斷沖擊著人們的內心信念,就整個社會來說,難以形成統一的價值規范體系,甚至會形成矛盾、沖突的社會價值理念。所以,混沌的思維只能使得價值主體在價值實踐過程中進行錯誤的行為,每一個利益主體總是按照最大化實現自身利益行為,難以形成共同的社會價值目標。各個利益主體預設的價值目標要么偏離社會價值總目標,要么在實現正確價值目標的過程中采取非道德的手段,所以把有利于整個社會(主要指經濟、政治領域)有序運行的道德規范以法制的形式確立,倡導統一的價值理念,這樣可以減少大量無序、失范行為。
2.道德失范行為的嚴格懲戒問題
對于目前社會中存在的失信行為,因為沒有得到及時的、嚴厲的處罰,所以失范行為屢禁不止。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總是在成本與收益之間博弈,道德失范的機會成本如果大于收益,企業的非道德行為就會受到限制。在倡導德福一統的道德資本經濟價值觀的同時,加強道德資本的投入,盡快把較低層次的道德制度化,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家庭領域和職業領域率先執行,運用道德資本的市場機制發揮經濟懲罰作用。其次,是政府部門依法對失信行為進行行政處罰,《統計法》、《建筑法》、《法官法》、《檢察官法》、《教師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出臺是強有力的保證。再次,試行企業道德失范懲戒誅連制,企業的道德失范行為固然是出自自身“經濟人”的理性選擇,但當地政府監管部門疏忽與縱容,利益的裙帶關系讓企業有了失范的理由與依賴,所以,打破企業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的利益裙帶關系,試行誅連制是實踐操作維度的勇敢嘗試。
3.建設信用代碼問題
建設信用代碼可有兩個方案選擇,一是政府強制的政務代碼(如個人身份證代碼、組織機構代碼等);二是社會自愿的商務代碼(如銀行貸款證號碼、企業誠信編碼等)[10]。在美國,信用局向客房出售的消費者個人信用調查報告,其內容、格式都有嚴格的法律限制,通常情況下,一份標準的消費者個人信用調查報告應該包括辨識信息、信用信息、公共記錄信息、查詢信息四個部分。可以在總結我國經濟實踐和借鑒外國信用體系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考慮建設中國的信用代碼。在國內也有類似的制度探索,在青島市經營的78304家企業的詳細信息已被錄入該數據庫。同時,數據庫面向社會開放,失信企業名單在青島“紅盾網”上發布。2004年3月9日青島3282家失信企業遭到公開曝光,其法人代表也被示以“紅牌”——3年內不得以法人代表人身份注冊新公司。同時,615家企業因誠信經營被認定為2003年度年檢免檢企業,并且今后到工商部門辦理業務,還可享受直通車服務和信息查詢免費等。圍繞建立企業誠信檔案,青島市工商局在全國較早制定了《企業信用管理辦法》。《辦法》設定5個大類、4個級別、340多個數據項,涵蓋涉及企業信用信息的主要內容,包括身份信息、良好信息、提示信息、警示信息和綜合信息[11]。
4.道德資本管理問題
信用是道德資本中最富操作性的項目,在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有專門管理信用的機構。個人信用管理、調查主要由商業化的消費者資信調查服務公司進行,即通常所說的信用局。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家信用局分別是英國的Experian、美國的Equifax和Trans Bureau,三大公司業務的觸角涵蓋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每年僅出售消費者個人信用報告項的收入高達15億美元。以總部設在亞特蘭大的Equifax公司為例,它的業務主要集中在信用服務和保險信息服務兩個方面[12]。中國必須從現實存在的經濟發展狀況出發,吸取經驗和教訓,努力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道德資本管理機構,把個人、企業、政府的信用記錄管好、用好,為經濟建設服務,既要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又要注意保護商業秘密。·
[1](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7.
[2]章海山.經濟倫理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9-11.
[3]王小錫.經濟道德觀視閾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論批判[J].江蘇社會科學,2009,(1).
[4]張其仔.新經濟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61.
[5]王躍生.非正式約束、經濟市場化、制度變遷[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7,(3).
[6]王小錫.道德資本與經濟倫理—王小錫自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
[7]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42.
[8]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61.
[9]羅能生.倫理道德的經濟分析[J].吉首大學學報,2000,(3).
[10]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經濟藍皮書(2003):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40.
[11]http://www.xinhuanet.com,新華網山東頻道,2004-03-11.
[12]蘇東斌,袁易明.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92.
On the Valua of Moral Capital Economic
SHI Hui-m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Study of the economic logic of moral capital,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new economic order of values and economic ethics,the telford and unification,with moral capital of th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will get more revenue,whereas split telford necessarily hinder economic values,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elford and wnification;noral capital;economic value
F279.23
A
1009-6566(2011)04-0020-04
2011-04-11
史慧明(1977—),男,江蘇常州人,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