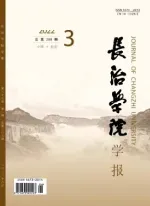上黨賽社面具造型及其審美意境分析
王劍芳
(山西大學 美術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上黨賽社面具造型及其審美意境分析
王劍芳
(山西大學 美術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上黨賽社面具造型與審美意境,與中國民間美術的歷史相關。對上黨賽社面具造型的研究,既可探究中國藝術固有的寫意傳神、變形夸張手法的由來發展,又可實證這種藝術風格的形成發展實源于民間藝人的不斷創造。文章既從面具的造型和審美意境入手,研究中國民間美術與中國傳統藝術的關系。
賽社面具;造型;審美
上黨,《釋名》曰:“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上黨地區位于山西省的東南部,即今長治、晉城兩市。它是由群山包圍起來的一塊高地。其東南部為太行山脈,與今河北、河南二省分界;西南部為王屋、中條二山,與今河南省分界;西面是太岳山脈;北面為五云山、八賦嶺等山地。上黨地區地高勢險,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狄子奇《國策地名考》曰“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其意即此。上黨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農耕文明發祥地,古老的傳說——諸如神嘗百草、后羿射日——都起源于此,至今民間仍保留有大量遺跡,成為古老民間賽社形成的基礎。早在春秋時已有“禱賽”之說,即“春祈秋報……祈一年之雨露,報一年土功之養長”。在祭賽過程中,逐漸出現了象征原始氏族圖騰崇拜的面具表演。上黨賽社面具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儒、釋、道、巫的宗教意識,同時又融合了當地民俗、民間彩塑、面塑、繪畫等多方面的內容,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
一、上黨賽社面具造型語言特征
根據T.利普斯的分類,造型藝術大體可分為形象藝術和空間藝術兩種。形象藝術指社會的具體形象和觀念形象化的繪畫、雕塑等,即所謂的再現藝術;而空間藝術是指以抽象的體積和空間構成的工藝美術、建筑、設計等。這兩種類型在造型藝術發展史中并存。上黨賽社面具被賦予了神秘而復雜的種種宗教和民俗的含義,它本身就是一種形象藝術,屬于造型藝術的一種,同時遵循著造型藝術的規律與原則。從整體上看,賽社面具的造型渾圓厚實、結構嚴謹、制作嫻熟,形象夸張有度,以體現人物的神韻為主,并顯示出粗獷拙樸之美。其造型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外形渾圓厚重
上黨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人們與外界交流甚少,相對閉塞。道光《壺關縣志》記載曰:“上黨之俗,質直好禮,勤儉力穡,民勇于公役,怯于私斗,自昔稱為易治。”該區域內的民眾終日臉朝黃土背朝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勤儉持家,風俗純厚。民間藝人在塑造面具形象時,必然要結合身邊人物的形象特征。甚至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來塑造神的。這樣,面具人物形象就與該地的民情風俗、審美意趣、面貌氣質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渾圓厚實”形象特征,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除此,造型特征也受到材料的限制,上黨賽社面具的原料大多為紙漿,這使得其造型不至于象木質面具那樣棱角分明,因此形成了紙漿面具與木質面具的不同特征,即前者主要靠“塑”,后者主要靠“雕”。以此為基礎,最終導致了上黨賽社面具有“渾圓厚實”的特色。
(二)形象寫實生動、夸張有度
在造型藝術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現手法是寫實。但是,與西方造型方式不同,中國傳統的寫實造型其思維方式傾向于概括性、直觀性、感性;而西方造型思維方式傾向于歸納性、分析性、理性。在藝術形式上則表現為:中國追求的是以造型形式來傳達個人的審美傾向、品位追求以及境界趣味;而西方造型形式則傾向用畫面來分析客觀世界。中國傳統造型重在強調人物的內在精神,并可將意象造型蘊涵于其中,而不拘囿于形象表面的真實準確。以唐代與宋代雕塑的不同表現形式為例,唐塑以裝飾取勝,宋塑以寫實為長,但仍體現出傳神的意蘊。在現今保存下來的眾多上黨古廟中,宋塑占在很大比重,并且均以面部表情變化的表現手法在藝術領域享有盛譽,得到專家學者的嘖嘖稱贊,成為此方面的杰作。上黨面具作為本地域藝術的一種,必然得此種土壤之滋潤,一方面以寫實見長,另一方面又強調寫意傳神,兼具夸張變形之態勢,在神怪的塑造方面尤其突出。這些在現場表演過程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如潞城市賈村賽社中《跳監齋》中的監齋面具,就可見到“三頭六臂,青面獠牙”的形象。這種將寫實與寫意、形似與神似的有機結合,在更廣泛的藝術空間中展現了上黨賽社面具的特色,不僅使民眾感到了藝術的真實與貼切,同時又增加了藝術表現手法的多樣性;既體現了強烈的地域景觀,又使藝術造型更加豐滿,在生活與藝術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使藝術具有了合理的生活基礎,生活在藝術中得到了升華。
二、上黨賽社面具的審美意境
(一)多學科的審美認知價值
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賽社祭祀文化,上黨賽社面具造型具有多學科的審美認知價值。從宗教角度來看,反映出古代社會的禮教和祭祀程序,蘊含著宗教禮儀的人文特征,上黨賽社面具非常注重傳統宗教觀念。塑造形式上,為了達到“天庭飽滿、地闊方圓”的正統觀念,更加講究飽滿圓潤;地域上,上黨地區寺廟眾多,而且有很多結合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三教堂,如長治市郊區的觀音堂明代懸塑,就是集儒、釋、道三教于一體的群體彩塑。受宗教和宗教雕塑藝術的影響,上黨賽社面具大都具備強烈的符號性特征,如長治市潞城王家樂戶的八仙面具。同時,也體現了變化的審美意識,如宗教的生殖崇拜、圖騰崇拜逐漸退出,儒家的道德崇拜、人格崇拜的藝術價值取向的突出。上黨賽社面具又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與貴州的地戲文化、藏族、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的儺戲文化差異也是很大的。賽社文化中以沒有了巫術色彩,娛情已成其主調,而在儺戲文化中,可以看到巫術的許多原始形態,具有濃郁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禮儀。如此等等,均具有很高的文化人類學意義和認知價值。
(二)表演形式多樣化、體現審美的娛情價值
作為傳統民間藝術的賽社文化有著強烈的審美價值追求。首先,賽社面具藝術,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演變,至明清時期形成的“大頭和尚”、“監齋”、“劉翠”、道教的“八仙面具”等等,衍化出多種類型,它們所呈現出的色彩美、造型美、裝飾美以及象征性、世俗性等,與民眾的審美與娛樂需要相符合,貫徹于他們的審美意識之中。其次,通過賽社祭祀走向世俗。早在上古時期,先民除了儺祭之外,還有臘祭、雩祭、社祭等。以春季和秋季祭祀為主即春祈風調雨順,秋報五谷豐登。明清時期,向民間歲時風俗靠攏,走向社火化、習俗化。賽社文化中派生出的隊戲、雜戲等,表演場所也走出賽社活動中特定場所的限制,走向市井與鄉村。如《除瘟》列隊在鄉村行走,邊走邊演。內容漸漸遠離宗教與巫術,而有越來越強的世俗娛情意味,唱腔和鼓點也相對簡單,內容也趨于世俗化,將寓教于樂參入其中,體現審美的娛情價值。
上黨賽社在長期的表演過程中,形成了多種多樣的劇目,戴面具表演成為酬神祭祀的主要方式。潞城市賈村四月四古廟會演出時,每次都要表演《猿猴脫殼》、《大頭和尚戲柳翠》、《跳監齋》、《八仙慶壽》等,而在《斬旱魃》、《除瘟》等帶有一定儺成分的表演中,則更體現了民眾對神靈敬重的心情以及娛神娛人的祭賽目的。如此行為,在神靈的扮演者與觀眾看來,面具并不是美術家贊不絕口的工藝品,也不是戲劇家所講的道具,而是代表著神圣的幽密,是天人溝通、仙凡交往的工具,是由人到仙的靈魂載體。一張面具,拉開了世俗社會與天上神仙之間的距離,不僅讓觀眾明白,演員并非演員,而是代表著神靈;也讓扮演者明白,自己已非俗人,其要表演的是神仙的思想。面具使人們徘徊在現實生活與想像生活之間,使人們可以暫時忘記世俗的緊張與不滿,在虛幻的生活中得到心靈上的一絲慰藉。故而巫詞中說道:“不戴面具是凡人,戴了面具是神靈”,一語道破其中奧秘。 賽社表演的目的不僅在娛神,更重要的在娛人,明清以后更是如此。民眾如此廣泛地參與賽社,即是因為賽社可以使他們的心情得到放松,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休閑,在心靈上得到滿足。詼諧幽默的表現手法、具有地域特色的面具、虛幻飄渺的想像,充分展現了神人共娛的祭賽目的。在《猿猴脫殼》這種古老演劇中,樂戶頭戴猿猴面具,伴隨著鼓點做一些簡單的類似猿猴形象特征的表演,既可以挑逗周圍的觀眾,亦可以取食神案前的祭品。偷吃后側臥于神案前的地毯上作祭拜形狀。這時,雜役拿盛敷面的篩蘿上場,在猿猴上方將敷面篩到猿猴身上和地毯上。曬畢,猿猴離去,留下一猿猴叩拜的平面剪影圖形。這種將立體形象轉化為平面形象的表演形式,類似于當代的行為藝術,帶給觀者強烈的視覺感受。
賽社面具是晉東南地區賽社活動中的重要表演面具,是中國民間工藝的一朵奇葩,不僅在中國傳統的面具中獨樹一幟,而且具有獨特的內涵和神韻。研究賽社面具,既有審美價值,又有現實意義。
[1](英)弗雷澤.金枝(上、下)[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2]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3]顧樸光.中國民間面具[M].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
[4]石林生,徐建群.黃河三峽儺文化[M].甘肅:甘肅文化出版社,2010.
[5]林河.中國巫儺史[M].廣東:花城出版社,2001.
G122
A
1673-2014(2011)03-0034-02
2011-01-24
王劍芳(1977— ),男,山西澤州人,碩士,主要從事視覺傳達設計理論研究。
(責任編輯 柴廣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