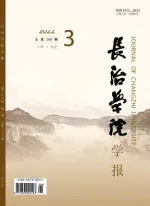當代民族聲樂作品演唱中的“依字行腔”辨析
音 璠
(長治學院 音樂舞蹈系,山西 長 治 046011)
當代民族聲樂作品演唱中的“依字行腔”辨析
音 璠
(長治學院 音樂舞蹈系,山西 長 治 046011)
“依字行腔”是中國千百年來傳統歌唱的藝決和經驗總結,是當代中國聲樂作品創作中一直使用的傳統創腔手法,也是歌唱語言的重要表現手段之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我國漢語講究字調和語調,聲調不同字義、語義亦不同,甚至意思完全相反。在歌唱中對歌詞的語言情態、語調、語氣和語勢等的處理手法不同,音樂的表現力亦不同,講究音調隨字調。因此,了解、繼承、掌握和運用“依字行腔”的方法,在民族聲樂作品的演唱中才能做到音調隨字調、以字正音、字正腔圓,達到字聲巧妙結合的藝術效果,使歌唱更加完美、流暢,對于歌曲演唱水平的提高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民族聲樂作品;“依字行腔”;音調隨字調
“依字行腔”是中國千百年來傳統歌唱的藝決和經驗總結,是我國戲曲唱腔的最大特征之一,是當代中國聲樂作品創作中一直使用的傳統創腔手法,也是歌唱語言的重要表現手段之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依字行腔”是京劇大師程硯秋較早提出來的,建國后于會泳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系研究》專著,對這一規律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作為國粹藝術的昆曲,六百年來一直按照“依字行腔”來譜曲、行腔。它準確地揭示了漢語和音樂之間的關系。
所謂“依字行腔”,就是依照字音的結構來歌唱,“說”是“唱”的依據與基礎,要求“腔隨字走”、“字領腔行”。曲調的進行應以字調的升降為依據,音調隨字調,歌唱才能字音準確,行腔圓滿。“字正腔圓”是我國傳統聲樂藝術的重要創造原則,明·魏良輔《曲律》中記有:“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說明了字與腔之間的辨證關系。而“依字行腔”、“腔隨字走”、“字領腔行”,是“字正腔圓”的重要表現方法和步驟。“依字行腔”把正字音放在了首位,而腔隨其后,做到字正、音清、腔圓三者合一。
一、民族聲樂作品演唱中“依字行腔”的作用與意義
聲樂作品是詩與音樂的有機結合,詩的語言形象為音樂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藝術構思的空間,其內容、形式、結構、韻律和節奏,都對音樂的表現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歌詞的自然語調和韻律,及其在不同情感體現中的變化與表現,是聲樂作品旋律體現的基礎。漢語音節結構的基本成分是聲母、韻母與聲調。一個音節或字在單獨發音時,不僅有聲、韻,還有高低、升降的音高變化,我們把這種變化叫做聲調或字調。而把一個音節或字的高低、升降變化的實際讀音或具體音高形式,稱為調值。漢語語音以北京語音為普通話標準,有四種調值。一聲調值為55,二聲調值為35,三聲調值為214,4聲調值為51。四聲在歌唱中調值的具體音高是相對音高,是通過字音之間在旋律中相互比較來體現的。我國漢語講究字調和語調,同樣一個字或一句話,由于咬字吐詞及語言聲調的不同會引起字義或語義的變化,甚至意思完全相反。聲調則具有顯著的區別詞義的作用,如:只求——知秋,燈塔——等他,聲韻相同而聲調不同,如果發音不準確,字義則完全不同。由于聲調的抑揚,能增強語言的韻律感和音樂性,尤其在古典詩詞中平仄對應的變化表現得尤為突出。除了戲曲和曲藝的唱詞,原則上仍要求單句最后一個字為仄聲字,雙字韻腳為平聲字外,現在一般歌曲的歌詞平仄要求已不十分嚴格。歌唱中出現的“音不正”或“倒字”現象,就是因為字的聲調與腔的旋律沒能夠和諧統一。
曲調不是字調的簡單翻譯,他既不能影響四聲的表義功能,又要為唱腔的表現提供更為廣闊的回旋音域。因此,在歌唱中既要把握原字調的高低、升降、曲直、長短的具體形式,還要注意字調在曲調旋律中體現的變化關系。不僅曲作者要根據詞的字調變化譜曲,演唱者也要“依字行腔”,在民歌中,那些表達特殊風格的語言,也要與聲調緊密結合來體現。如:《沂蒙山我的娘親親》中,“娘”字在普通話中的語調值是35,在歌唱中,就要以山東話“娘”的語調四聲來演唱,使其更具地方色彩。因此,掌握漢語聲調的四聲平仄規律,無論對于撰詞諧律、譜曲創腔,還是演唱行腔,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與作用。
歌曲的音樂性雖然主要從曲調中體現出來,但在歌唱中對歌詞的語言情態、語調、語氣和語勢等的處理手法不同,音樂的表現力亦不同,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曲調的音樂性與表現力。同一曲調由于語言的處理不同而表現各異,有的委婉深情,有的絢麗明朗,有的柔美纖細,有的質樸含蓄等。語言不僅是聲樂作品創作的基礎,也是聲樂演唱和教學的基礎。在傳統民族聲樂藝術中,大部分演唱的曲調是依聲填詞的,詞曲結合要達到完美和諧,是靠演唱時的潤腔修飾,將字的聲、韻和調的發音、自然趨勢與曲調旋律節奏和諧一致,使字與腔達到完美統一,才能達到字正腔圓的效果。因此,了解、繼承、掌握和運用“依字行腔”的方法,在演唱中做到以字正音、字正腔圓,達到字聲巧妙結合的藝術效果,歌唱將會更加完美、流暢,對于當代民族聲樂作品演唱水平的提高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對我國傳統歌唱藝決和歌唱語言的運用與傳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依字行腔”的藝術特征——“音調隨字調”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多種語言或語種的表現以及其他因素,形成了民族獨特的演唱風格與技巧,使得我國民族聲樂藝術具有了濃郁的生活氣息,以情感真摯質樸、聲腔優美圓潤、語言鮮明生動、風格瑰麗多姿為特點。歌唱中的“依字行腔”具有“音調隨字調”的藝術特征。漢語咬字方法的獨特性,形成當代民族唱法聲腔及音色的基礎,使它獨具一格;其次是由于漢語特有的歸韻收音方法,形成了完美的咬字收音過程。“依字行腔”的最終目的就是在演唱中做到“以字正音”、“字正腔圓”,達到字聲巧妙結合的藝術效果,使歌唱更加完美、流暢。
清朝末年,西洋作曲技法傳入中國。受西洋作曲技法的影響,作曲者忽視了歌詞的聲調,而是根據歌詞譜好曲子后,再將歌詞直接填進去,使得許多創作歌曲中存在著“以字就腔”的現象。而歌唱者也普遍存在著不進行二度創作、按部就班地照譜宣唱的弊病,局限于曲譜所規定的音符、時值、音高、節拍、節奏、速度等,不進行適當的藝術處理,使得歌唱索然無味,卻以為這是“尊重原作”。而“音調隨字調”則講究曲調的進行以字調的升降為依據,因而成為“依字行腔”的重要藝術特征。
三、“依字行腔”的藝術規律和方法
“依字行腔”的獨具一格特色的形成首先是因為漢語的咬字方法具有的獨特性,這也是形成當代民族唱法聲腔及音色的基礎,其次是由于漢語特有的歸韻收音方法,形成了完美的咬字收音過程。
1、“依字行腔”中咬字、吐字講究嚴格的藝術規律
“依字行腔”中注重歌唱中的咬字與吐字,起音強調字頭要叼緊,講究字頭與咬字的“噴口”的大小和強弱。“字頭”是聲母音節的開頭部分,漢語中有22個聲母,聲母由輔音充當,而輔音的特點是時程短,音勢弱,很容易受干擾,也容易出現吃字的現象,從而影響咬字的清晰度和可懂度。咬字強調的是字頭聲母部分的破阻,因此,要特別強調歌唱中“四呼”、“五音”的口型與發音著力的部位。吐字一般指字腹和字尾部分的發音,漢語中的韻母有36個,占時值較長,歌唱時響度最大,是字的主體部分。字腹是韻母中的主要母音,口腔開度大,在演唱中,要求音值引長延伸而不變形。傳統民族聲樂藝術演唱中,講究字尾的歸韻與收聲,按相同或相近韻母歸韻,有歸韻“十三轍”。要求字尾必須交待清楚,歸韻要收穩,避免字音發生變化。在歌唱中做到字頭重咬,字腹保持,字尾收清,使歌唱“字正腔圓”。
2、“依字行腔”的技巧和方法
在民族聲樂作品的演唱中應注意,曲調并非字調的簡單翻譯,要適宜于字的韻律聲情的表現,在作曲家將字調與曲調有機結合的基礎上,演唱者也要根據字音的語勢以及情感變化要求,進行潤腔或創腔處理,充分發揮聲調抑揚頓挫的藝術效果。演唱中的二度創作,既要發揮唱腔旋律的音樂形象,又要使字音字調符合唱腔旋律的行腔趨勢,是字調與曲調有機結合,在不影響曲調旋律風格的情況下,充分運用裝飾音等手法,調整曲調旋律中字音的音高趨勢,在有矛盾沖突的地方,適當變更音符與音型,使歌唱中的字音清晰,字義明了。“依字行腔”要求歌唱者正確掌握四聲調值的音高變化,掌握字的音高位置和走向,音調隨字調,以字的音調來行腔。在歌唱中“依字行腔”是對曲調的潤飾、烘托、渲染、補充、豐富,以彌補曲調的呆板,既調整了音調與字調的矛盾,又進一步刻畫了音樂形象。“依字行腔”的方法有:
(1)運用裝飾音的手法,使音調隨字調,調整曲調旋律中字音的音高趨勢。在民族聲樂作品的演唱中進行“依字行腔”,使音調隨字調,就應在把握民族咬字、吐字的風格及聲調特點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行腔中的各種技法如:倚音、滑音、顫音、波音等,給聲腔加以潤色,按字音的調值來演唱,我們把這種演唱方法稱為“潤腔”。其裝飾音的運用,主要是強調對旋律的潤色加味,增強表情意義。如:《梅花引》(韓靜霆詞,徐沛東曲)中,“回眸一望”、“臨風一笑”中的“一”字,按譜唱出讓人聽到的是“一往”、“一小”,不僅破壞了旋律美,而且字意不明。運用的裝飾音方法,在其音“re”前加一個前倚音“do”,不僅旋律柔美,字意也明晰。此曲中還有“誰是我知音”中的“誰”字,也應在其“do”音前加一前倚音“la”,而不至于使人聽到的是平聲的“shēi”。
(2)在有矛盾沖突的地方,適當變更音符與音型,使歌唱中的字音清晰,字義明了。如:民族聲樂作品《斷橋遺夢》(韓靜霆詞,趙季平曲)中,二段歌詞“上天入地只求”中的“只求”二字,如果按部就班地按譜演唱,聽到的不是“只求”而是“知秋”,使字意完全改變。在不影響曲調旋律風格的情況下,運用變更音符和裝飾音的方法,使“只”字上的“do”音變為“la”,“求”字上的“do”音前加一個前倚音“la”,使音調隨字調,不僅使字意明確清晰,而且對演唱曲調起到了潤飾和豐富的效果。
總之,中國傳統的民族聲樂理論不僅具有獨特的審美標準和豐富的內涵,同時又顯示出演唱技巧和演唱方法等方面的科學性。“依字行腔”的方法只有在立足于漢語語言的基礎上,通過對咬字、吐字、歸韻及潤腔的正確合理運用,在演唱中才能做到“以字正音”、“字正腔圓”,達到字聲巧妙結合、音調隨字調的藝術效果,才能使歌唱聲音更加舒展、流暢,潤腔更加細膩圓潤、豐富靈活,使咬字吐字清晰、準確而完美。
[1]鄒長海,聲樂藝術語言學:講話與歌唱[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7.
[2]鄒本初,歌唱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11.
[3]余篤剛,聲樂語言藝術[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2.8.
[4]許講真,漢族民歌潤腔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9.
J616.22
A
1673-2014(2011)06-0059-03
2011—11—07
山西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編號QZ-06014)。
音 璠(1964— ),女,北京人,講師,主要從事聲樂教學與教學法的研究。
(責任編輯 柴廣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