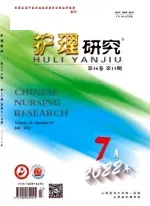國內限制性液體復蘇在創傷失血性休克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支淑華
創傷是當今人類一大公害,約占全球死亡率的7%,據統計,創傷是美國45歲以下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據資料顯示,我國每年死于創傷的總人數達70萬人,傷者達數百萬人,創傷已成為我國人口的第4位死因[1]。而創傷失血性休克無論在平時還是戰時都是一種常見的臨床危急綜合征。有資料統計,全球每年的創傷約有20%因未能得到及時的救治而死亡[2]。而創傷中因大出血引起休克占首位,因此控制出血是搶救創傷失血性休克的緊急措施[3]。以往,對于創傷失血性休克,傳統觀念和臨床措施是努力盡早地充分進行液體復蘇,新的液體復蘇認為:在活動性出血控制前積極地進行液體復蘇會增加出血量,使并發癥和病死率增加。因此,在創傷失血性休克早期進行限制性液體復蘇,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現就限制性液體復蘇的應用進展綜述如下。
1 限制性液體復蘇的概念
限制性液體復蘇亦稱低壓性液體復蘇或延遲液體復蘇,是指機體處于有活動性出血的創傷失血休克時,通過控制液體輸入的速度,使血壓維持在較低水平,直至徹底止血。
近年來,隨著對休克病理生理研究的不斷深入,并通過大量的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表明,早期大量、快速輸入晶體液體后使傷者面臨“死亡三聯征”——代謝性酸中毒、凝血功能障礙和低體溫的威脅。因此,在創傷失血性休克早期進行限制性液體復蘇,尋求一個復蘇平衡點,既可通過液體復蘇適當地恢復組織器官的血液灌注,又不至于過多地擾亂機體的代償機制和內環境。故創傷失血性休克,尤其是有活動性出血、在手術徹底止血前不予大量的液體輸入,而是限制液體的輸入量,維持機體的基本需求,在手術止血后再進行大量的液體復蘇,這稱為限制性液體復蘇[4,5]。
2 限制性液體復蘇對創傷性休克病人影響的臨床研究
張吉新等[6]回顧性分析了536例未控制出血的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的液體復蘇方法,其中常規液體復蘇組282例,限制液體復蘇組254例,比較常規液體復蘇組和限制性液體復蘇組的治愈率、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的發生率及病死率。結果常規液體復蘇組治愈率為63.5%,病死率 36.5%,ARDS發生率為23.8%,MODS發生率為35.1%;限制性液體復蘇組治愈率為82.7%,病死率17.3%,ARDS發生率為8.7%,MODS發生率為16.5%。組間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是限制性液體復蘇治療,能減少未控制出血的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MODS和ARDS的發生率,提高其治愈率。結論支持限制性液體復蘇的效果。
楊祖清等[7]對243例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進行充分液體復蘇和限制性液體復蘇的對比研究發現,充分液體復蘇組在到達手術室前平均輸液2 930 mL,平均動脈壓(MAP)維持在60 mmHg~80 mmHg(1 mmHg=0.133 kPa),死亡48例(病死率為37.80%),存活者(79例)中發生并發癥 30例(37.97%)。限制液體復蘇組平均輸液630 mL,MAP維持在40 mmHg~60 mmHg,死亡27例(病死率為23.28%),存活病人89例中有并發癥發生的18例(20.22%)。兩組比較病死率及存活病例并發癥的發生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黃善灶[8]對150例嚴重多發傷失血性休克病人進行充分液體復蘇和限制性液體復蘇,比較兩組病死率、ARDS、MODS、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急性腎衰竭(ARF)的發生率。結果充分液體復蘇組病死率31.1%,ARDS發生率為33.8%,MODS發生率39.2%,DIC發生率20.3%,ARF發生率14.9%;限制性液體復蘇組病死率17.1%,A RDS發生率17.1%,MODS發生率18.4%,DIC發生率11.8%,ARF發生率為13.2%。兩組病死率、治愈率及并發癥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 RF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以上3項不同的臨床研究表明,未止血前限制性液體復蘇在減少失血性休克病人的器官衰竭等并發癥發生率和病死率方面有明顯的優勢。
3 限制性液體復蘇的實驗研究
為證明臨床中限制性液體復蘇對于搶救失血性病人的科學有效性,張愛華等[9]將60只大鼠分為正常對照組、休克不復蘇組、限制性液體復蘇組、大量液體復蘇組。各液體復蘇組在大鼠MAP降至35 mmHg~40 mmHg時分別給予生理鹽水灌注,使血壓維持在各相應水平。輸液1 h后,各液體復蘇組均給予手術止血、回輸血液及給予足量的液體輸注,保持大鼠的M AP≥90 mmHg。監測出血量、輸液量、存活時間、存活率、堿缺失、血細胞比積、心腦腎功能的變化。結果創傷失血性休克早期在出血未控制的情況下,大量液體復蘇組出血量和輸液量明顯大于限制性液體復蘇組。限制性液體復蘇組大鼠的心、腦、腎病理學損害明顯輕于大量液體復蘇組。陸遠強等[10]對相似的動物模型研究后也發現:與傳統輸液相比,限制性液體復蘇對于失血性休克能更好地穩定血流動力學,從而穩定了心、肝、腎、腸等重要組織器官的灌流,改善組織缺血狀況,減少肝、腎和小腸黏膜等器官的細胞凋亡,降低未控制性失血性休克的病死率,改善預后。王晨虹等[11]將孕兔制成未控制重度失血性休克模型,隨機分為假休克組、傳統液體復蘇組、限制性液體復蘇組,分別于實驗0 min、90 min、180 min和4 h檢測和比較各組血清丙二醛(MDA)、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的含量,并在實驗4 h處死孕兔,比較各組左肺干濕質量比(DW/WW)。結果缺血再灌注后兩個治療組SOD含量持續下降,TNF-α和MDA的含量持續上升。傳統液體復蘇組SOD和肺DW/WW明顯高于限制性液體復蘇組,但低于假休克組;而傳統液體復蘇組TNF-α和MDA含量明顯低于限制性液體復蘇組,但高于假休克組。結論:早期限制性液體復蘇能減少缺血再灌注時氧自由基的產生和炎癥介質釋放,減輕肺缺血再灌注損傷,是臨床上產科未控制重度失血性休克早期救治的理想復蘇方案。
以上3位學者從各自的實驗模型共同得出:在出血未控制的情況下,早期限制性液體復蘇是救治創傷失血性休克理想復蘇方案的結論。
4 限制性液體復蘇時機
創傷失血性休克由于發生嚴重創傷失血后其有效血容量下降,組織灌注不足或短期內不積極救治。據統計,32.6%~59.5%的病人將死于失血性休克,因此液體復蘇是關鍵。失血性休克液體復蘇傳統的觀點認為,積極液體復蘇即迅速恢復血容量,及時、快速、大量輸入液體,盡可能將血壓恢復到正常水平,以保證臟器和組織的灌注。但大量液體復蘇在創傷性休克的搶救過程中容易造成液體超負荷,液體積聚在組織間隙,出現面部、四肢、軀干、內臟器官水腫。杜曉冬等[1]研究發現,在損傷嚴重度評分(IS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的病人中,隨著補液量的增加,病人的器官功能衰竭率及病死率上升。朱義用等[12]研究報告,限制性液體復蘇能防止大量液體復蘇產生液體超負荷。
限制性液體復蘇的新概念是近年來經過大量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提出的。在活動性出血控制前快速大量輸液會增加出血量,使并發癥發生率和病死率增加,應限制液體復蘇。其機制為:①提升血壓可加重出血;②大量補液稀釋了凝血因子;③液體復蘇使脈壓增加,也可機械破壞已形成的血凝塊[13]。鄭偉華等[14]通過研究兩種液體復蘇效果得出:搶救創傷性失血性休克限制性液體復蘇優于積極液體復蘇。沈建慶等[15]研究,休克早期在出血未控制的情況下,限制性液體復蘇能避免早期大量液體復蘇的有害作用,避免過分擾亂機體的代償機制和內環境,改善臟器灌注和氧供,顯著降低了創傷性失血性休克病人的早期和后期病死率,改善預后。
5 限制性液體復蘇適當的液體種類
目前,臨床上常用與復蘇的液體主要有晶體液和膠體液兩大類,晶體液包括生理鹽水、林格液、乳酸林格液及高滲鹽液等;膠體液主要有右旋糖酐、明膠、羥乙基淀粉、白蛋白和血液制品等。復蘇治療時選擇晶體還是膠體之爭已持續30多年,但基本觀點沒有改變,主張晶體液復蘇的理由是費用低,能糾正脫水和低鈉血癥,擴充細胞外液的數量,有良好的腎功能保護作用,一般無不良作用;反對理由是晶體液擴容效果差,半衰期短,需大量輸液,可能引起血中白蛋白、凝血因子、血小板等有效成分過度稀釋,增加肺水腫、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率。贊成膠體液的理由是膠體在血管內擴容能力強、停留時間長;反對理由是膠體液可降低腎小球濾過率,抑制凝血和免疫功能,有一定的變態反應發生率。因此,目前主張合理應用,并根據病情調整比例。
5.1 7.5%氯化鈉溶液 7.5%氯化鈉溶液可產生相當于正常血漿滲透壓8倍的壓力,輸入血管后產生的滲透壓梯度使組織間液、細胞內液迅速向血管內轉移,導致血容量擴張,有效循環血量迅速增加;高滲狀態還可使腫脹的血管內皮細胞收縮,毛細血管內徑恢復正常,疏通微循環減輕心臟的前后負荷,改善組織灌流,是逆轉失血性休克的關鍵環節。張吉新等[6]研究證實,限制性液體復蘇治療,特別是應用7.5%氯化鈉能減少未控制出血的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MODS和ARDS的發生率,提高其治愈率。趙中江等[16]也通過臨床證實了小劑量高滲鹽水復蘇可以減輕未控制創傷失血性休克的并發癥及病死率,值得臨床推廣。彭祝君等[17]研究指出,早期應用高滲鹽水能降低重度顱腦損傷并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的病死率,改善預后。
5.2 高滲氯化鈉羥乙基淀粉40注射液(高滲鹽復合液HSH)
高滲氯化鈉羥乙基淀粉40注射液是經過反復實驗篩選形成的氯化鈉與羥乙基淀粉40重新組合的一種新型抗術中失血性休克的藥物。其作用機制是利用高滲脫水等原理使休克的病理生理狀態得到改善。張會英等[18]通過對術中失血性休克病人進行高滲氯化鈉羥乙基淀粉40注射液靜脈給藥治療,觀察其肝功能、腎功能、凝血功能、電解質及血常規的變化,結果顯示在治療期間未見實驗室指標有明顯異常的改變;朱紅軍等[19]通過實驗研究也證明,高滲氯化鈉羥乙基淀粉40注射液對于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是安全、有效、可靠的,能改善病人的休克狀態,贏得搶救時間,繼而配合使用其他治療,能提高休克病人的搶救成功率。肖接承等[20]通過動物實驗證實了高滲鹽復合液是目前用于嚴重胸部創傷抗休克治療效果較好的復蘇液,而且對肺組織炎癥反應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5.3 羥乙基淀粉(HES)羥乙基淀粉是一類由支鏈淀粉衍生出的高相對分子質量復合物,屬于大分子質量膠體液,與晶體液相比,它在血管內存留時間相對較長,能產生較高的膠體滲透壓,吸引血管外液體進入血管內,有效維持循環容量。李濤等[21]通過不同分子質量的HES對失血性休克的模型大鼠的作用,觀察其對M AP、血流動力學和血氣指標的影響,同時觀察存活時間和24 h存活率,并以萬汶和賀斯作為對照,結果顯示,不同相對分子質量的HES均具有明顯抗失血性休克作用,其中以HES 200效果更明顯。
5.4 參麥注射液 參麥注射液于1992年被列為首批全國中醫院急診科必備的中成藥,能升高血壓、改善心肌代謝、增加心肌能量貯備、提高機體耐缺氧能力以及加強心肌的收縮力。申五一等[22]通過臨床實驗驗證了在液體復蘇過程中加用參麥注射液能有效提高休克病人的液體復蘇效果,提高血氧飽和度,有利于創傷性休克的復蘇,是一種安全有效的輔助治療藥物,可以從多個環節改善和逆轉創傷性休克的進展,尤其適合休克早期限制性液體復蘇。
6 限制性液體復蘇效果的判斷
傳統的評價方法以血壓、心率、中心靜脈壓(CVP)、心排血量、尿量作為灌注充分的參數和復蘇終點。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趨向于采用新的評價方法,但 CVP、血壓、心率、尿量仍是判斷血容量狀態的重要參數,尤其是動態觀察其變化趨勢時指導意義更大。何娟明[23]在CVP監測下進行加壓快速輸液搶救失血性休克的療效觀察,監測病人 CVP、收縮壓、舒張壓、心率、血氧飽和度、末梢循環、頸外靜脈充盈、尿量等情況。黃強等[24]監測CVP、動脈血氣、血細胞比積、凝血酶原時間等以指導休克復蘇治療,獲得滿意復蘇效果。劉松橋等[25]進行的失血性休克犬容量狀態評價的實驗性研究表明,胸腔內血容量指數(ITBVI)能反映容量復蘇后前負荷的變化,是反映容量狀態的良好指標,可能有助于液體管理。莫蓓容等[26]對危重病人進行無創血流動力學監測,根據監測值指導和實施液體復蘇,為創傷失血性休克進行早期限制性液體復蘇提供直觀、連續、可靠的指導依據。
而目前隨著分子生物學研究的逐漸深入,血乳酸(BL)、內皮素(ET)、剩余堿(BE)、TNF-α成為判斷限制性液體復蘇效果的重要指標。BL正常值為1 mmol/L~2 mmol/L,能直接反映無氧代謝,其水平提高提示氧債的增加,是反映組織缺氧一個較敏感、可靠的指標,并有評估病人預后的作用。ET是目前已知最強的縮血管物質,在失血性休克的病理演化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崔恒熙等[27]應用BL和ET觀察復蘇效果后認為動態觀察兩者的變化關系能夠很好判斷復蘇的效果及預后。方國美[28]在評估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進行早期限制性液體復蘇時觀察BL、BE時得出,BE是一個反映組織低灌流程度和持續時間的敏感指標,其正常值為+3 mmol/L~-3 mmol/L。堿缺失的測定可評價休克的嚴重性與復蘇的完全性。
TNF-α是機體應激后產生最早并起到核心作用的炎癥介質,對MODS的發生和發展起重要作用。霍正祿等[29]的實驗研究證實,TNF-α濃度的升高與預后密切相關,是評價液體復蘇效果的指標之一。
7 小結
創傷失血性休克的液體復蘇療法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需要正確判斷及全面分析。大量的實驗醫學和臨床醫學均證實了限制性液體復蘇在創傷失血性休克搶救中的價值,該方法既對血壓進行了干預,保證了組織器官有效的血流灌注,又可避免血液過度稀釋所致的并發癥,從而提高生存率。在創傷失血性休克的救治中,何種情況下需要行限制性液體復蘇以及持續多長時間一直是很多學者關注的問題,但目前尚未制訂統一的液體復蘇指南,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和臨床經驗的積累,液體復蘇治療一定會更加完善。
[1]杜曉冬,余海放,王玲.ISS、補液量、BE對創傷失血性休克病人的影響[J].現代預防醫學,2005,32(7):837-838.
[2]王欽存,肖南,習有芳,等.限制性液體復蘇對出血未控制性休克后續救治的影響[J].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04,24(6):354-356.
[3]黃明靜,創傷性休克患者的院前急救護理[J].護士進修雜志,2007,22(13):1243-1244.
[4]韋世奎,何英,黃瑜琴,等.限制性液體復蘇治療失血性休克 56例臨床分析[J].右江民族醫學院學報,2008,30(1):71-72.
[5]林小玲.嚴重創傷的急救護理進展[J].全科護理,2009,7(10A):2602-2603.
[6]張吉新,李士華,畢寶林,等.創傷失血性休克的液體復蘇[J].創傷外科雜志,2008,10(3):200-202.
[7]楊祖清,楊敬寧,杜娟,等.限制性液體復蘇治療失血性休克的應用研究[J].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06,15(11):1032-1034.
[8]黃善灶.限制性液體復蘇治療嚴重多發傷失血性休克臨床分析[J].中國急救復蘇與災害醫學雜志,2008,6(3):379-380.
[9]張愛華,陶紅,徐燕,等.創傷非控制失血性休克大鼠限制性液體復蘇的實驗研究[J].中華護理雜志,2008,43(8):763-765.
[10]陸遠強,蔡秀軍,顧琳慧,等.不同液體復蘇方式對失血性休克大鼠各器官細胞凋亡的影響[J].中華醫學雜志,2005,85(18):1252-1256.
[11]王晨虹,涂新枝,張銓富,等.限制性液體復蘇對失血性休克孕兔肺缺血再灌注損傷的保護作用[J].醫學研究雜志,2008,37(3):42-45.
[12]朱義用,景炳文,盧峰.創傷性休克的液體超負荷分析[J].中國急救醫學,2006,26(10):647-649.
[13]沈洪.創傷早期液體復蘇的利弊[J].中華急診醫學雜志,2002,11(2):136-137.
[14]鄭偉華,汪新良,徐華,等.限制性液體復蘇救治與積極液體復蘇救治創傷性失血性休克的效果比較[J].中國急救復蘇與災害醫學雜志,2007,2(9):533-535.
[15]沈建慶,丁焱,周立剛.失血性休克限制性液體復蘇的療效評價[J].中國醫師進修雜志,2006,29(4):29-30.
[16]趙中江,鄧哲,邱晏,等.高滲鹽水復蘇創傷性未控制失血性休克的療效評價[J].廣東醫學,2008,29(1):140-141.
[17]彭祝君,羅云海,黃時雨.高滲鹽水治療重度顱腦損傷并創傷失血性休克的臨床研究[J].湘南學院學報(醫學版),2007,9(3):41-42.
[18]張會英,劉杰,葛艷玲,等.高滲氯化鈉羥乙基淀粉40注射液在抗術中失血性休克的臨床實驗指標觀察[J].醫學研究雜志,2007,36(8):71-72.
[19]朱紅軍,李文燕,劉洋.霍姆注射液對失血性休克復蘇效果的實驗研究[J].中國誤診學雜志,2008,8(29):7063-7065.
[20]肖接承,華菲,沈振亞,等.高滲鹽羥乙基淀粉液早期復蘇兔肺挫傷合并失血性休克對肺組織局部炎癥反應的影響[J].蘇州大學學報(醫學版),2008,28(3):383-385.
[21]李濤,方玉強,劉良明,等.羥乙基淀粉對失血性休克大鼠復蘇效果的影響[J].第三軍醫大學學報,2008,30(14):1319-1321.
[22]申五一,王蘭娣,劉紅軍.參麥注射液用于創傷性休克早期液體復蘇臨床研究[J].中國中醫急癥,2007,16(10):1211-1213.
[23]何娟明.加壓快速輸液搶救失血性休克的療效觀察[J].實用醫技雜志,2006,13(15):2697-2698.
[24]黃強,陳自力,李修江.早期使用限制性液體復蘇治療重度骨盆骨折并創傷失血性休克的療效評價[J].中華創傷雜志,2008,24(4):271-273.
[25]劉松橋,邱海波,楊毅,等.胸腔內血容量指數對失血性休克犬容量狀態評價的意義[J].外科理論與實踐,2006,11(1):24-27.
[26]莫蓓容,劉海丘,韓雪飛,等.無創血流動力學監測在危重患者液體復蘇中的應用[J].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06,22(7A):1-3.
[27]崔恒熙,曹葦.低壓復蘇治療未控制出血性休克的作用[J].江蘇大學學報(醫學版),2007,17(2):152-154.
[28]方國美.創傷失血性休克患者限制性液體復蘇的探討[J].護士進修雜志,2007,22(13):1200-1201.
[29]霍正祿,鄭荔峰,王美堂,等.未控制出血性休克與 TNF-α的關聯性及不同液體復蘇的作用[J].中國急救醫學,2006,26(3):18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