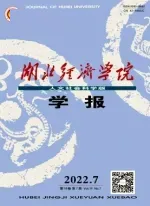革命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組織動機考察
李小紅,周麗玲
(1.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歷史與社會文化系,貴州 都勻558000;2.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馬列部,貴州 都勻558000)
革命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組織動機考察
李小紅1,周麗玲2
(1.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歷史與社會文化系,貴州 都勻558000;2.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馬列部,貴州 都勻558000)
處于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農業生產互助運動,其發動者的動機是擴大再生產,參與者的動機也是擴大再生產。二者的動機達到有機統一,這是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更是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最佳體現。
互助;組織動機;考察
中國共產黨在嚴酷的革命斗爭形勢下,對根據地民間傳統農業生產互助進行必要的揚棄,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農業生產互助運動。關于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的組織動機,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對其進行簡單考察,均未對其進行過系統性考察。本文嘗試對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的組織動機進行系統性考察,因筆者學識有限,不足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一
革命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是在中共領導下組織的,發動者是中共,參與者是農民,所以組織動機可從中共和農民兩個方面進行考察。首先來看發動者的組織動機。
革命根據地政權雖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但依然置身于小農經濟下,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狀況并沒有改變。在經過土改的地區,雖然土地的占有趨于合理,但土地的使用卻更趨于分散。由于土改力求達到“平均地權”的目的,在實踐中僅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多余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貧雇農,而中農原有的土地未動。同時,土地的分配又遵循“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這種力圖公平的方式致使土改后土地使用狀況更趨支離破碎,不利于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在未經土改的地區,雖然經過減租減息及反奸清算運動,土地占有狀況有所改變,但是仍舊不合理,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抑制。再加上頻仍戰爭的摧殘,生產資源變得更加分散和匱乏,直接導致了根據地農業生產在初中期的下降趨勢。此趨勢表現最為顯著的就是土地產量的下降。例如,1929~1931年,中央蘇區的才溪鄉,“生產低落約20%”[1]P332。1940年,晉綏邊區的晉西北區,“土地產量降低1/3以上,棉花總產量只及戰前3%”。同年,晉冀魯豫邊區,“糧食產量平均降低1/4到1/3”[2]P338。另據1942年晉西北興縣八個自然村糧食產量的統計資料可知:1937年,每坰土地產量3.21斗;1939年,每坰土地產量2.04斗;1940年,每坰土地產量2.07斗;1941年,每坰土地產量2.41斗。[3]P103由此可知,1939~1941年間,各年的土地產量與1937年相比較是下降的,下降比例一般為25%~35%。土地產量的下降,將直接威脅著根據地政權最基本的生存安全。
中共在這一危機面前,出于本能的反應,不得不采取種種措施,首先必須遏制土地產量的下降趨勢,其次為了最終確保革命的成功,必須尋求一種能夠“提高勞動效率,提高生產力,使農民共同上升”[4]P63的有效途徑,最終增強根據地政權和農民的經濟實力。
當然,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條件下,中共發動互助的直接動機是擴大再生產,除此主要動機外,還附帶其他動機。比如中共欲借助互助組織整合社會資源,穩定社會秩序;有效控制農村基層,培育堅實的政治基礎;保障兵源、軍糧的充足供給,穩定軍心。由此可見,根據地互助在經濟、政治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傳統中國的土地占有狀況。在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實現了土地占有權和使用權的統一。在暫時未經土地改革的地區 (主要指抗戰期間及解放戰爭初期新解放的地區),由于減租減息政策的實行,農民已經部分獲得土地。抗戰期間,在新解放的地區,由于實行減租減息,使得農村土地占有狀況和階級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根據北岳區、太行區、晉綏區、鹽阜區、濱海區五個地區的調查資料可知,“減租后地主戶數比減租前減少1/3,土地減少40%~70%,平均減少54.25%;富農戶數下降7%,土地減少16.7%;中農戶數增加18.4%,土地增長44%;貧農戶數減少1/5,土地增加18.4%;雇農減少50%。”
[5]P15解放戰爭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區,減租減息是結合反奸清算的群眾運動展開的。通過反奸清算,有些農民收回了自己被強占的土地,有些農民分到了沒收的地主的土地,從而,部分地緩解了農民的土地問題。例如,“在東北的嫩江省,僅沒收由日寇移民組織的‘開拓團’及東北漢奸組織的‘滿拓團’的土地就達382.5152萬坰(占全省耕地總面積的44.6%)”[6]P62,全部分給了無地少地的農民。另外,農民還通過清算地主的額外加租和高利貸盤剝從農民手中奪去的財產,構成了地主對農民的一大筆負債,迫使地主以土地還債,這樣也使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總之,在革命根據地的早期建設中,通過土改或減租減息及反奸清算運動,農民已經獲得或部分獲得土地。土地一直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農民獲得夢寐以求的土地,必然大大增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樣,農民發家致富的意識開始復蘇,勞動積極性提高。馬克思主義認為,“土地所有權是個人獨立發展的基礎。”[7]P909農民獲得土地,大大解放了農民追求財富的潛能。農民心里清楚:原先整年在地里忙來忙去,干死干活弄到年底還是兩手空空,挨凍受餓,哪有心計劃怎樣種地,該鋤三遍鋤一遍,莊稼怎能長得好,現在出力是自家的,誰能不努力干?這顯然與傳統社會中農民“知足常樂”的心態不可同日而語了。
農民不但獲得了土地,而且在土地改革充分的地區,各層次的農民所擁有的土地大體相當。根據陜北賈家溝、賀家川等八個村土地分配的調查資料可知:該八村共有雇農3戶,人口5人,土地18.9坰,人均土地3.78坰;貧農125戶,土地1696.7坰,人均土地4.06坰;中農107戶,人口482人,土地2065.7坰,人均土地4.29坰;富裕中農30戶,人口158人,土地783坰,人均土地4.96坰。總計265戶,人口1063人,土地4564.3坰,人均土地4.29坰。[3]P33-35由此可知,貧農、雇農人均土地數量較全體平均數量略低,中農幾乎相等,富裕中農略高,差距很小。土地占有的相對平均化,為各個層次的農民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起跑線,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了農民發家致富的激情。
在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增強和發家致富激情得到激發的同時,根據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進生產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在根據地廢除了舊政權時期的一切苛捐雜稅和無限制的攤派勒索,僅向農民征收適量的土地稅,并且征稅程序規范化。例如,蘇區規定“土地稅之收入支出須統一于高級蘇維埃政府,低級政府不得自由收支”。[8]P289這樣就避免了舊政權稅收混亂無度的局面。征稅稅制的上述規定,使得農民免除了苛稅攤派的侵擾,對恢復并改善農業經營能力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中共新政權采取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比如在農業資金供給方面,根據地政府禁止苛刻的原有民間高利貸。在已經土改的蘇區,明確規定“蘇維埃政權之下,禁止高利借貸”。[8]P288在暫時未土改的地區,實行減息政策。在禁止民間高利貸的同時,中共新政權通過國家財政信貸的渠道,從各方面給農業生產以巨大的支援。此外,根據地政府支持鼓勵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植樹造林,增殖畜產等,發動農民對于某些農作物訂出生產計劃,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和組織勞動競賽等。”[8]P371由此可知,中共新政權對農業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巨大的。
在根據地,農民不僅在經濟上擺脫了受剝削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擺脫了受欺壓的地位。在根據地內,出身于農民的鄉村干部控制了農村政治生活的各種組織,他們成為新的鄉村精英。新的鄉村精英地位的確立和維持,來自政府部門,而非其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這使得農民尤其是經濟上不占據優勢的貧農(也包括雇農)開始居于鄉村社會的核心地位。“貧農團即使人數不占大多數,也自然成為領導核心。鄉村中的一切工作,特別是關于土地改革中的一切問題,必須先經貧農團啟發和贊成,否則就不能辦”[9]P382。正如農民自己所說的:以前是地主的天下,現在是我們的世界。這必然增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根據地雖然依舊處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個體勞動與集體勞動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已有很大緩和。具體分析來看,一是經過土地改革或減租減息,農村各階層的經濟差距縮小,加上互助組織內部交易方式制度化,使得農民怕吃虧的顧慮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二是互助勞動時,奉行大活集中,零活分散,宜合則合,宜分則分的原則,使得集體勞動和家庭勞動巧妙地協調起來。同時,交易方式在力求公平的基礎上兼顧簡便,使得農民能夠容易掌握,使得農民怕麻煩的顧慮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這樣,農民對集體勞動的抵觸情緒有了很大轉變,互助合作具備了最佳條件。
總體來看,根據地雖然生產力依舊低下,生產資源一度也更加分散和匱乏,但農民經濟上翻了身,政治上掌了權,貧困的生活命運已得以根本扭轉,更重要的是中共新政權對農業生產的極大重視,使得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愿望具備了實現的客觀條件。
面對生產技術落后,政府和農民本身的經濟力量都很有限的現實狀況,中共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走生產互助的道路。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走生產互助的道路,“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10]P932在根據地,中共維護政權生存的本能同農民發家致富的希望相結合,導致了發動者和參與者二者動機的完全一致性,就是擴大再生產。這也是根據地農業生產互助運動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更是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最佳體現。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一卷)[Z].人民出版社,1993.
[2]鄭慶平.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概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3]張聞天.神府縣興縣農村調查[M].人民出版社,1986.
[4]史敬棠.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上冊)[M].三聯書店,1957.
[5]董志凱.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6]陳吉元.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1949-1989[M].山西經濟出版社, 1993.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Z].人民出版社,1974.
[8]許毅.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上冊[M].人民出版社,1982.
[9]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篇)[Z].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10]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三卷)[Z].人民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