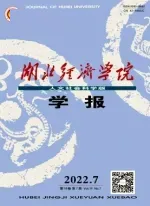論嚴復翻譯原則中的“雅”
王言
(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 外語系,廣東 從化 510900)
論嚴復翻譯原則中的“雅”
王言
(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 外語系,廣東 從化 510900)
在中國翻譯界,嚴復的“信,達,雅”翻譯理論十分流行,每一個學過中國翻譯理論的人都了解它們,對于“信”和“達”,翻譯界并無爭議,爭論的焦點是“雅”,不同的學者見解不一,筆者認為:“雅”指的是原文的風格,做到“雅”就是指保持原文的風格。本文將試圖解決以下三個問題:1.嚴復的“雅”的原始概念,不同的人怎樣去理解它?2.筆者對“雅”的態度?3.怎樣做到“雅”?在解決這三個問題的過程中,筆者將把嚴復的理論和泰特勒的翻譯原則及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奈達的“功能對等”聯系起來,然后解釋我們怎樣去理解這種聯系,如何將其運用到翻譯實踐中去。筆者認為這將是本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信達雅;功能對等;源語;譯語;筆調;文體
嚴復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學貫中西,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翻譯家,也是我國首創完整翻譯標準的先驅者。嚴復吸收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思想的精髓,并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天演論》譯例言里鮮明地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這條著名的“三字經”對后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譯者幾乎沒有不受這三個字影響的,對于“信”和“達”,翻譯界并無爭議,爭論的焦點是“雅”,不同的學者見解不一,筆者認為“雅”指的是原文的風格,做到“雅”就是指保持原文的風格,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就這一觀點展開討論。
一、嚴復“信達雅”的概述以及關于“雅”的不同理解
關于“信”和“達”,大多數學者都沒有異議。大家都一致贊同嚴復先生提出的看法——即 “信”表示譯文要忠實原文;“達”表示譯文要表達通順,符合“目標語”(Target Language)的表達習慣。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對“雅”的理解,中國翻譯界有很多學者專家都曾著書立說,闡述了他們心中“雅”的含義。下面,首先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嚴復先生關于“雅”的原始表述:
“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為譯事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而雅。”(羅瓊,1981:16)
不同人對這一段關于“雅”的文字有著自己不同的看法和見解,總的說來,這些觀點可以被籠統地分為兩個方面:即消極派和積極派。消極派認為嚴復的“雅”的學說,觀點陳舊,表述不科學。他們引用嚴復先生自己關于“雅”的一些看法作為佐證,試圖證明,嚴復本人也認為“雅”不能跟“信”和“達”并存。嚴復曾經說過:
“信達而外,求其而雅,用漢字以前句法,則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羅瓊,1981:16)
從這段表述,那些反對“雅”這一提法的人找出了自己的一些根據。他們認為,嚴復自己都承認,“雅”意味著雅致,古雅,現世的文字是無法做到“達”,“雅”并存的。在這一派觀點中,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中國現代翻譯事業的偉大踐行者——瞿秋白先生,曾經評論到:
“嚴復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王圻暖,1984:20)
盡管,關于“雅”的提法,有上述的消極看法,但是還是有很多學者是堅定的支持嚴復先生的這一理論,在他們看來,嚴復的“雅”不僅指的是譯文要雅致,古雅,確切的表述應該是:“雅”指的是譯文要保持原文的文采,風格和筆調。在“積極派”中,筆者認為張經浩先生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也最易于理解。在《論翻譯》一書中,張先生是這樣說的:
“其實嚴復關于‘雅’的用意和根據早在他的《天演論——譯例言》中就說的很清楚了,他說:‘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信達而外,求其而雅。’原來‘雅’指的是文章應該有文采,不能平淡無奇。其目的是為了爭取讀者。”(張經浩,1996:61)
在筆者看來,張經浩先生的這一關于“雅”的解釋,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對于以張先生的理論為代表的“積極派”的觀點,筆者深表贊同,下面是筆者的一些看法。
二、筆者關于嚴復“雅”的態度
在“信,達,雅”的翻譯三字經中,“信”和“達”已經深入人心,無需贅述,我們爭論的焦點在于“雅”。筆者不認為,“雅”的提法是陳舊的,不科學的。相反的,筆者認為,嚴復先生,“雅”的理論是簡潔,正確和實用的,我們應該對這一理論持有積極的態度,并且要根據實際需要,努力去實踐“雅”。以下就是筆者的一些依據:
(一)我們應該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列寧曾經說過:“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這也就意味著,任何事物都有其歷史的局限性,我們對任何事物的評價都不能脫離該事物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否則我們的判斷就會陷入不科學的境地。
關于嚴復“雅”的翻譯理論,我們同樣也要歷史地分析,不能脫離嚴復先生所生活和學習的歷史時代,更不能脫離嚴復翻譯理論在當時的環境下所面對的讀者的歷史背景。嚴復提出了“雅”,的確是強調譯文要古雅,雅致。結合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我們不難看出,他的“雅”還是有進步意義的。眾所周知,嚴復生活在清末民初,無論是他海外求學,還是學成歸國施展抱負,都沒有脫離他所處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中國的語言文字,尤其是正統的書面語言,還是奉文言文為正朔的。所以,無論是嚴復還是他的理論可能的受眾們,都還是習慣文言方式的舊式知識分子。在他們眼中,只有古韻古雅的文章,才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他才提出:“信達而外,求其而雅,用漢字以前句法……”
(二)我們應該用變化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的運動和變化發展之中。嚴復的“雅”,針對的是他所處的時代和背景,在當時無疑是極其先進的,至少他是系統地提出翻譯理論的第一人。今天,作為后人的我們所理解的“雅”,則應該是變化,發展并符合我們所處的時代。事實上,很多學者和研究者,正式這樣運動變化的去理解嚴復先生的理論的,只有這樣得到的看法才是正確的,全面的。
“后來的翻譯理論家給嚴復的雅注入了新的理解即雅指保持原文風格,原文雅,譯文則雅,反之亦然。”(馮慶華,1998:18)
上面這段引用就很能說明問題,還是用張經浩先生的看法來加強一下這個理解,在《論翻譯》一書中,張先生提到:
“嚴復的雅是指文章的色彩,即譯文不能平淡無奇,只“信”不“達”,譯了等于沒譯:只有“信達”而不雅,譯文中,原文的風格筆調便蕩然無存。所以“雅”是對“信”與“達”的必不可少的深化與補充。”(張經浩,1996:61)
由此可見,對嚴復“雅”的理論,持積極觀點的學者是這樣理解的,這樣的理解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也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最好體現。
(三)理解事物要運用普遍的聯系的觀點,切忌孤立僵化。如果把嚴復先生的理論,結合其他翻譯理論家的論述,綜合起來看,就很容易找到,嚴復理論的可取之處。早在18世紀,英國著名學者——Alexander Fraser Tytler就提出過著名的翻譯三原則,即:
1.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original work.
2.The style and manner of the writing should be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3.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c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嚴復的信達雅來自泰特勒的三原則,信來自第一原則“再現原作之意”。達來自第三原則“順通”,而雅來自第二原則“風格”,“筆調”。(林錄南,1994:739)
泰特勒是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及實踐家,而嚴復則學成于英國,所以他的思想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受到泰特勒的影響也在所難免。
而縱觀現代的國外翻譯大家,我們也可以很容易地為嚴復“雅”的理論找到相應的依據——這就是美國著名翻譯家尤金.耐達的“功能對等原則”。 (譚載喜,1999:20)
“等效原則的關鍵因素就是接受者。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的‘功能對等’,也十分注意接受者的感受,功能對等表示兩種對等:一邊是原文和原文的讀者,一邊是譯文和譯文的讀者”(金緹,1998;30)
金緹先生的見解無疑給嚴復的翻譯理論和耐達的原則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具體來講我們應該如何把二者聯系起來呢?下面讓我們仔細的看看耐達先生的“功能對等”原則,在這里我們引用嚴久生先生的一段話:
“一般來說最好用對等來討論譯文的適度范圍,因為從來就沒有完全的對等,各種不同的譯文,實際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對等。這就是說對等不能理解為數學意義的對等,只是近似的對等,這種對等觀總是包含著已知和經驗的因素,分為最高和最低的對等,最高效應是讀譯文者應該基本按照原文讀者理解和領會原文的方式來理解和領會譯文。最低效應則是譯文讀者對譯文的理解應該能夠達到或想象的出原文讀者是怎樣理解和領會原文的。”(嚴久生,2001:18)
在這里,耐達提到了“等效原則”的最低標準和最高標準。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Minimal standard”or the“Maximal standard”(Nida,2001:8),我們的核心都應該是讀者,我們應該關注譯文是否給“目標語”讀者帶來了“源語言”,給它的讀者那樣的感受或者是近似的感受。
嚴復的“雅”同樣也是關注讀者感受的,這一點上文諸多學者在論述“雅”的含義時,都已說得很明白了。由此不難看出,嚴復的“雅”所要求的譯文保持原文的文風、筆調,完全可以用耐達的“功能對等”來解釋。
三、如何實踐“雅”的理論
一種理論,如果僅僅停留在口頭而不付諸實踐,無疑會喪失其長久的生命力。我們已經能夠為“雅”的原則,找到很好的理論依據,接下來就是應該如何去實現它。在這一點上,劉宓慶先生做了很深的研究:
“對翻譯來說,為了把握和體現原文的風格特別是反映出原作家的寫風格,我們應該:第一,注重學習,著手在翻譯以前對作家的生平,創作道路,方法以及作品的時代背景有一個深刻了解;第二,注重分析,分析作家在這個作品中如何使用語言體現他的個人風格;第三,注重調整,真正做到文隨其體,話隨其人。”(劉宓慶,1998:589)
所以要真正的實現“雅”,廣大譯者,一定要學會分析,分析原文,把握原文的題材和體裁以及作者的個人風格。時刻提醒自己我們的翻譯要做到“文隨其體,話隨其人”。
最后借用艾默生的一句名言來結束我們的探討:“The years teach much which the days never know.”——Emerson says(Pu Rao,2001:6),翻譯理論是一門科學,如果想有更高的造詣,我們只能是一步一個腳印,讀更多的書,做更多的事。
[1]Nida,E.Language and Culture[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Pu,Rao.The Quotations[M].Chengdu: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01.
[3]Steiner,G.After Babel[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Tytler,A.1790.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A].In Yuping Shen(ed.),2002.Selection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C].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5]Wilss,W.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6]曹憲國.漢英詞典[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1.
[7]馮慶華.實用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8]金緹.論等效翻譯[M].北京: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9]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M].北京: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10]林錄南.中國當代翻譯百論[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4.
[11]羅瓊.翻譯研究論文集[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社,1981.
[12]譚載喜.語言文化與翻譯[M].北京: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13]王圻暖.翻譯論文集[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4.
[14]嚴久生.語言文化和翻譯[M].北京: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15]張經浩.譯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