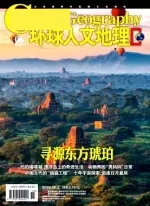探訪桑株古道穿越喀喇昆侖山的抗戰運輸線
幾年前,通過一本叫做《未完成的探險》的小冊子,我認識了德國探險家特林克勒和穿行于昆侖山和喀喇昆侖山中的桑株古道。1927年8月3日,特林克勒的探險隊從克什米爾的列城出發,經過兩個月,穿越了世界屋脊喀喇昆侖山,走過了廣袤、坎坷的無人區,當他們精疲力竭地翻過最后一座達坂——桑株達坂后,終于進入了塔里木綠洲,回到了紅塵。
特林克勒對喀喇昆侖之路的描述深深地吸引著我。幾年來,我多次考察昆侖山之路,進入喀喇昆侖山區,沿著特林克勒的足跡考察……2009年7月,我率探險隊再次進入桑株古道,經過4天的攀登,當我們站在海拔5050米的桑株達坂,眺望一望無際的高山雪嶺,我再次體會到特林克勒對喀喇昆侖之路描述的含義,也真正理解了為什么古往今來人們會不辭辛苦地往返于如此艱險的旅途,更懷想它在抗戰時期如何成為向中國輸送緊缺物資的國際運輸線。
杏子成熟的康克爾鄉
進入塔里木綠洲的第一村
桑株古道也稱為“喀喇昆侖之路”,它位于亞洲的心臟,起于新疆南部的皮山縣桑株鄉,穿越世界最高的山脈,到達克什米爾的列城,是連接中亞和南亞的橋梁。在西方探險家進入的時候,昆侖山地區人煙稀少,離皮山縣30多公里的桑株鄉所轄的地域,還是塔里木邊緣的小綠洲……一個世紀過去了,桑株鄉已成了擁有5000多人的大鄉村,隨著人數的增長,綠洲又向昆侖山淺山地帶擴展,十幾年前,皮山縣政府又在桑株鄉以南20公里的山區建立了康克爾柯爾克孜民族鄉,這里也就成了從克什米爾沿桑株古道進入塔里木綠洲的第一村。
7月23日,為了能順利進入康克爾鄉,我們3個領隊一大早就驅車行駛240公里來到了皮山縣,下午前往康克爾鄉打前站。8月24日,兩位維吾爾朋友駕車把我們9名隊員送到了康克爾鄉。同時,我們還聯系到了柯爾克孜馱工依明和托乎提木薩——他們在我們前一年進入桑株古道時幫助過我們。
康克爾鄉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于畜牧業和種植杏樹。這里雖然地處山區,土地貧瘠,但自古以來出產的杏子以個大、肉厚、香甜而出名。我們到達時正是杏子成熟的季節,房前屋后,山坡谷底,隨處可見碩果累累的杏樹,在村舍東側的河床上,豐收的人們忙碌著,在炊煙裊裊升起的河谷中,在夕陽的映輝下,成片金黃色的杏樹和銀色的桑株河呈現出一派祥和的景象。康克爾鄉是昆侖山腳下的世外桃源,不僅景色優美,鄉民也淳樸好客,晚上我們住在了馱工托乎提木薩家,他的妻子為我們做了一頓香噴噴的柯爾克孜抓飯,他6歲的小女兒穿著我們帶去的連衣裙,可愛極了,蹦蹦跳跳地進出果園,給我們端來了一盤盤透紅的杏子。
桑株峽谷的古棧道上
毛驢后腿踏空,幾乎失足墜入河中
離開村子時,出于好奇或興奮,4個女隊員一上路就分別騎上毛驢狂奔,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村子的最南邊,若不是為了看桑株巖畫她們還不肯下驢。桑株巖畫刻在一處不高的花崗巖山體下面,其面積雖說只有1~2平方米,但卻是昆侖山區的著名巖畫,涉及放牧、狩獵、星辰,是生活在昆侖山區的先民們的生活寫照,據考證至少也有兩三千年的歷史,不過直到1927年德國探險家特林克勒路過此地時,才將桑株巖畫公布于世。
正午時分,烈日照射在昆侖大地上,極其干燥的河谷沒有一絲微風,空氣似乎都凝固了。激動和興奮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悶的腳步聲和淋漓的汗水。在離河道幾十米高的峭壁上,一條蜿蜒曲折的小道依稀可辨,這便是穿越河谷的人工棧道。這條棧道起于何時,是誰開鑿的,我們無人知曉,在史書上也找不到任何記載,但從棧道上巖石磨礪的程度來看,這條棧道至少已存在上千年了,不論是對于遠古的先民,還是早年的商旅,棧道都是他們賴以生存和走向西藏和南亞的必經之路。
千百年的風雨侵蝕,讓棧道已破碎不堪,許多塌方斷裂的路段用紅柳和石塊修復起來,人走在上面有種搖搖欲墜的感覺,在有些我看來毛驢根本無法通過路段,為了保險起見,我從毛驢身上取下了裝有團隊經費、照相機和攝像機的背包,以防老驢失足,墜入下面洶涌的桑株河。當隊員們相互保護著通過了第一段棧道之后,我們目睹了毛驢過棧道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馱著沉重行李的毛驢根本無法靠自身力量爬上陡峭的棧道,往往是4個馱工一起又牽又推,加上棍棒使勁的敲打,強行讓驢通過。站在不遠處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驢顫抖的四肢,驢蹄的鐵掌與巖石劇烈的碰撞發出的響聲,緊緊揪住我們的心。一頭馱著3個大包的毛驢終于堅持不住了,臥在了狹窄陡峭的棧道上,一條前腿卡在石縫中,馱工用木棍使勁敲打毛驢的脖子,拼命掙扎的毛驢的后腿突然踏空,差點掉下懸崖,我們禁不住大叫起來。
我真佩服昆侖山區的毛驢,它們具有極強的耐力、適應高海拔的能力和生存本領。那頭陷入絕境的毛驢,最終在馱工的努力幫助下脫離險境,但它的后腿關節處被巖石劃開一道近10厘米長的口子,鮮血直流,我們趕緊用繃帶給它包扎。
走向曲谷達克高山牧場
蔥綠的草坪中,簇擁著馬蓮草
此行中,需要途經曲谷達克——桑株達坂以南的高山牧場,平均海拔4200米,是古往今來人們翻越達坂前最后的落腳地。前進的難度在于,海拔會迅速地上升到4000多米,不僅要通過更險要的棧道,還要頻繁地在河水中穿行。為了能盡快地適應高海拔地帶,出發前我就叮嚀每個隊員:照顧好自己就是對團隊的最大貢獻,只要能走就不要騎毛驢。
出發不久,便進入了一條狹窄的河谷。但讓人費解的是,河岸上有一堵厚約兩米,長約80米的卵石壘砌的墻,它依山勢而建,橫斷河谷,殘缺不全,可以猜測出這道墻至少經受了近一個世紀的風雨;從工程量和用途上來看,它也絕非當地游牧民族所建,但它究竟建于何時,有何用途,都是不解之謎。
中午時分,當我們登上一個山崗,視野豁然開闊,一個由綠樹簇擁的院落坐落在河谷中央,這便是特林格勒提到過的庫爾梁—— 一個古老的牧場,有幾戶柯爾克孜人家常駐,每到夏季,馱工依明80多歲的岳父就會到這里放羊。前方的道路被河流阻斷,我們只得渡河,但上漲的河水已經淹沒到了毛驢的肚皮,但毛驢很快渡過了河,直奔庫爾梁,而我們可沒那么幸運,不是涉水鞋被沖走,就是被沖倒在河中,或者小腿被激流中的暗石撞傷。當我們渡過河,沿著河道向庫爾梁行進,看到了一伙從桑株達坂過來的柯爾克孜牧羊人,他們身背行囊,穿著露著腳趾的解放鞋,在沒有棧道的峭壁上攀爬跳躍,矯健的身手讓我們這些戶外老驢望塵莫及。
一整天的攀爬和涉水,讓隊員們體力消耗很大,直到傍晚才到達地圖上標有蘇干特阿合側的地方。這里海拔3000米,有一塊昆侖山中不多見的綠地,蔥綠的草坪中,簇擁著茂密的馬蓮草,清澈的山泉匯成涓涓流淌的小溪在草坪中穿行。累了一天的我們,展開四肢躺在草坪上,享受著大自然的恩賜。但由于營地建在河邊,夜里震耳欲聾的水聲使人難以入睡。
從蘇干特阿合側南行不久,河谷漸漸開闊,遠處巍峨的雪山像巨大的城墻把河谷隔斷,河谷的盡頭跌宕起伏的山丘便是曲谷達克,一道道冰川順山谷而下,與山丘相壤。在接近山丘時,河谷開始向東南方向延伸,河水漸漸小了下來,在河谷轉彎處有一個向西延伸的山谷,十幾根一米多高的天然石柱呈“一”字形,靜靜地聳立在谷口,上端都放有獸皮和石塊,但象征著什么無從查考。我和隊友老馬相信這是千百年來往返于古道的人們的一種祭祀,于是我倆也走向石柱,虔誠地放上了一小塊石頭。歲月斑駁,一根根聳立的石柱,一塊塊壘起的石頭,似乎在向我們訴說著古道的滄桑。
曲谷達克四面環山,每到夏季,雪山的融水便把貧瘠的山丘滋潤出一層綠色,成群的牦牛在山坡上悠閑地游蕩。當我們沿著牧道攀登到海拔4100米的一處高崗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藍天、白云、雪山、草地交織成的美麗畫卷。我們都放松下來,躺在山坡上享受著微風和陽光的沐浴。但為了能在一天內翻過桑株達坂,我們還是起身繼續前行,一直到天黑才扎營。
高山缺氧中翻越桑株達坂
抗戰時期印度到新疆的國際運輸線
第二天,海拔越來越高,漸漸看不見原本稀疏的牧草,隊伍艱難地在布滿礫石的山坡上攀爬,稀薄的空氣讓人透不過氣來。轉過一個山梁后,一條向西延伸的小道通向高高的山梁,山梁后面一座大山拔地而起,橫亙在我們面前,所謂的桑株達坂就是大山之巔。當我到達海拔4300米的一個山梁下時,隊伍已經拉開了很長距離:走在前面的人已經翻過了山梁,走在后面的人還不見蹤影。夕陽已被達扳遮住,遠去的驢隊像一個個小黑點在“之”字形的小道向上蠕動。
隊友老張雖說有過7500米的登山記錄,但還是有高山反應,還沒等帳篷完全搭好,便一頭倒在帳篷里睡了過去。當一名女隊友搖搖晃晃登上山梁時,天已經黑了,她渾身發抖,嘔吐不止,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來。對于第一次參加戶外活動,沒有任何心理和體能準備的她來說,一天上升1500多米已經很不容易了。
清晨,一條清晰的 “之”字形牧道直通初升的太陽照亮的山頂。1951年,為從新疆進入西藏,新疆軍區在桑株達坂附近打通了這條馱道。直到1957年10月6日新藏公路開通前,它一直是進藏部隊的供給線。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馱道大部分路段被崩塌的礫石掩埋,別說駱駝,就連毛驢也難以通過。
我們沿著陡峭的牧道向上攀登,高山缺氧,兩條腿就像灌了鉛似的,每走幾十步就要停下來大口地喘氣。3個小時后,當我們站在海拔5030米的達坂上時,心曠神怡地眺望鱗次櫛比的雪山,回首俯視1500多米下的曲谷達克牧場,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此時,一切煩惱似乎都不復存在,還有一些興奮的隊友在大家都伴唱下,在懸崖邊上翩翩起舞。
上山容易下山難。雖說是夏季,但達坂的南坡冰雪還沒有完全消融,因此馱道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冰道。幾天的行走讓驢蹄上的鐵釘早已磨平,毛驢走在馱道上如同穿著冰刀下山。在許多路段,往往是4個馱工“護送”一頭毛驢。我們相互攙扶著踩著毛驢踏出的痕跡向下挪動,時而會看到殘留在路邊礫石上的堆堆白骨。據考證,這條路也是公元7-10世紀西藏通往新疆的古道。在近現代,這條古道在軍事上也發揮過重要作用。據《1943馱工日記》記載,1942—1945年,國民政府沿著這條古道開辟了一條從印度到新疆的國際運輸線,使用馱馬1500余頭,先后參加馱工達1300余人。在徒步翻越喜馬拉雅—喀喇昆侖山脈的1059公里古道中,人畜傷亡率達10%左右,共運進6600條汽車輪胎及抗戰時期其他緊缺物資。
昆侖山深處神秘的洞穴
發現60公斤重的上等墨玉
7月29日,考察隊進入了喀拉喀什河谷,在地圖上標有蒙古包的地方,有一座干打壘的院落,從周圍粗大的柳樹可以看出,100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院落西邊高聳的山壁上有許多洞穴,洞口有人工壘砌的門欄,洞穴之間有通道相連,也有的洞穴開鑿在垂直的山體上,使人難以進入。這些洞穴是昆侖山深處穴居人的“家”,特林克勒路過此地時也有過描述,但洞穴開鑿于何時,穴居人究竟是什么人卻無從考證。
喀拉喀什河是新疆和田兩大河流之一,發源于喀喇昆侖山,在下游與玉龍喀什河(白玉河)匯合形成和田河,最終流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離開蒙古包不久,我們又踏上了棧道,可是沒走多遠突然發現棧道塌陷,只得返回到蒙古包,從那座有洞穴的山上翻過去,這一往返最少也耗費了3~4個小時。攀登這座高50米,坡度超過70度的懸崖,是此次行程中最危險的路段,一旦失足就會墜入洶涌的喀拉喀什河中。
翻過懸崖后,我們沿著河谷而行。喀拉喀什河在維吾爾語中意為“墨玉河”,以盛產墨玉而出名,當我們在河道上休息時,還果真發現了一塊60公斤重的上等墨玉。黃昏時我們到了達佩里塔含西,得知再有20公里就到賽圖拉時,我們徹底放松了。
賽圖拉是219國道路經之地,自古以來在軍事和通商上都有著重要的作用,早在一個半世紀前,清朝政府就在賽圖拉設防,在219國道上還能看到高山頂上聳立的哨所,哨所的下方便是軍營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