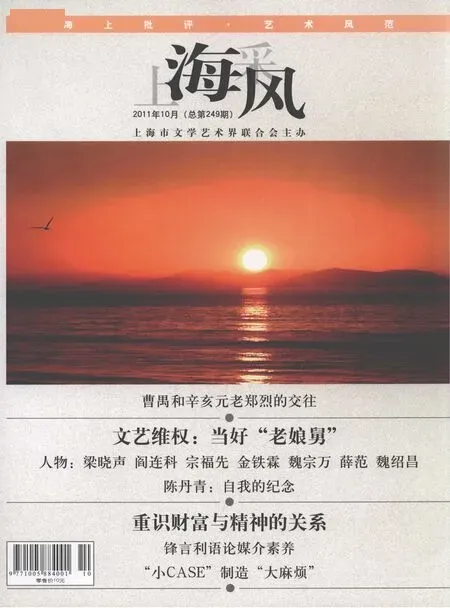曹禺和辛亥元老鄭烈的交往
文/曹樹鈞


曹禺清華畢業(yè)照(1933年)
鄭烈,字曉云,早期同盟會(huì)的會(huì)員,辛亥革命的元老,我國杰出戲劇家曹禺第一位夫人鄭秀的父親。曹禺與鄭烈的交往在他早年生活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記。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交往,曹禺在很長一段時(shí)間里諱莫如深。今年欣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jì)念,這段塵封已久的史實(shí),理應(yīng)還它的本來面目,這既是對(duì)辛亥革命的紀(jì)念,也是對(duì)曹禺這位我國現(xiàn)當(dāng)代戲劇史上首屈一指的杰出劇作家生平研究的一個(gè)應(yīng)有的補(bǔ)充和還原。它還需從曹禺和鄭烈女兒鄭秀的初戀談起。
清華園演話劇月下定情
青春是美好的,青春期的初戀更洋溢著誘人的芬芳。1933年,一個(gè)女大學(xué)生闖進(jìn)了曹禺的生活。她叫鄭秀,也在清華大學(xué)讀書,是法律系的學(xué)生;曹禺當(dāng)時(shí)在西洋文學(xué)系學(xué)習(xí),與后來蜚聲文壇的錢鐘書是同班同學(xué)。
曹禺與鄭秀第一次見面在193l年,曹禺在清華大禮堂演《娜拉》的時(shí)候。那時(shí)鄭秀還在北京貝滿中學(xué)念高中。
演出結(jié)束后,鄭秀聽清華同學(xué)成己介紹剛才演娜拉的就是曹禺,大吃一驚。面前站著的是一個(gè)矮個(gè)子男青年,圓圓的臉,戴一副近視眼鏡,穿一件布長衫,貌不驚人,簡直想像不出剛才臺(tái)上活蹦亂跳的娜拉就是他。
曹禺也凝神注視著這位陌生姑娘,趁成己介紹的時(shí)候,仔細(xì)地打量了一下她:高高的鼻梁,紅潤的臉龐;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發(fā)出動(dòng)人的光彩;身材苗條,面容清秀,一副大家閨秀的儀表。不知為什么,曹禺第一面便對(duì)她有一種親近感。
第二年秋,鄭秀考進(jìn)清華法律系,曹禺聞?dòng)嵃底愿吲d,但苦于沒有接近的機(jī)會(huì)。
1933年春,清華話劇社排演英國話劇《罪》。高爾斯華綏著,三場(chǎng)話劇,又名《最前的與最后的》。此劇由曹禺翻譯、導(dǎo)演,男主人公拉里由他主演,拉里的女友汪達(dá),曹禺特邀鄭秀擔(dān)任,借機(jī)可以接近鄭秀。
排練在二院九十一號(hào)曹禺的宿舍里進(jìn)行。前后排了一個(gè)月。每次排完之后,曹禺都送鄭秀回新南院宿舍。在一個(gè)月的接觸中。鄭秀感到曹禺這個(gè)人聰明、有才華,對(duì)自己有一種灼熱的、特殊的熱情。
但又覺得他個(gè)子太矮,自己穿著高跟皮鞋比他還高一點(diǎn),不是理想的朋友。她想找一個(gè)學(xué)理工科的,人再漂亮一點(diǎn),更有魅力些。
曹禺知道鄭秀每晚都在校圖書館自修。他每次到圖書館閱覽室,總看見她專心致志地在用功。一天晚上,快八點(diǎn)的光景,曹禺拿著一張劇照,約鄭秀出去走一走。鄭秀正在專心看書,便說:“有什么事?待會(huì)兒吧!”
曹禺說:“好吧,我回頭再來接你。”
到九點(diǎn)半,圖書館快要關(guān)門了,曹禺又來了。他將一張他扮演《娜拉》的劇照送給鄭秀,并說:“我們沿著新南院后面的河邊走走,好嗎?”
鄭秀心里想,他盛情邀請(qǐng)我,就當(dāng)是我的老大哥,跟他一塊走走吧。于是,就大大方方地同曹禺一起出外散步。
曹禺一邊走,一邊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的愛好,談起他的父親、母親。鄭秀很奇怪,家寶(曹禺本名萬家寶)平時(shí)沉默寡言,排戲時(shí)話也不多,今天不知哪兒來的那么多的話。她只是聽,不大搭腔,而且走得很快。曹禺老覺得跟不上她。
又一天晚上,曹禺約鄭秀出來散步。他戴著一副寬邊的玳瑁眼鏡,左臂夾著一大疊書。他拿出一張照片給鄭秀:“這是我母親的相片,送給你做個(gè)紀(jì)念吧。”接著又說:“鄭秀,我有句話想告訴你。”
可是停頓了好一會(huì),他又不吭聲了,只是一個(gè)勁地朝前走。走著走著,忽然左臂夾著的一疊書散落在地上。曹禺忙蹲下去撿書。慌亂中,一副眼鏡又掉了下來。鄭秀見他的窘狀,禁不住咯咯笑了起來,忙幫他將眼鏡撿起來。這時(shí),她忽然發(fā)現(xiàn)曹禺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閃現(xiàn)出異樣的光采,蘊(yùn)含著深邃的智慧之光,似乎有一種攝人魂魄的美。鄭秀凝神注視著曹禺,曹禺也深情地看著她。好一會(huì)兒,鄭秀才醒悟過來,滿臉緋紅,掩飾地說:“天不早了,該回去了。”
“還早呢,再走走吧!”曹禺挽留地說。
說也奇怪,鄭秀也不由自主地同他又并肩散起步來。她的腳步自然地放慢起來,聽他談將來;談她的優(yōu)點(diǎn):聰明、大方、用功、活潑……聽著他那娓娓動(dòng)聽的言談,鄭秀心頭蕩起幸福、甜蜜的感覺。
“我認(rèn)為我們兩個(gè)性格不同。我是家里的大女兒,從小在教會(huì)學(xué)校讀的書,我講究嚴(yán)謹(jǐn)、潔凈;講究儀表,花錢花慣了。從小過的是獨(dú)立生活,長大了脾氣也不好。我們兩個(gè)交朋友,怕不合適。”她很直率地向曹禺說。
“性格不合,相互會(huì)了解,多諒解就行。我覺得你很像我母親,慷慨,落落大方,有大家風(fēng)度,又有抱負(fù)。不光我喜歡,我媽媽也一定會(huì)喜歡你的。”曹禺也很直率。
原先兩人散步,是曹禺一人談的多,鄭秀很少插話。自從“撿書”事件之后,似乎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她的芳心,鄭秀開始主動(dòng)地談她的家庭,她的經(jīng)歷,尤其喜歡談寵愛她的爸爸鄭烈,于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辛亥元老的形象,在曹禺的腦海中越來越清晰起來……
扮郵差黃龍崗九死一生
在散步過程中,鄭秀滔滔不絕向曹禺談起她父親鄭烈的往事。
“我的父親鄭烈,字曉云,福州人。他和辛亥先烈方聲洞是至交,還是親戚。他們都是日本留學(xué)生,第一批同盟會(huì)會(huì)員,在孫中山先生主持下,宣誓‘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宣統(tǒng)三年(1911年)父親與方聲洞一起,在同盟會(huì)最高軍事指揮員黃興策劃下參加廣州起義。起義缺乏武器,方聲洞、鄭曉云等商議,事先買了一口大的楠木棺材,將武器放在空棺內(nèi)。進(jìn)廣州城門時(shí),清官喝令開棺檢查。方聲洞急中生智,謊稱開棺鑰匙忘帶在身邊,同時(shí)又給清官塞了一些好處費(fèi),這才將棺木運(yùn)進(jìn)城里。不料起義時(shí),寡不敵眾,方聲洞、林覺民等許多人在戰(zhàn)斗中犧牲,方聲洞身中數(shù)槍逝世,也有人受傷被俘慘遭殺害。廣州起義共死難烈士86人,事后收拾烈士遺骸72具,合葬在廣州城郊黃花崗,這就是民國史上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聽父親說,在這次起義中,他幸免于難。他和辛亥元老胡漢民一起從死尸堆里爬出來,胡漢民化裝成琴師,父親化妝成郵差,才逃出封鎖線,撿回了一條性命。方聲洞視死如歸,舍生取義。廣州起義前一夜就寫好兩封遺書,一封給父母,一封給妻子王穎。在給父母的信中,方聲洞說:‘先男兒在世,若能建功立業(yè)以強(qiáng)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斗而死,亦大樂也;視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yīng)爾也。’在給妻子王疑的遺書中,方聲洞還寫道:‘刻吾為大義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無憾矣。’并叮囑妻子他死后要‘教旭兒長大一定要愛國。’旭兒指的是方賢旭,他生于1910年,和你同年。二姨夫父親罹難時(shí),他剛滿周歲……”
談起方聲洞的姐姐方君瑛,鄭秀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她告訴曹禺,方君瑛是父親最贊嘆的一位女杰。她領(lǐng)導(dǎo)能力、組織能力特強(qiáng)。在同盟會(huì)中,大家一致推舉她當(dāng)實(shí)行部部長,負(fù)責(zé)行刺、暗殺清廷巨官。孫中山先生特別看重她的頭腦冷靜,為人正直,辦事縝密果斷。福州光復(fù)后,父親等共舉她為女子師范學(xué)校校長,后往法國留學(xué),成為我國女留學(xué)生在法國獲得碩士學(xué)位的第一人。
“可惜,”說到這兒鄭秀忽然長嘆了口氣,“她1922年回國不久,就在第二年,在寓所吸嗎啡自殺,因服得過多,不治身亡。”
“她為什么要自殺?”曹禺急切地問。
“她對(duì)當(dāng)時(shí)國內(nèi)復(fù)雜的狀況,國事日非,社會(huì)腐敗,人民悲慘,感到十分憤怒傷痛。我父親當(dāng)時(shí)親眼見到她留下的兩紙遺書,并應(yīng)南洋一家報(bào)社的邀請(qǐng),寫過許多同盟會(huì)時(shí)代福州革命同志的史實(shí)。在文章中,父親盛贊方君瑛是‘同盟會(huì)女杰’。他還對(duì)我說,同盟會(huì)女杰,一般人只知道有浙江的秋瑾,而不知道我們福建也有一位女杰,她對(duì)革命的貢獻(xiàn),以及她的德性之美,都不在秋瑾之下。”
聽著鄭秀滿含深情的描述,曹禺對(duì)尚未謀面的未來岳丈及滿門忠烈的方氏一家充滿了崇敬之情。
金陵城翁婿暢談《精忠柏》
曹禺與鄭秀的初戀在美景如畫的清華園迅速升溫。初夏的夜晚,皓月當(dāng)空,如水的月光灑在清華大禮堂前白色大理石圓柱上,將禮堂周圍照耀得像銀色世界。從禮堂前大樓窗口傳出橫笛、黑管、薩斯管和圓號(hào)吹奏出的悅耳旋律。

方聲洞

方聲洞與妻王穎、子方賢旭

同盟會(huì)女杰——方君瑛
“這么晚了,校軍樂隊(duì)還在演奏。家寶,你能聽得出這是什么曲子嗎?”鄭秀故意考考曹禺。
“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真美!貝多芬真是了不起的音樂天才!”曹禺贊嘆道。“穎,咱們坐會(huì)吧。”鄭秀號(hào)穎如,曹禺簡稱“穎”,有時(shí)又叫她“多拉”,那是狄更斯自傳體小說《大衛(wèi)·考帕菲爾》中一個(gè)女孩的名字。
兩人在旗桿底座的石板上盡情聆聽美妙的樂曲,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
然而,不久鄭秀將她和曹禺的戀情寫信告訴父親鄭烈,父親起先卻一個(gè)勁兒不贊成。鄭秀有姐妹八個(gè),她最大。父親對(duì)她的婚事很慎重,希望她嫁給一個(gè)既有才華、家庭又有一定地位的青年。父親還從側(cè)面了解到萬家已是一個(gè)敗落的家庭;萬家寶平時(shí)穿著也很寒酸,常常穿一件竹布長衫;個(gè)子不高,夾著一大堆書,在清華園踽踽獨(dú)行。尤其讓他不放心的是,相傳這個(gè)萬家寶還是個(gè)激進(jìn)人物,甚至有人說他是共產(chǎn)黨。為此,他特地托人到清華大學(xué)詢問有關(guān)情況,問此事是否屬實(shí)。對(duì)方回答說;清華有兩個(gè)姓萬的,一個(gè)是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跑了,剩下的這個(gè)姓萬的,看樣子也靠不住。這個(gè)回復(fù),又讓鄭秀父親增加了煩惱。他特地寫了一封信,勸女兒頭腦不要太熱,要冷靜,要三思,婚姻乃終身大事,一失足會(huì)成千古恨。不久,他接到鄭秀的來信,堅(jiān)持要同家寶相愛,并詳細(xì)地介紹了曹禺的家庭情況,說他也是書香門第出身,并詳述了萬德尊的經(jīng)歷。
收到女兒的來信,鄭老先生在書房里踱過來,走過去,思考良久。最后他將秘書喊來,吩咐他去南京歷史檔案館跑一趟,在前清檔案中查一查,有沒有一個(gè)留學(xué)生叫萬德尊的。秘書查閱后稟報(bào)說:確有此人。在“清國留學(xué)生公館第五次報(bào)告”中,載有“同學(xué)姓名調(diào)查錄”,有一個(gè)叫萬德尊的,字宗石,是湖北潛江人,與他同期在日本陸軍士官學(xué)校留學(xué)的還有閻錫山、黃國梁等。
聽了秘書的稟報(bào),鄭老先生這才放心,便回一信給鄭秀說:只要你自己中意,為父不加干涉。鄭秀將此復(fù)信告訴家寶,兩人都?xì)g喜不已,相約晚上進(jìn)城觀看意大利著名歌劇《風(fēng)流寡婦》,以示慶賀。
此后,鄭秀每隔一段時(shí)間,將他們兩人的情況簡要告訴她父親。職業(yè)劇團(tuán)“中旅”公演的《雷雨》,風(fēng)靡全國大獲成功,很快各地掀起《雷雨》熱,曹禺成為名噪一時(shí)的劇壇新星,鄭老先生也感到家寶確是一個(gè)突出的人才。
1934年—1936年,曹禺的兩部大型話劇《雷雨》《日出》發(fā)表,轟動(dòng)全國。南京國立戲劇學(xué)校(后改為國立戲劇專科學(xué)校,簡稱“劇專”)多次邀請(qǐng)曹禺來校任教。1936年秋,曹禺終于來到南京任教。在鄭秀的引見下,拜會(huì)了仰慕已久的鄭老先生。老先生見他彬彬有禮,又能侃侃而談,越發(fā)喜歡。在曹禺的影響下,鄭老先生竟對(duì)話劇創(chuàng)作也發(fā)生了興趣,并試著寫了一部多幕話劇《精忠柏》。他讓秘書用毛筆認(rèn)認(rèn)真真抄了一遍,親書“請(qǐng)家寶斧正”幾個(gè)字,送給曹禺過目。曹禺一看啼笑皆非,劇本寫得不倫不類,既不像京戲,又不像文明戲,但他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見。鄭老先生看了連連點(diǎn)頭:“講得極是,講得極是。”
為了進(jìn)一步修改劇本,同時(shí)也為了進(jìn)一步加深對(duì)曹禺的了解,鄭烈多次邀請(qǐng)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帶車庫的洋房里詳談。
鄭烈的《精忠柏》寫得很長,取材于宋朝岳飛抗金的歷史題材,從岳母刺字、受宗澤重用、朱仙鎮(zhèn)大捷,一直寫到十二道金牌召回、在風(fēng)波亭遇害等情節(jié),都寫得十分詳細(xì)。劇中出場(chǎng)的人物不少,除岳飛、岳云等主要的正面人物之外,秦檜、王氏、萬俟占等賣國奸佞也都全部出場(chǎng)。鄭烈當(dāng)時(shí)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負(fù)責(zé)檢察署、監(jiān)獄等部門,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謙恭,敬稱為“伯父”。但談到劇本意見,他也較坦誠。他說:“伯父,您的這部劇作好在不胡編,主要?dú)v史事件、主要?dú)v史人物處處有出處。情節(jié)發(fā)展原原本本,脈絡(luò)十分清楚。不過,劇本本身可能長了一些,搬上舞臺(tái)的話,至少要七八個(gè)小時(shí)以上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許的話,我可以冒昧幫您再作一些刪削。”同時(shí),曹禺又謙虛地請(qǐng)問:“劇本為什么取名‘精忠柏’?”
“這是因?yàn)楹贾菸骱脑缽R中,樹枝均向南傾斜。后人認(rèn)為這是岳飛堅(jiān)決抗金的精誠感召所致,故贊譽(yù)為精忠柏。岳廟久經(jīng)滄桑,此事是否屬實(shí),已難稽考。但我?guī)状稳ミ^杭州,岳廟內(nèi)仍有精忠柏亭。亭中陳列若干柏樹樹段,據(jù)云精忠柏已枯萎而死,留此以供后人憑吊。我覺得這是國人對(duì)岳飛精神的敬仰之情,故之取名‘精忠柏’,你意如何?”鄭烈問曹禺。曹禺極口稱贊,兩人共同贊譽(yù)岳飛還我河山、精忠報(bào)國的精神。
“很有深義,它象征了岳武穆的精神,一種堅(jiān)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悲劇精神。”未來的翁婿越談越投機(jī)。
1987年,鄭秀在回憶這段歷史時(shí),對(duì)筆者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父親后來喜歡曹禺甚至超過了喜歡我。”
訂婚宴群賢畢至
南京,曹禺住在四牌樓十七號(hào)一幢兩層樓的樓房里,樓上樓下各兩間。這幢樓,原先是白楊、馬彥祥當(dāng)初同居時(shí)的住所。后兩人分離,白楊去上海明星公司拍電影,馬彥祥另住別處,將原住房讓給曹禺租用。1936年夏,鄭秀從清華大學(xué)畢業(yè),系里的教授想留她在學(xué)校當(dāng)助教,待遇不錯(cuò),而且可能一邊教書一邊做學(xué)問。鄭秀有些心動(dòng),寫信征求曹禺的意見,他一連來了好幾封信,勸鄭秀無論如何要回南京,說若是兩地分居以后各方面都很不方便,鄭秀只好放棄了自己的學(xué)業(yè),在南京審計(jì)部當(dāng)了一名科員。住在青年會(huì),與曹禺每周見面。

曹禺繼母薛詠南
1936年秋,經(jīng)兩家協(xié)商,決定在南京舉行訂婚儀式。曹禺繼母親自來南京與親家公鄭烈一起張羅安排。繼母薛詠南,為人精明能干,落落大方,舉止很有分寸。她第一次進(jìn)親家公家,手頭只有一百二十五元大洋,鄭烈家有十個(gè)傭人,她當(dāng)場(chǎng)每人給十元大洋。
這年11月26日,兩人在南京平倉巷德瑞奧同學(xué)會(huì)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德瑞奧同學(xué)會(huì)在南京頗有名氣,里面有舞廳、餐廳,可容四五百人。每位應(yīng)邀的賓客,都收到一份精美的請(qǐng)柬,那上面寫著:
茲定于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shí)正假座德瑞奧同學(xué)會(huì)。
為小兒家寶
小女 秀
舉行訂婚典禮 恭請(qǐng)
光臨
萬薛詠南
謹(jǐn)邀
鄭曉云
十一月二十日
這天下午,賓客盈門,薛詠南穿著一件狐皮大衣,當(dāng)著親朋好友的面,從一只盒子里拿出白金鑲金剛鉆戒指,作為訂婚禮,祝愿鄭秀、曹禺相親相愛,白頭偕老。

萬老太太讓曹禺將這只戒指給鄭秀戴上。曹禺拿起戒指,鄭重而深情地給鄭秀戴上了。
許多文化名人,像巴金、靳以、馬彥祥、張?zhí)煲淼榷紖⒓恿诉@次典禮。那時(shí)上海與南京剛剛開辟了飛機(jī)航線,巴金與靳以是特地坐了飛機(jī)從上海趕到南京的。他們帶來的禮品是一個(gè)特大號(hào)的洋娃娃,做工十分精巧:那洋娃娃的一對(duì)大眼睛眨巴眨巴會(huì)動(dòng);嘴也能一張一閉的,還會(huì)表演吸奶的動(dòng)作。鄭秀看了十分喜歡。
臨開宴的時(shí)候,忽然仆人向曹禺通報(bào):正在劇校兼課的田漢先生來了。曹禺原聽說田漢去福州游覽去了,故而未送請(qǐng)?zhí)?/p>
不一會(huì)兒,田漢興沖沖地走了進(jìn)來,手里拿著一包東西,一見曹禺就說:“家寶,恭喜恭喜!”
曹禺介紹田漢與母親、鄭秀認(rèn)識(shí)。見過禮后,田漢將手中拿著的兩卷東西展開。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田漢親手書寫的“蜚聲誘和”四個(gè)大字。另有一張條幅,上面是田漢親筆題詩一首。詩曰:
女以男為家,男以女為室。
室家至足樂,國亡乃無日。
萬兄殆國寶,英年擅寫實(shí)。
揭出黑漆團(tuán),病者可諱疾。
從來舞臺(tái)上,非無救亡術(shù)。
時(shí)局雖萬變,出路只有一:
不與強(qiáng)敵戰(zhàn),無由脫桎梏!
攜手火線下,羨兄得良匹。
從容畫蛾眉,且待戰(zhàn)爭畢。
譬如《雷雨》后,登山看《日出》!

曹禺與鄭秀演《最前的與最后的》(1932年)
“一份薄禮,不成敬意。”田漢豪爽地說。
“謝謝田先生,寫得好極了。”曹禺、鄭秀齊聲道。
“田先生,請(qǐng)共進(jìn)晚餐。”萬老太太熱情地邀請(qǐng)說。
“不,不!我是專程賀喜,送上這份薄禮,表示敬意。至于喜酒嘛,改日再來討擾。”說完田漢就要告辭。萬老太太、曹禺、鄭秀等一再挽留,田漢堅(jiān)辭,邁開大步一陣風(fēng)似地離開了宴會(huì)廳。
夜12點(diǎn),訂婚儀式在歡騰熱鬧的氣氛中結(jié)束了。曹禺鄭秀送鄭父上車,鄭父對(duì)鄭秀說:“萬老太太真是個(gè)能人,落落大方,舉止很有分寸,是個(gè)見過世面的人。她要是個(gè)男的,那可真了不得。秀,有這樣的婆婆,也是你日后的福氣。”一句話說得鄭秀粉臉緋紅。
望著父親遠(yuǎn)去的汽車,鄭秀、曹禺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
石頭城爭看家寶演樸園
1937年元旦,南京各大報(bào)紙登出了赫然醒目的廣告:
一九三七年中國劇壇第一聲
中國戲劇協(xié)會(huì)假座世界大戲院
六幕劇《雷雨》作劇曹禺導(dǎo)演馬彥祥
姿態(tài)新穎,技巧純熟,30余人登臺(tái)
時(shí)間 日?qǐng)龆r(shí) 夜場(chǎng)八時(shí)
演員陣容表也引起了觀眾極大的興趣(出場(chǎng)先后為序):
魯 貴 馬彥祥 周繁漪 鄭挹梅
四 鳳 李 萱 周 萍 戴 涯
大 海 裘 水 周樸園 萬家寶
周 沖 王英豪 魯侍萍 于真如
當(dāng)晚,在世界大戲院,緊張的預(yù)演在進(jìn)行著。

曹禺飾演的周樸園(1937年)
后臺(tái),演員們正進(jìn)行著有條不紊的化妝。服裝管理員王先生幫挹梅穿一件杏黃色的長旗袍,她感到很奇怪:“怎么穿這種顏色的衣服?”王先生告訴她,“這是萬先生特意關(guān)照的,他說這樣的色彩打上燈光更能襯托出人物性格。”挹梅將信將疑,放眼一看,萬先生正在化妝,便不便再打擾他。
不一會(huì),萬先生走過來了,戴一副橢圓形的金邊眼境,穿一件團(tuán)花的官紗大褂,頭發(fā)很潤澤地分梳到后面,宛如換了一個(gè)人。在鄭挹梅的印象中萬先生個(gè)子不高,今天好像突然長高了一些,便好奇地問:“萬先生,您今天怎么忽然長高了?”曹禺微微一笑,將左腳的一只皮鞋脫了下來,“秘密在這兒!”挹梅一看,那鞋底加厚了許多,禁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您真有辦法!”
“這叫天無絕人之路!”曹禺笑著說。
激動(dòng)人心的正式公演開始了。世界大戲院的池座里鴉雀無聲,人們被臺(tái)上精湛的表演迷住了。尤其是曹禺扮演的周樸園,更引起觀眾的注目。他既演出了周樸園專橫、虛偽的一面,同時(shí)又揭示了這一人物變異復(fù)雜的人性,體現(xiàn)了劇作家的悲憫情懷,讓觀眾們嘆為觀止。
給觀眾印象最深的是全劇結(jié)束時(shí)曹禺的表演:周沖和四鳳相繼觸電而死,周公館籠罩在驚恐之中,場(chǎng)上只剩下周樸園和繁漪。周樸園突然想起了周萍,他驚慌地叫道:“萍兒呢?大少爺呢?萍兒,萍兒!”曹禺連叫了三聲“萍兒!”緊接著傳來的是書房內(nèi)周萍自殺的槍聲,室內(nèi)死一般的沉寂。在這一段戲中,曹禺處理這三聲“萍兒”,用的是氣聲,一聲與一聲不同,越來越強(qiáng),將人物驚慌、不安、恐懼的心理狀態(tài)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出來,緊緊地攫住了觀眾的心。直到幕落,觀眾緊張的心情還難以平息。五十年后,同臺(tái)演出的鄭挹梅回憶說:“這三聲‘萍兒’給我的印象極深,至今還在我耳邊回響。”
扮演魯貴又兼導(dǎo)演的馬彥祥回憶起這次演出,也興奮地說:“我看過不下十幾個(gè)周樸園,但曹禺演得最好。這可能因?yàn)樗米约簩懙娜宋铩K莻€(gè)好演員,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我覺得演周樸園沒有誰比他演得更好的了。”
曹禺扮演的周樸園這一舞臺(tái)形象,又一次顯示了他卓越的表演才能。曹禺親近的朋友,有的甚至認(rèn)為他表演藝術(shù)的成就高于劇作,若不是受身材限制,“他真是中國能夠演多型角色而藝術(shù)修養(yǎng)最高的優(yōu)秀演員。”
中國戲劇學(xué)會(huì)演出的《雷雨》是一臺(tái)珠聯(lián)璧合的演出。除曹禺外,其他幾個(gè)角色也演得十分成功。馬彥祥扮演的魯貴,將這個(gè)猥瑣的狡仆演得維妙維肖。尤其第三幕,他被周家辭退后,在家里百無聊賴,躺在竹躺椅上,蹺起腿,揮著蒲扇,哼著“天牌呀、地牌呀”的黃色小調(diào),還冷嘲熱諷地?cái)?shù)落四鳳,摳著腳丫子,不時(shí)地放在鼻子跟前聞聞,一見周沖深夜送來一百元錢,忙揮起蒲扇扇去凳子上的灰,又阿諛地給他打扇,活畫出一副善于逢迎、見錢眼開的無賴嘴臉。
《雷雨》在南京的首演引起了出人意外的轟動(dòng),口碑載道,佳評(píng)滿街。演出連場(chǎng)客滿,要求延長演期的函電紛至沓來,愈演愈滿,觀眾如潮。
鄭秀與鄭老先生一家也來看戲了。《雷雨》在南京的轟動(dòng),使鄭老先生覺得臉上也有光彩,他逢人便夸家寶“真乃奇才!既會(huì)編戲,又會(huì)演戲。”他在南京世界大戲院為《雷雨》的演出還特地包了好幾場(chǎng),要親戚朋友們都去看看。鄭秀也為自己選中這樣一個(gè)好對(duì)象而感到自豪。
奉父命鄭秀避難蕪湖城
1937年7月抗戰(zhàn)爆發(fā),8月13日,日寇又大舉進(jìn)攻上海。在三個(gè)月的戰(zhàn)斗中,大約有27萬中國士兵傷亡,不久日寇飛機(jī)開始轟炸南京,南京岌岌可危。
鄭秀遵照父親意見,避難到安徽蕪湖,在老同學(xué)周燕家暫住。“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由于戰(zhàn)火頻繁,接連數(shù)月,鄭秀與家人失去聯(lián)系。她在蕪湖度日如年。情急之下,在老同學(xué)陪伴下,到街上請(qǐng)一個(gè)瞎子測(cè)字,占卜一下家人、曹禺吉兇如何。只見那瞎子口中念念有詞,不一會(huì)吐出一番話來:
“小姐不必?fù)?dān)憂,你所思念的親人、好友,不出半月便有音信。”
鄭秀聽了大喜,多給了一些錢,并連聲謝過瞎子。當(dāng)晚睡在床上,鄭秀對(duì)瞎子的話將信將疑,她自思自忖,也許他說的是真的呢?這樣一想,也就心安了。不久,便沉沉入睡。這是三個(gè)月來,她頭一回睡得這么香。
第二天一早,鄭秀忽然被人推醒。
“秀,好消息!”周燕拿著一張電報(bào)紙笑嘻嘻地說。
“什么好消息?”
“你猜猜看。”周燕神秘地笑了笑。鄭秀見她一雙手抄在背后。
“拿過來吧,別逗了。”趁周燕不提防,鄭秀猛地一把將一張紙搶了過來。一看,是曹禺母親從天津發(fā)來的電報(bào),全文為:“萬已乘英輪平安赴港,即赴漢。”
鄭秀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將電報(bào)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地又看了一遍。讀完,高興得抱住周燕直打轉(zhuǎn)。
這一時(shí)期,曹禺、鄭秀正處在熱戀中,來往書信很多,鄭秀的表弟、沈澧莉的弟弟沈祖戡為鄭秀當(dāng)信使,每天來回為他們發(fā)信、寄信,忙得不亦樂乎。
第二天,鄭秀又收到曹禺寫來的一封信,告訴她,他已離香港到達(dá)漢口,現(xiàn)住在外婆家,讓她盡快趕到武漢找他。
9月底,曹禺和鄭秀趕到國立劇校遷校所在地長沙,租了兩間破舊房子,將就住了下來。
在長沙,曹禺除了指導(dǎo)劇校學(xué)生進(jìn)行《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戰(zhàn)街頭劇演出,還在長沙又一村民眾大禮堂舉行劇場(chǎng)公演,演出《毀家紓難》《炸藥》《反正》三個(gè)抗敵獨(dú)幕劇。
一天,曹禺正在指導(dǎo)學(xué)生的劇場(chǎng)演出。演出的最后一個(gè)劇目是《反正》。可能因?yàn)榻裉斓挠^眾一半以上是傷員的緣故,這個(gè)戲的演出效果特別好,許多場(chǎng)面都使剛強(qiáng)如鐵的傷員低下頭擦淚。有一個(gè)傷員被感動(dòng)得無法控制,突然在樓座上站了起來,揮起拳頭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堅(jiān)持抗戰(zhàn)到底!”
演出在暴風(fēng)雨般的掌聲中勝利結(jié)束。學(xué)生們到后臺(tái),高興得跳了起來,女同學(xué)互相擁抱著,有的激動(dòng)得哭了起來。看著這樣熱烈的場(chǎng)面,這樣可愛的學(xué)生,曹禺含淚而立,久久說不出一句話。
正在曹禺欣喜、激動(dòng)不已的時(shí)候,一個(gè)學(xué)生來喊他:
“萬先生,外面有一位小姐在找您。”
來找曹禺的姑娘不是別人,正是鄭秀。一見曹禺走出劇場(chǎng)門外,鄭秀忙笑嘻嘻迎上去,說:“家寶,爸的回電來了。”
原來曹禺與鄭秀相約在長沙舉行正式婚禮,為了鄭重起見,決定兩人分頭發(fā)電報(bào)征求家中意見。前幾天,曹禺已收到萬老太太發(fā)來的電報(bào),電文為:“同意,祝你們幸福。”這幾天就等鄭秀父親的回電了。
曹禺接過鄭父回電一看,電文極為簡練,只有一個(gè)字“可”(這也是民國初年一些革命黨人慣用的寫法)。
不久,曹禺與鄭秀在長沙青年會(huì)舉行婚禮。余上沅校長為證婚人,參加婚禮的有吳祖光、余上沅夫婦,陳治策夫婦,教務(wù)處的兩個(gè)同事等二十余人。婚禮簡樸而又隆重,是一個(gè)合乎規(guī)格的、很正式的儀式。婚后,兩人便遷往稻谷倉居住。新房布置得也非常質(zhì)樸,兩把藤椅,兩張帆布床,還有一個(gè)大書桌。
曹禺和鄭秀就在這樣的一個(gè)小家里開始了他們的生活。身處亂世,鄭秀隨著曹禺顛沛流離地去過很多地方。對(duì)她來說,那是一段雖苦猶甜的珍貴記憶。
別生父淚灑機(jī)場(chǎng)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國民黨軍隊(duì)土崩瓦解,全國已處于革命勝利的前夜。上海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濃重。
龍華機(jī)場(chǎng),一架即將起飛的專機(jī)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鄭秀一個(gè)人站在飛機(jī)旁,焦急地向機(jī)場(chǎng)入口處張望。
“穎如,你還在望什么?”鄭父焦急地問。
“你不是說通知家寶與我們一起去臺(tái)灣嗎?怎么到現(xiàn)在還沒有來?”
“誰知道呢,也許他碰上什么事……”鄭父含含糊糊地搪塞著,其實(shí)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處,根本就沒有派人去接曹禺。為了讓女兒同自己一起離開大陸,鄭父四次動(dòng)員女兒。

此時(shí),鄭秀與曹禺的感情已漸趨冷漠。從江安遷居重慶后,曹禺住南岸復(fù)旦大學(xué)教書,每周回來兩三次,與孩子們恢復(fù)了感情,但與方瑞仍藕斷絲連,方瑞仍苦苦地追求他(注:這一段情緣詳見《江安之戀與<北京人>的誕生》,曹樹鈞著,載本刊2010年7月號(hào))。回到重慶之后,鄭秀如魚得水,交游廣泛,與男性朋友接觸頻繁,既有清華過去的老同學(xué),也有新交的朋友。這引起曹禺的誤會(huì),以為鄭秀經(jīng)過江安一場(chǎng)風(fēng)波之后已不愿意同他恢復(fù)關(guān)系,兩人之間的關(guān)系又漸漸疏遠(yuǎn)起來。1947年,曹禺從美國講學(xué)回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一度在上海實(shí)驗(yàn)戲劇學(xué)校(今上海戲劇學(xué)院前身)任教,又經(jīng)黃佐臨介紹,擔(dān)任上海文華影業(yè)公司編導(dǎo),創(chuàng)作并導(dǎo)演了電影《艷陽天》。此時(shí),鄭秀則帶著萬黛、萬昭兩個(gè)女兒住在南京,偶爾到上海小住,也總是很快返回南京,因?yàn)樗谀暇┚蜆I(yè)。時(shí)局緊張以后,當(dāng)局通知鄭父攜全家撤往臺(tái)灣。這使鄭秀感到十分為難。一頭是父親,一頭是丈夫,哪一頭都依依難舍。她愛曹禺,父親說已通知曹禺同行,她這才同意動(dòng)身。
鄭秀看看手表,離飛機(jī)起飛的時(shí)間只有五分鐘了,她仍癡癡地等著。
時(shí)間過了,還不見曹禺的人影,飛機(jī)響起了啟動(dòng)的響聲。
“穎如,快上機(jī)吧!他不會(huì)來了!”
“不,他不去,我也下去!”鄭秀毅然將兩個(gè)女兒叫下機(jī)艙。
“穎如,穎如!”鄭父焦躁地阻止她:“穎如,難道你忍心拋下為父嗎?”兩鬢白發(fā)的父親深情地望著女兒鄭秀。
鄭秀心中一陣酸痛,但又決然地說:“爸,女兒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說著她含淚拉著兩個(gè)女兒,轉(zhuǎn)身就往出口處走。
“穎如,穎如!你給我回來!回來!”
鄭父聲嘶力竭地叫著,鄭秀和兩個(gè)孩子噙著淚,一步一回頭地走出機(jī)場(chǎng)。她就這樣和父親一訣成永別了。
憶往昔難忘翁婿情
從1948年至1988年,曹禺與鄭烈的音訊中斷了將近半個(gè)世紀(jì)。上世紀(jì)八十年代,筆者在從事文學(xué)傳記《攝魂——戲劇大師曹禺》(曹樹鈞、俞健萌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5月初版)創(chuàng)作和第一部關(guān)于曹禺的電視傳記片《杰出的戲劇家曹禺》的拍攝過程中,多次訪問鄭秀,才重新打開了鄭秀多年諱言的記憶。
一次在交談中,我告訴鄭秀,有一位德國記者叫烏韋·克勞特,他酷愛中國文化,熱愛曹禺,特地請(qǐng)著名表演藝術(shù)家、翻譯家英若誠為他引見曹禺,同曹禺結(jié)成好友,他特地寫了一篇長篇專訪《戲劇家曹禺》,文中曹禺在建國后第一次提到了他的岳父鄭曉云。
鄭秀十分感慨地說:“他現(xiàn)在又想起他的岳丈了!”她問此文刊在什么地方,我告訴他發(fā)在兩個(gè)刊物上,一個(gè)是《中國文學(xué)》1980年第11期,英文版,向全世界發(fā)行,一個(gè)是北京的刊物《人物》1981年7月第4期。
我對(duì)鄭秀說,曹禺的內(nèi)心深處是不可能忘卻他的岳父的,在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曹禺與岳丈暢談話劇《精忠柏》,岳飛留給他的印象是刻骨銘心的。1943年1月,在重慶,《戲劇月刊》創(chuàng)刊號(hào)(曹禺是九個(gè)編委之一)上“特刊稿件預(yù)告欄中,公布了曹禺創(chuàng)作的有關(guān)岳飛的歷史劇《三人行》即將問世的消息,曹禺為此還寫了一篇《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談》。這年2月,曹禺又應(yīng)邀在上清寺儲(chǔ)匯大樓重慶儲(chǔ)匯局同人進(jìn)修服務(wù)社作了一次題為《悲劇的精神》的學(xué)術(shù)講演。在講演中他認(rèn)為莎士比亞筆下的普魯托斯、中國的屈原、諸葛亮、岳飛是有著可歌可泣悲劇精神的人物,處于抗戰(zhàn)時(shí)期的中華民族要存在,“中國要立足于世界,我們要救亡,要反抗,”就要弘揚(yáng)這些真正的悲劇人物雄偉的氣魄,他們勇往直前、堅(jiān)持不懈的悲劇精神。
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強(qiáng)、國家要立足于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終與岳飛和鄭烈的心是相通的,與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脈相通的。
關(guān)于這部已經(jīng)預(yù)告的歌頌岳飛的劇本,曹禺這樣描述道:“《三人行》是岳飛、宋高宗和秦檜的故事。在重慶只寫了一幕,太難了。全部是詩,沒有別的對(duì)話,吃力得不得了。大熱的天,搞得累死了。是馬宗融為我找到的房子。馬宗融是巴金介紹我的,一個(gè)法國留學(xué)生,是非常好的朋友。這家農(nóng)民大概是個(gè)中農(nóng)吧,有三四個(gè)孩子,我是自己背著米下鄉(xiāng),自己燒飯。我是想試一試,用新詩寫一部詩體劇,終于搞不下去了。第一幕是從金回來,我想寫出點(diǎn)新意,但是,也沒有歷史可考,材料上遇到問題,不得不罷手了。我記得很清楚,就寫在一個(gè)記賬用的條紙上,寫了無數(shù)次,只寫了一幕。‘文革’期間,我把它撕毀了。”
遺憾的是這部歷史劇因?yàn)榉N種原因未能完成。但它所要歌頌的悲劇精神,我們從曹禺的講演中,已經(jīng)可以觸摸得到了。
“不思量,自難忘。”歷史是不可能割斷的,血濃于水,民族的感情、愛國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無法切斷的。
曹禺和鄭秀在南京訂婚,訂婚照擺在鄭烈的客廳中,鄭秀表妹沈澧莉母親曾贊揚(yáng)說:“這張照片拍得好,曹禺微微笑。”鄭秀還曾托筆者尋找這張“微微笑”的照片。
鄭秀又怎能忘記父親用他的自備汽車,親自送女兒、送表妹、表弟上車避難安徽蕪湖,逃過南京大屠殺這一劫的情景呢?
鄭秀更忘不了“四人幫”粉碎后,方聲洞夫人王穎邀請(qǐng)鄭秀、沈澧莉、沈祖戡在北京舉行歡迎遠(yuǎn)方來客的家宴上,所講述的黃花崗72烈士們可歌可泣的壯舉。
一百年前,辛亥先烈為推翻封建專制政體所作出的豐功偉績,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不僅永載史冊(cè),而且將永遠(yuǎn)活在億萬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