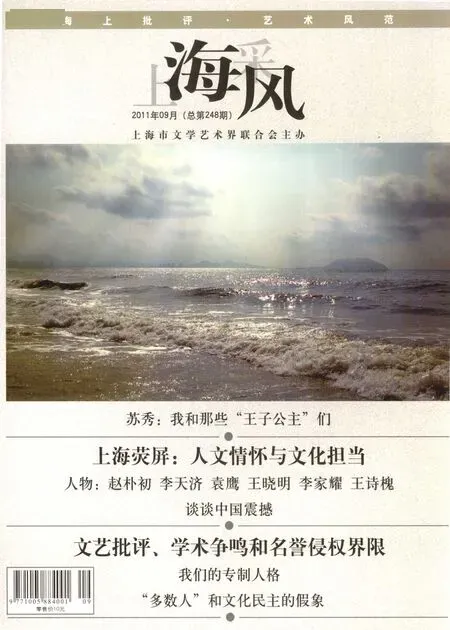《杜月笙正傳》連載風波
文/張朝杰

我今年虛歲九十有二,住在松江社會福利院,近日整理書架,在不多的藏書中,翻到一本《杜月笙正傳》,不由引起我對一些往事的回憶。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發行的報刊和出版的書籍中鮮見關于上海灘傳奇人物之一——杜月笙的只字片語。當時任《青年報》文藝組組長的吳紀椿,我們叫他小吳,30歲左右,思想敏銳,思路開闊,他想出要請原《文匯報》總編、已退休在家的徐老徐鑄成執筆,撰寫《杜月笙正傳》供《青年報》長篇連載。這當然是一個好點子。在取得總編施惠群(后任市政府秘書長)和徐老的同意后,每周一期的《青年報》,從1981年7月10日第7版起每周一個版連載,每期在報紙作顯眼的預告。這在當時是一件很轟動的事件,引起全國多家媒體關注和轉載,尤其使上海出版的《青年報》訂戶猛增十幾萬份。
當時我也在《青年報》編輯部工作(離休后返聘)。一天,總編老施(那時還未時興稱施總),要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開門見山問道:“張老(我那時只有六十開外,卻是全報社最年長的,才得到這尊稱),你認識杜月笙的兒子嗎?”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老施繼續說,杜月笙有個兒子在上海,叫杜維翰,打電話給市委統戰部,說杜月笙是統戰對象,他以家屬身份不同意《青年報》刊出《杜月笙正傳》,統戰部也打電話給市委宣傳部,宣傳部也通知他不行就不要刊登了吧!
可是如果真的不刊登,如何向廣大讀者,尤其是聞風而來的大量新訂戶交代呢?這會影響報紙聲譽的。他要我到杜維翰家去做說客,我答應了。
當天晚飯后,我拿了老施給我的地址,在一家公寓的二樓,找到了杜家。我按了門鈴,有人來開門。我問:“你是杜維翰先生嗎?”他說:“是的。”我說我是《青年報》的記者,并給他看我的記者證。對方看也不看,毫無表情地讓我進門后,把門關上,走在前面,引我進了他的臥室。
當時,杜維翰在徐匯區房管所工作。單位里就分配給他這么一間一室的住房。他和我分坐在靠近床尾的一只茶幾兩旁的椅子上。他未給我介紹一下他的夫人,坐在床沿邊上側身看著我。茶未倒一杯,煙也沒遞一根。
為了打破僵局,我先開口:“聽說你不同意我們刊登《杜月笙正傳》?”他沉著臉說:“你們比我們懂政策啊!”(其意是他不同意,我們按政策就不可以刊登)。他的夫人插話說:“我們的爸爸雖然去世了,可是他在國內外還有很多朋友。誰要是瞎寫的話,會有人出來說話的。”話外之音是:你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寫不登為佳。
我心想,既然已經“疑無路”,那就只好“又一村”了。于是便問他:“你有個哥哥在哪里?”他說:“在臺灣。”我說:“不是的。在臺灣的是你大哥杜維藩。還有一個和你我差不多年齡(當時我想不起名字,后來記起來是杜維屏)。”他說:“在香港。”我說:“我們三個人,小時候一起踢過小橡皮球的。”聽后他有些驚異,可臉色開始“陰轉多云”,趕緊問道:“是不是在正始中學(杜月笙在善鐘路、今常熟路上開辦的中學)?”我說:“不是的,是在勤余坊。”
勤余坊位于華格臬路杜公館的西隔壁。華格臬路后名寧海西路。多年前從寧海西路向北到延安中路,嵩山路向東到上海音樂廳附近已不見房子(包括杜公館和勤余坊),成為一大片綠化地區。我父親家住在勤余坊一號,朱學范家和范默林家住在二號。弄堂寬敞,杜月笙的汽車,后來是一輛大型防彈車,夜間就停在這弄堂里。我節假日常和堂弟兄們在弄堂里踢小橡皮球。杜維翰和杜維屏有時也來和我們一起踢。可是,只要他倆一看到父親杜月笙坐的汽車經過勤余坊駛向杜公館,就會馬上跑步回家去。由此可見杜月笙家教之嚴。
杜維翰聽到我提起勤余坊,臉上開始“多云轉晴”,朝我細細看了片刻后說:“你是張伯伯的……像,很像。”他夫人也笑了,忙著給我倒茶、遞煙。
杜維翰這時像是想起了什么,問我是不是有個哥哥或是弟弟曾經在香港讀大學?我說,就是我啊!他說:“那就是了。我曾在景星渡輪上(往返于香港和九龍之間的)遇到過你,問你在做什么,你說在讀夜大學,蠻愜意的。”我記起來了,那是1940年下半年的事(一別四十余年,難怪剛見面時互不相識),我在廣州遷港的嶺南大學上大一,借香港大學課堂,下午五點到八點上三堂課,每學期讀十八個學分,因此我說蠻愜意的。
話熱絡起來,我又問:“那么你后來做什么?”他說:“為了抗日,我離開香港到重慶參加了青年軍,到緬甸和日軍作戰。抗日勝利回國后,青年軍被改編為新一軍和新六軍,我所在的部隊奉命調到東北去,路過上海,我被父親攔下來,退了伍……”我急忙插嘴道:“這說明你父親不讓你到東北去打內戰,好事啊!我們會把你父親做過的好事全寫出來的。”他笑了。我接著說:“你就同意吧!我會把每一期報紙寄一份給你看,你有什么意見就及時打電話告訴我,好嗎?”他點了點頭。我馬上說:“謝謝!”
我給他留下了我報社辦公室的電話號碼,然后向他和他夫人告辭。他送我到樓梯口,握著我的手說:“我們是世交,你常來坐坐。”我點點頭。
第二天上班,我就到總編辦公室去。老施是聰明人,一看我的神色就知道我辦妥了。我故意不提杜維翰是否已經同意,反問他:“你怎么知道我認識杜月笙的兒子?是從我檔案中找到我反動家庭的反動社會關系發現的,是嗎?現在倒派上用場了。”他笑了。這時我再也忍不住告訴他,帶來的是好消息。他眉頭散開,心里一塊石頭放下了,高興地連說:“張老,謝謝你,你立了大功。”我說:“一等功是吳紀椿的,給我個三等功吧。”
吳紀椿當然也很高興,他帶我到徐鑄成家見了徐鑄老,我又告訴他一些我所知道的杜月笙的情況。當時徐鑄老每周寫一篇,到時小吳去取稿,徐鑄老從不食言和拖延。記得我還經《解放日報》總編王維的同意,從資料室里借了兩本老《申報》有關杜月笙的剪報冊,送到徐老處供他寫作時參考。
幾天后,《杜月笙正傳》正式刊發,吳紀椿一期一期編發付印,我則將《青年報》樣報一份一份寄給杜維翰。連載持續了兩個半月,共刊發過12期,到當年9月25日為止,刊登了全書18章中的前13章。因為《杜月笙正傳》即將成書,后五章就不發,吊足讀者胃口。難能可貴的是,此后杜家公子自始至終沒有提過一次意見,我想是因為徐鑄老寫得客觀、很實在的緣故。
長篇連載結束后,有一天,吳紀椿送我一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的《杜月笙正傳》,說是徐老要我拿來送給你的。我一直保藏到現在,二十九年多了。這里我再引用徐鑄老在扉頁前言上的幾段話,以志懷念之情:
“自己雖‘年方七五’,畢竟記憶力日益衰退了,如果經再三考慮,訂出計劃后才系統動筆,怕時間‘稍縱即逝’有些應該‘留’下的史料,因此要白白地‘帶’走了。近年來,不是號召對老同志要‘搶救’史料嗎?我這是抓緊時間,自我‘搶救’。”
“這次試寫《杜月笙正傳》,不免有些膽怯,仿佛演慣小戲的人,一旦要排演整本的連臺大戲,感到功力夠不上,而且所寫的‘角色’,是這樣復雜,臉譜色彩又這么陰暗,牽涉面似乎又很廣,如何寫得近似而不失真呢?”
“報社和出版社朋友們的幫助,是成書的主因。特別是吳紀椿同志,從選題到整理,他是一直和我一起操心、流汗的。”
《杜月笙正傳》出版若干年后,杜月笙的長子杜維藩從臺灣到上海來。他在杜維翰家約見幾位老同學。我二姐夫李修明曾在山海關路育才中學與他做過同學,應約去了。二姐夫后來告訴我,杜維翰問他,為什么我沒再到他家去。二姐夫回答說是因為張朝杰曾被錯劃成右派,雖然已“平反”,他仍心有余悸,所以沒再去。杜維翰表示能理解。
又若干年后,有關杜月笙的書已充斥書市。我看過兩部。書中有些情況,我很疑惑,想去問問杜維翰,后得知他早已偕夫人到香港去了。我至今一想到此事仍感到非常遺憾。

作者1926年與哥哥姐姐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