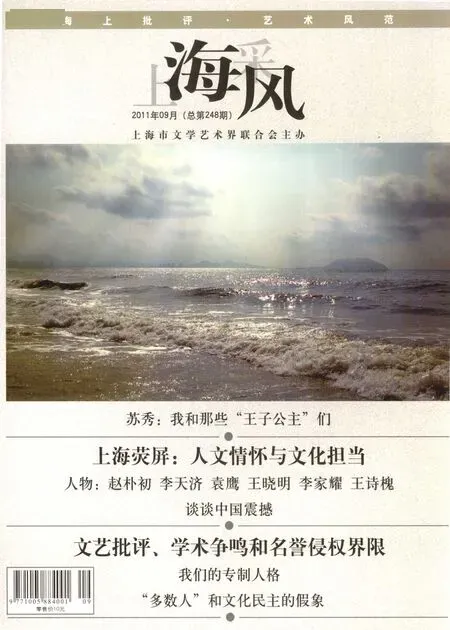趙樸初:翰墨永留香
文/宋連庠

1991年,本文作者與趙樸初合影(陳邦織攝)

趙樸初贈送本文作者的墨跡
春宵寂寂,在晶瑩臺燈下,賞讀上海古籍出版社面世的《趙樸初韻文集》,書中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均為我所喜愛,其中尤其是一首題為《辛未夏,奉酬陳蓮濤先生惠贈(貓蝶圖)》的五古,讓我一邊吟誦,一邊又憶起辛未1991年夏,在京華趙府的“無盡意齋”與趙樸老歡晤時的難忘情景來。
辛未夏,我杏壇賦退,解羈一身輕,便趁游京華之便,打算先拜訪心儀已久的佛學與詩詞曲書大家趙樸初先生。晉京前,特遵照鄧偉志老師的主意,求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學者陳邦炎(字蘊之,樸老夫人陳邦織的胞弟)先生給樸老的親筆信,內容主要介紹我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同時說明繪贈樸老的《貓蝶圖》的“江南貓王”陳蓮濤老人(1901-1994),系上海文史館館員,乃曾精繪《白貓黑貓圖》送給鄧小平先生受到稱贊的那位90高齡的佛門居士,以便我面晤樸老。
記得那天是1991年7月28日,一清早,我披著雨絲,拎著小包,前往北京西城東絨線胡同樸老寓所。因與樸老素昧平生,事先又未約定,也不知此訪能否相晤,并求得這位“一代書圣”的墨寶。也許是三生有緣,那天正值星期天休假日,樸老正在他的“無盡意齋”中,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言事,當他展閱了邦炎弟的信札后,遂即出齋,立于綠樹掩映的四合院北屋階前,笑容可掬地熱情迎客。樸老丁未1907年生,屬羊,當時已85歲耄齡,卻仍精神矍鑠,步履輕捷。我隨樸老入室,一起落坐于沙發,但見樸老神清氣爽,容顏白皙,貌慈祥如菩薩低眉,談風健而氣韻十足,不由得心中慶幸,樸老頤齡可期也!
秀才人情紙一張
我這個年逾花甲的后生,奉贈樸老雅禮兩件:一是90歲的“江南貓王”精繪的《貓蝶圖》(諧音耄耋圖)一幅,再就是我參與編撰的《贈言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一冊。
樸老先展畫細賞,但見幅間老花貓與二彩蝶嬉戲栩栩如生,妙趣盎然,不禁連聲笑贊: “畫得好,畫得好!90歲的人了,真是不容易呀!”當樸老聞悉蓮翁也為佛門居士,與滬上明旸、真禪、光德等大和尚均為好友,而且不論滬上的“龍華”、“靜安”等古寺還是寧波的“天童”、“阿育王”等禪林,均懸有蓮翁敬繪的佛像或題書的楹聯時,不覺心有靈犀,倍感親切。旋又信手翻閱了《贈言詞典》,說:“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這書好,很有用,我要經常翻翻。”
我向樸老轉達王元化(1920-2008)與夫人張可對他的問候。樸老說:“王元化很有學問。”我又轉告: “王老師所以久未寫信給您,一是擔心您每信必回,累著了您,于心不忍。再則是為了避騙字之嫌。”樸老聽罷哈哈大笑。事實也確如此。我曾在王元化先生寓所,拜讀了已裱成長卷的樸老書信多頁,均為毛筆直書。其信情意謙誠而富含哲理,其書鐵畫銀鉤而剛柔相濟。一向頂真的樸老,寫信也一絲不茍。為了及時回雁,不少信寫于深夜或書于病中,這就難怪王元化要“于心不忍”了!
意趣相諧訴肺腑
緣于樸老平易隨和,因而在一見如故的溫馨里,我不覺直訴肺腑;“文革”前夕,我曾偕莘莘學子賞讀過樸老的名曲《某公三哭》,還因朗誦該曲而榮獲“第八屆上海普通話教學觀摩一等獎”,然而沒料到,“文革”中卻因之被誣作“為修正主義招魂”,遭到大字報的圍攻,而掛上了“牛鬼蛇神”的“黑牌子”,吃了不少苦頭。樸老聽罷,不覺啞然失笑而感慨萬千。樸老說:“《某公三哭》一曲,我也很喜歡。原來這三首散曲的題目,分別為《尼哭尼》、《尼又哭尼》和《尼哭自己》。后來毛澤東讀了,就用鉛筆在《尼哭自己》一題上,改作了《某公自哭》,這樣在正式發表時就成了《某公三哭:哭西尼·哭東尼·哭自己》了。”我又欣幸地告樸老,“四兇”翦滅后,人心大快!我重返教壇和學員們一道,曾賞讀樸老的《反聽曲》(“聽話要反聽,魔怪現原形”)與懷念周總理的《金縷曲》(“轉瞬周年矣”)。樸老聞之,瞬目揚眉,如遇知音。
談及歇浦人士,樸老不覺神馳遐想,他請我回滬后代向古建筑園林詩書畫大家“梓翁”陳從周教授問好,這使我憶起從周先生書齋“梓室”之北壁,懸有樸老丙辰1976年8月,為“奉酬”從周先生惠贈“墨竹”而撰寫并書的一首七古:“壁上風來聲簌簌,數竿瀟灑遺塵俗。多能真見梓人才,自是胸中有成竹,不寫盲師寫此君,虛心勁節似同倫。因緣明月三生石,慚愧真堂作記人!”此詩之誕生還有一段佳話。1963年6月,為紀念鑒真大和尚入寂二十周甲(共1200年)陳從周曾應邀赴揚州,協助前輩建筑名師梁思成設計“盲師”鑒真和尚紀念堂前之紀念碑,而碑文則為趙樸初以紀念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謹撰并書的,故詩中有句云:“因緣明月三生石,慚愧(自謙語)真堂(鑒真紀念堂)作記人。”其書格調高雅,凝重中透溢清逸之氣,“梓翁”心甚寶之。
詩書只把結緣看
正歡敘間,邦織夫人冒雨購物歸來,看了邦炎弟手書后,便詢問滬上友好情景,不禁喜形于色,言談十分懇切。邦織老師雖說已年過古稀,卻思維睿敏,渾身充溢著青春的活力,還熱情地半跪著為樸老和我攝影留念。
時近晌午,因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樸老下午還有活動,我便起身告辭,相約以后上海再見。握別前,我從包里取出冊頁,請求樸老贈書一幅,大師慨然俯允。
兩天后,我去取字。樸老因外事交往不在家,其秘書宗家順君交我墨寶兩件,又香茶一袋,請我轉交邦炎先生。字幅一幅是奉酬自號貓癡的蓮濤先生的一首五言詩:“九十有童心,猶耽貓蝶戲。丹青拜嘉惠,掛壁增春氣。平等視冤親,待登歡喜地。號癡良非癡,畫中無盡意。”
贈我的兩小幅,一是宋代王安石的《歸依贊》:“歸依佛,彈指越三祗,愿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又書云:“—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 連庠同志留念 辛未夏樸初(章)。”其書勁秀超逸,別具神韻,字里行間的佛學禪意,我略悟數分:“諸佛菩薩”離不開眾生之源;凡大智大德者,必懷悲天憫人之善心。若真能心甘樂意并不辭艱險地為“眾生”謀福益,作奉獻,則定能“修成正果”。
流光如馳,一晃20年過去,樸老駕鶴西歸,也已11個春秋。今宵又于臺燈下,品賞哲人的墨跡,仿佛又添感悟。正是:寄意詩書翰墨緣,慈悲禪意記心間。赤誠播灑真善美,福樂祥和滿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