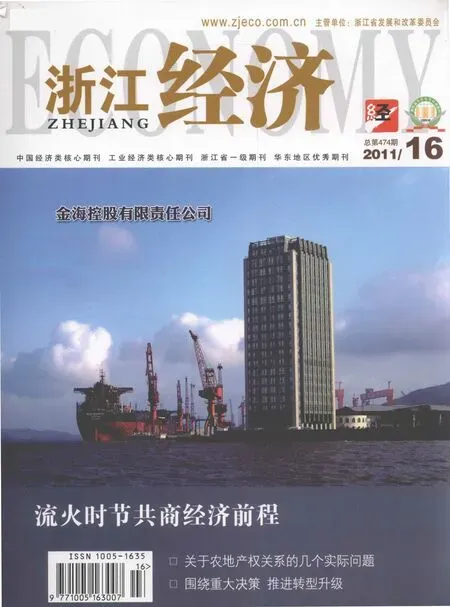地理空間的“本底參數”
地理空間的“本底參數”

卓勇良,1955年生,畢業于原杭州大學,現任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1980年進入浙江省政府調研室工作,歷任省發展研究中心副處長、新疆自治區體改委主任助理以及省體改辦改革與發展研究所所長。1996-1997年在日本進修。長期從事浙江經濟研究,主持和執筆省內多個重大課題研究,多次獲省政府科技進步、優秀社科成果,以及省委省政府黨政系統調研獎等獎項。
高密度均質化空間是浙江城市化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本底參數”,使得浙江城市化進程和行為方式具有相當大的獨特性
1997年11月,我參加原計經委在金華召開的一個城市化會議,提出了空間均質化概念。意思是浙江由于人口密度較高,各地均有較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形成了均質化的地理空間結構。由于空間均質化是由人口高密度導致的,所以又可以提出“高密度均質化空間”這樣的概念。
人口密度較高形成三個重要的客觀效應,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是各地均有較好的勞動力供給條件;二是各地均有較好的消費需求條件;三是各地均有較方便的交通條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篇第三章指出,分工受到市場范圍限制,“有些業務,那怕是最普通的業務,也只能在大都市經營。”而在高密度均質化空間下,較小范圍也能形成規模經濟,這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幾乎每縣都有小啤酒廠這樣的企業的經濟學原因。
為了弄清浙江地理空間的確切情況,我去年做了一個有關省份的宜居空間密度比較。這是因為地理空間存在著山區丘陵和水面的多樣化結構,相同國土面積的宜居程度差異很大,只有去掉水面面積,同時對丘陵山區進行系數化處理,才能得到同質化、可比較的地理空間數據。
分析結果表明,浙江宜居空間人口及城鎮密度,均遙居全國首位。1980年,浙江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間人口904人,居全國第一;第二位的是江蘇,為789人;第三位的是山東,只有672人。人口密度又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各地城鎮密度,2009年,浙江宜居空間城鎮密度居全國第一,每萬平方公里有城市8.0個、鎮177個。而第三位的江蘇,每萬平方公里只有5.3個城市,129個鎮。
所以,在浙江城市化進程中,高密度均質化空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本底參數”,使得浙江城市化進程和行為方式具有相當大的獨特性。“本底參數”這個詞主要用于理工科方面,如天文學指天然射線的照射為“本底輻射”,意思是未經人類行為影響下的輻射水平。而我提出這一概念,就是要突出強調浙江地理空間客觀特征的獨特性,以及對于浙江城市化的決定性作用。
這里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使得浙江城市化形成了從分散化走向集中化的軌跡,或者說是形成了以分散化為基礎的集中化過程。
長期來對浙江經濟發展的指責都逃不了一個“散”字,這真的是天大的“冤假錯案”。浙江活力的奧秘,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在于這個“散”字。浙江發展快的一個重要因素,無非就是創業主體眾多,而這些創業主體分布于浙江大地的角角落落。當年沒有要素流動一說,能人們只能“就地鬧革命”。浙江多半的角角落落都具有較好投資環境,早期創業成功率較高。與此同時,得益于前期的所謂分散化發展,使得后期具有了一大批集聚發展的內核。
說到這里,我們得建立一個“果園模型”。現假定基期年有100個果園,每個果園只種一棵果樹,形成典型的分散化。若干年之后的報告年,一部分果園由于規模擴大,相距較近,相互粘連,數個合為一個。這樣,果園總數有所減少,果樹總數增加到一萬多棵,對此,我們或可稱之為集中化。這樣,前期的分散化,成了后期集中化的“革命種子”。
千百萬個創業積極性蘊藏于千百萬個人的心中,千百萬個民營企業分布于千百萬個村落之中。家鄉是改革開放初期創業者們創業成功的“大地之母”,沒有浙江地理空間“本底參數”支撐,也就沒有浙江如此眾多的企業主體。
“分散化”是從計劃走向市場,經濟起步時期經歷的階段性現象。歷經30余年發展,一部分村落原地轉變為城鎮,其中一部分逐漸成為大中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有一部分村落的工業經過市場經濟“清道夫”作用而淘汰,成為高度都市化的鄉村社區。今日浙江的多數鄉村,傳統“三農”幾近絕跡,這是高密度均質化空間格局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