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注與悲憫中的思考與期盼——隋榮小說創作概觀
■ 楊鐵鋼
隋榮,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練筆,90年代初即發表作品。總計創作數百萬言,面世作品幾十篇(部),多篇多次獲省部級獎勵。由此,使他成為大慶油田一位較有成就和影響的作家。近日,筆者集中閱讀了隋榮自2003年至2010年間發表的作品共十三篇,計短篇小說三篇,中篇小說十篇,據此,談談對他以中篇為主的小說創作特點形成的幾點感悟。
從表現的生活內容領域——題材上看,隋榮上述十三篇小說涉及到了三個方面:《懸羊》 (中篇),反映學校教育的內容;《大舅一家》 (中篇),表現的是城市下崗人員生活的艱難;其余十一篇作品的故事情節都發生在油田,直接或間接地與石油生產、石油工人的生活有關。從中,我們又獲得了隋榮小說創作在題材表現上的特點。
“題材,屬文學作品的內容范疇。而文學作品的內容除了題材而外,還有情節(故事、沖突)、主題兩個要素,三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情節——題材——主題。
用語言表述就是:情節是題材的表象形式;主題是題材的內在意涵;題材是情節和主題的中介載體。由此可知:對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的創作僅從題材一個維度進行劃分,是難以全面、深刻、準確地認識和把握其創作特色和個性的。正確的做法應是將情節——題材——主題三者、尤其是題材——主題兩者緊密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的分析體認”(筆者《追求與突破——楊利民戲劇文學創作簡論》)。如果我們將“情節——題材——主題三者、尤其是題材——主題兩者緊密結合起來”,對隋榮的小說“進行綜合的分析體認”,就會得出這樣的觀感:隋榮以平凡的甚至是細瑣的故事和情節,多塑造女性的形象,揭示人性的主題,表現社會的問題,以此顯現出他對小人物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悲憫,以及他對整個社會、人生的思考與期盼。也因此,使我們在他的作品中時時會體味到一種隱隱的憂思與淡淡的感傷。
女性形象的塑造。隋榮幾乎每篇作品都有女性形象的存在,且大多數以女性形象為核心。統觀這些女性形象大體可分為二大類五小種。
第一類是勞動型女性,包括二小種:一是會戰時期的家屬工,如秋妹(《饑餓的薩爾圖草原》)、影(《與狼同行》、《野狼》);二是隨遷和招工進來的油田家屬工,如五月(《五月》)、淑英(《淑英的愛情》)、盧花(《盧花》)。
第二類是知識型女性,包括三小種:一是具有極左傾向的政治女性,如肖紅(《盧花》);二是嚴肅的工作者,如林惠(《沙塵暴》)、楊妮(《我把生命獻給你》);三是濫情的游戲者,如黎娜、王風(《我把生命獻給你》)、劉雯雯、劉丹、菲菲(《和太陽有約》)等。
無論是作家對形象的把握與塑造,還是形象自身所具有的品格、所體現出的價值觀,都以第一類的女性形象為豐滿、成功,生動、感人。
《饑餓的薩爾圖草原》中的秋妹,在會戰之初就隨丈夫從青海油田轉戰來到大慶油田,又在會戰最艱苦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因事故失去了丈夫。憑借偶遇的“緣分”,她在從軍隊轉業來到油田的純樸、厚道,“干活舍得下力氣,又善于體貼人”的田螺身上,體會到了一種與前夫的“直爽、專注和粗野”不同的感情——“親切、摯愛的柔情”,由此使他們很快結合,并在困難的年代里、艱苦的環境中、沉重的工作壓力下,相親相愛,相濡以沫。但最終田螺為了給秋妹和孩子節省兩個土豆而誤食斷腸草中毒致死。個體的能力與情愛在社會、自然的災害面前顯得既難能可貴但又何其渺小無力。“背著一袋苞米,拖著笨拙的身體朝草原深處走去,有一個小孩牽著她的衣角跟在后面”這一作品結尾,在讀者的心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同時也使今天的人們再一次深切地感知到了會戰家屬們曾經的苦難與付出的犧牲。
五月(《五月》)、淑英(《淑英的愛情》)、盧花(《盧花》)三個人,是在會戰之后,來到油田的。她們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歷:都是在農村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出生長大,都是為了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或隨丈夫遷入油田,如五月;或下嫁于人投奔而來,如淑英;或通過招工渠道進入油田,如盧花。她們的生活環境與工作處境也大體相近:日子過得都比較艱難,工作都很勞累辛苦。她們有著相同、相近的性格與理想:都賢惠、樸實、勤快、要強、善良;都期盼夫妻恩愛、家庭和睦、生活富足。她們與老一代會戰家屬們如秋妹的最大不同是:老一代更多地體現為被動地“受”——接受、承受自然、社會、家庭帶給他們的種種困苦、磨難,即使有所努力、抗爭,也顯得微弱甚至無效,所以在她們身上更多地體現出了忍韌的品格特質;而五月她們這一代則更多地表現出的是主動地“求”:一方面接受、承受生活與工作帶給她們的苦痛、壓力,一方面也在不失時機、甚至是尋找時機、創造條件做著抗爭的種種努力,因此,她們的結局也就大不同于上一代。形成這一局面的原因當然在客觀、主觀兩個方面。從客觀方面說,轉入大規模建設時期的油田,在自然、社會、人文條件上都日益優于會戰時期,因此,這就為人的生存提供了越來越寬松的選擇機會和發展的可能。
五月以愛心與苦干,支撐起家庭的天,使丈夫因有她的衷愛而安心于外面的工作,使女兒因享她的慈愛而各得其所,使婆母、姑、叔因獲她的關愛而和諧共處。淑英不滿足于家屬管理站的單調工作,而抓住私人煉油廠被查封的機會,自我做主,買下房子辦起豬場,全力排除只把她當作“滿足欲望的享樂瀉憤的女人”的丈夫對她生活、事業的干擾,策略而有效地抗拒了心懷不軌的食堂管理員老王對她的騷擾。她不肯在命運面前低頭,“我不信命,我不甘心,不甘”,“她知道眼淚是改變不了自己命運的,只有用自己的行動去抗爭,去找回那失去的生活”,她以她的實際行動和“不摻假”的摯愛真情贏得了大樹的愛情,最終又以無私的大愛成全了大樹與前妻的破鏡重圓。盧花憑借踏實的工作和善良的心地,在人事紛雜的環境中看破了肖紅的趨時,小木匠的委瑣,王長鎖的正直,因此與肖紅保持距離,對小木匠多有防范,對王長鎖相親相戀,雖因此遭肖紅的制裁、小木匠的傷害,但終于贏得了王長鎖的真愛。從以上三個人的不同人生結局中,我們完全可以認同這樣的一個社會人生法則:即使在同樣的客觀環境下,不同的人也會呈現出不同的人生樣態,而這則主要取決于個體素質品格的差異。五月、淑英、盧花三個人都具備賢惠、樸實、勤快、要強、善良的美德,但又各具傾向。具體而言:五月柔韌善良,淑英精干堅強,盧花柔中有剛。正是如上的相同的客觀條件與如此不同的主觀差異的綜合作用,才決定形成了五月、淑英、盧花三個人各自不同的人生軌跡和結局。隋榮小說創作中如上女性形象塑造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表現出了社會生活的真實性,呈現出了人物性格、命運的多樣性,揭示出了蘊涵于社會與人生深層次的規律性。
人性主題的揭示。客觀地說,人與一般動物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聯系表現在人同其它動物一樣,都是自然之子,因此有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學說的誕生,和稱人為裸猿的別名的出現。但人又的確不同于一般的動物,所以才有“萬物之靈長”的美譽,和人性理論的界定與創立。一般意義上的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本性,即人之為人的必不可少的品性。但所有這些都是書面或口頭的理論與言說,從人的實際生活表現上看,人與一般動物、獸性與人性的聯系與區別的確復雜難辨。也正因此,才成為以表現人與人生為己任的作家及其創作所關注的永恒主題。在此方面,隋榮也做出了他的努力和貢獻,其標志就是《與狼同行》、《野狼》兩個短篇的創作。
《與狼同行》、《野狼》是兩篇同題作品,《野狼》是對《與狼同行》的擴寫,寫的都是從部隊轉業到油田工作的馬源與薛冬的故事。在戰爭年代,二人是生死與共的弟兄、英雄,解放四平、抗美援朝,二人都立下過赫赫戰功,來到油田又同在筑路大隊一起打拼。不同也僅在于馬源是大隊長,在《與狼同行》中,馬源有家室妻兒,薛冬痛失妻子暫時獨身。馬源有著許多美好的人性:勇敢無畏,富有愛心,事業心強,從不服輸,既有男人的豪爽大度,又不乏丈夫、父親的恩愛柔情。但在馬源的身上又的確存在著非人性的動物式的本能。在《與狼同行》中,他強行占有妻妹鳳,而后又將鳳轉嫁給薛冬。前者堪稱亂倫,后者無疑是欺騙。無論何者,都有背人性。隋榮對他筆下的人物多懷理解和同情甚至寬容的態度,但他少見地對馬源不能原諒,其表現就是他決心將《與狼同行》擴寫為《野狼》,讓薛冬在水災中喪生的妻子秀復活,安排她帶著受水災刺激留下的“時而清醒時而糊涂”的后遺癥,不遠數千里,拄著棍子找到油田與薛冬劫后重逢。然而就是對薛冬這樣的生死與共的戰友、弟兄,對秀這樣的大難不死,身有疾患的戰友之妻,馬源仍不放過,趁其不清醒時冒充薛冬占有她。隋榮對馬源的態度最決絕地表現在《野狼》結尾的設計上:通過馬源遺留在薛冬家的煙嘴,薛冬明白了事實的真相,與馬源對決:
薛冬瞧準機會,飛起一腳,踢在馬源的襠部,馬源大叫一聲,跪倒在地,昏了過去。馬源成了廢人。
馬源受到了懲處,也許有人會對他受懲處的形式持有異議,但對他受到懲處的必然結局凡堅守人性尊嚴的人們都應拍手稱快。這也正是《野狼》優于《與狼同行》之處,也是隋榮擴寫的成功處。至此,我們也就理解了作品中的人與狼的搏斗的內容有著雙重的意義:顯層次上,它構成了真實、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隱層次上,它象征著人性與獸性的激烈較量。
在說過了馬源之后,我們還應提及一個人物,他和馬源存在著相同的人性缺失,他就是《淑英的愛情》中淑英的丈夫德才。淑英為什么果決地離開丈夫德才?就因為德才身上存有太多遠離人性的本能性的品質,他把食、性、玩、樂的觀能享受當作其人生的一切。在他的眼里,淑英“只是個女人,一個隨時喚來喚去的女人,一個供他使喚的滿足欲望的享樂泄憤的女人”,他名為德才,實則無德無才,由此才使淑英的心“由熱變涼”。相反,大樹“敬重她,把她看作是女人中一個完美無缺的圣潔勤勞的女人”,而淑英也從大樹那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讓人顫栗的刻骨銘心的感情”。可以說,他們的結合,是美好人性戰勝非人性的勝利,因此,作為讀者的我們也為此感到無比的欣慰。
社會問題的表現。在社會生活中本來屬常態的事物、內容、現象,一旦成為人們所關注、困惑、難解的事,就可稱為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需要政治家們正視與解決,也需要作家們反映與表現。是否具備這樣的態度與作為,是檢驗政治家、作家責任感與使命感高低、強弱的重要尺度。隋榮以他的創作實績證明了他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他關注被稱為涉及國人最多、最直接影響個人、家庭、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最大社會問題——教育的現狀與發展,因此寫出了《懸羊》。中學生曲琨,在家里,很少見到父母,因為他們都在忙著賺錢。他從他們那里除了得到金錢之外再沒有什么,而他的父母認為這恰恰是他們所能給予兒子的全部——愛。在學校,曲琨同樣過得不快活:一年的課程半年講完,曲琨跟不上,因此被老師稱為笨孩子,也因此常遭老師的奚落、同學的恥笑。所以他厭學,他逃學,他逃進網吧、餐館,經歷著許多不該經歷的人與事,最后他逃向遠方。作品以曲琨的一個夢蘊涵和揭示了主題:許許多多像曲琨一樣的中、小學生生活、學習于“像那懸羊,攀緣于峭壁之上,引吭高歌,夜間將角掛在樹杈上,懸角而眠”的惡劣危險的境地。解救他們于“倒懸”,真的是刻不容緩的社會大問題!
隋榮通過對《大舅一家》三個表哥及一個表嫂下崗經歷及艱難生活處境的展示,提出了如何關注下崗職工,怎樣幫助他們解決再就業,提高生活水平的問題。作品難能可貴的是通過大表哥順子、三表嫂英子的形象塑造,在真實、生動地表現他們經歷的曲折、艱難的同時,形象、具體地揭示出了他們下崗不拋棄志氣、貧窮不貶損品格的美好道德情操:順子的真誠率直、慷慨大義、扶危濟困,英子的溫順柔情、善良體貼、通情達理,給這日漸冰冷的物欲橫流的社會充填了人性的溫熱,更向急功近利、忘乎所以的人們做出了回歸人性、理性的導航。
作為社會問題,如果說教育的現狀是影響普遍、深遠的問題,下崗職工的生存與再就業是現實而具體的問題,那么,官場的風氣與腐敗則是最深刻、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作家,隋榮當然不會忽視對官場腐敗的透視與表現,只不過他將自己的透視與表現進行得比較含蓄與蘊籍,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真實與深刻。這就要說到他的兩部中篇小說《沙塵暴》和《我把生命獻給你》了。
邵礦長的一次體檢誤判,在全礦乃至全廠引起了一場《沙塵暴》:曹副礦長內外聯絡、疏通,廠綜合辦秘書楊臣出謀劃策、通風報信,特別是性格多疑、清高、內向的礦秘書張廣利時憂時喜、患得患失。正因為如此的人心伏動,各懷其志,而導致在自然的沙塵暴襲來時,將住院的邵礦長的叮囑忘到腦后而沉于酒局的曹副礦長未能就安全生產做出安排,只有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三隊女隊長林惠獨去現場巡查,遭到偷油者的圍攻致死。這引起了廠方的高度重視和嚴密徹查:醫院校正了體檢誤判,邵礦長無病出院;紀檢部門澄清了邵礦長將住院期間收受的禮金全部捐獻給了住院治療的解除勞動合同的女工海霞的事實;邵礦長被提升為廠長助理;韓思軍被聘為三礦礦長;曹副礦長、張秘書晉升的美夢破滅。一場人事的沙塵暴借助于一次自然的沙塵暴而塵埃落定,雖不免有幾分巧合甚至滑稽,但它確能促使人們進行深度的思考與認識。
我們完全可以把《我把生命獻給你》中的陳曉銘視為《沙塵暴》中張秘書的再現和繼續。二人都是秘書,都有著強烈的進取欲望,但在現實中又都不如意。陳曉銘深以自己的低微出身和缺少關系靠山為苦,雖然憑著好記性博得了李廠長的重用,參加工作僅半個月就被從基層實習崗調進了廠辦公室。不久,又因他處事機警,避免了一次集體上訪事件,被調到秘書崗位上負責寫材料。但盡管如此,他仍要受父親是副廠長、性情孤傲的女干事王風的輕視;他要遭同事也是競爭對手唐炎的陷害;他必須接受自己已被確定為廠宣傳部副部長第一候選人但結果是第二名被任命的事實打擊。當然,免不了痛苦,而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痛苦向大學的同學,現在的同事、妻子楊妮述說:
“我不服氣,我不是官欲極強的人,也不是心胸狹隘的人,對那些年富力強,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我是佩服的,我也希望能把權力交給這樣的人,這樣我們的企業才有希望,可要是把權力交給像楊副部長這樣的投機分子,我是不甘心的。”
人在痛苦的時候也是最需要撫慰因而也是最容易出錯的時候。陳曉銘沒有逃出這一規律的制約:身為公司副總經理之女的二礦副礦長黎娜找了上來,安慰、誘惑、照顧,使他失去了自控而被掌控。結合、懷孕、生產、離婚、再結婚。最終的結果是三個月后他被提拔為廠辦副主任,很快又升為主任,還有岳父調他去六廠任副廠長的允諾。而深愛著他的楊妮卻被調到遠離市區處于荒涼草原上的九礦,并在一次撲救野火中犧牲。
《沙塵暴》中張秘書的處境為我們掀開了現實官場黑幕的一角;《我把生命獻給你》中陳曉銘的經歷則為世人將現實官場的黑幕大大地拉開了,雖然仍不是全部。但僅此,也足可以使人們對今天官場生態有所認知,對掙扎其中的小人物有所了解和理解:
命運總是在捉弄生活在世間的小人物,使他們脫離正常的生活軌跡,為滿足自己的私欲出賣情感出賣肉體出賣靈魂。
這是社會的不良和不良的人生的真實寫照。改變的必要和改造的可能不言而明,但這必須要全體國人、尤其是執政黨、各級官員做艱苦而長期的努力。隋榮的努力與貢獻就是對這一重大而深刻的社會問題進行了真實而藝術的表達。
如果以創作時間為序對所見的隋榮上述13篇作品進行整體掃描,我們會比較清晰地看出他小說創作的變化軌跡。
從體裁上說,2005年以前,短篇、中篇齊頭并進;2005年之后,集中于中篇的創作。
從表現的內容上看,仍以2005年為界劃分為前后兩段。前段,無論短篇還是中篇,人物一般較少,關系也不復雜,故事情節比較集中簡練;后段,人物增多,隨之關系也相對復雜起來,故事情節也因之繁復起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和太陽有約》。從創作的效果來看,各有優劣:前段的作品多給人簡潔明快的感受,并且主要人物性格也較鮮明突出,如五月的柔韌善良,淑英的精干堅強。透過這樣的表達,讀者也能體會到作者對作品駕御的從容。后段作品固然顯見作家對內容豐富的創作追求,但因人物的增多與關系的復雜,致使人物淹沒于其中,除了《我把生命獻給你》中的陳曉銘、《盧花》中的盧花性格塑造較為鮮明突出外,其它幾部中篇作品的主要人物性格因受過多人物、關系、故事的牽制和遮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鮮明度。
從具體創作手法而論,我們也可見出隋榮獨具個性的追求與努力。《洼地》是他少見的正面表現石油工人生產生活的作品,采用第二人稱和意識流的手法,形成電影蒙泰奇的結構效果,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現了較為豐富的內容,同時也含蓄地表達了對石油工人所做出的奉獻和犧牲的欽敬與贊美的主題。對夢幻的大量和連續的運用,是隋榮小說創作所體現出的最突出的特色,它們或用以象征主題,如《懸羊》中曲琨夢見懸羊的情景;或用以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如《饑餓的薩爾圖草原》中秋妹在丈夫死后的夢境;或用以實現情節的跳越與結構的變換,如《五月》、《和太陽有約》、《我把生命獻給你》等篇中的有關表現。對夢幻的大量運用,說明了隋榮對人物心理的深度認知及對現代藝術成果的有效借鑒。
從語言方面關照隋榮的小說創作,我們不難體悟到他那自然、樸素、流暢的文字表達功力和風格的存在與形成。而這,也正是他取得日后創作新豐收的最基礎和現實的保證。在此,也希望隋榮在未來的創作中,在人物的性格塑造與故事情節的豐富二者關系的處理上多加留意,力求二者的辯證統一:既要人物(主要、核心人物)性格的鮮明,又要故事情節的豐富,而不是顧此失彼,或厚此薄彼、有此無彼。這是筆者個人的閱讀感想,也是一個具有共性意義的不低要求,更是隋榮完全能夠做到的事情,因此,我信心滿懷地相信并期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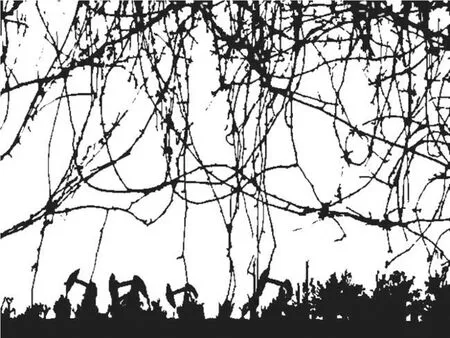
油 歌 版畫/王洪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