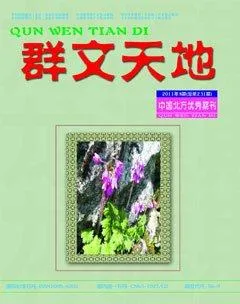在“現(xiàn)實(shí)”與“超現(xiàn)實(shí)”中穿梭
許多人認(rèn)為超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利用自動(dòng)寫(xiě)作總是創(chuàng)作些稀奇古怪甚至讓人費(fèi)解的東西,這一點(diǎn)也許并沒(méi)有錯(cuò),但這并不足以概括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自動(dòng)寫(xiě)作的所有特征,布勒東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用自動(dòng)寫(xiě)作手法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很少出現(xiàn)新的詞語(yǔ),并且違背語(yǔ)法規(guī)則的現(xiàn)象也不是特別的多見(jiàn),作為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文藝思潮的開(kāi)路人,布勒東的這一番話,值得我們對(duì)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自動(dòng)寫(xiě)作做更深一步的了解、探究。皮埃爾.勒韋爾迪被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視為自己的道路上的前輩人物,他的不少觀點(diǎn)被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所采用,勒韋爾迪認(rèn)為:“只是拼命地努力去寫(xiě)一些奇特得令人驚異的作品是徒勞無(wú)益的,獨(dú)特性是不帶痕跡的。它是自然而然地突然產(chǎn)生的,多半是在出乎你意料的一瞬間,你仿佛覺(jué)得你是在寫(xiě)一些最平常的隨時(shí)可能發(fā)生的事物,毫無(wú)奇妙之處。”①這段話可以補(bǔ)充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自動(dòng)寫(xiě)作的一個(gè)特征,我們往往將自動(dòng)寫(xiě)作歸于一種不可理喻的創(chuàng)作手法,避之唯恐不及,唯一的錯(cuò)誤在于我們對(duì)他了解得并不全面。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自動(dòng)寫(xiě)作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令人暈眩的東西。它的重要之處在于為讀者創(chuàng)造了一種由偶然性所引發(fā)的神奇,這種神奇并不完全脫離我們的審美經(jīng)驗(yàn),我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實(shí)際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轉(zhuǎn)換了我們的欣賞視角,創(chuàng)作視角,有些意象,我們?cè)隗@詫之余會(huì)覺(jué)得很有內(nèi)涵,仔細(xì)品位之后也有幾分合理之處,這些絕對(duì)不是在自動(dòng)寫(xiě)作過(guò)程中的創(chuàng)作主體憑空捏造出來(lái)的,而是像勒韋爾迪所說(shuō),是創(chuàng)作主義自然而然寫(xiě)出來(lái)的,雖然創(chuàng)作主體自己沒(méi)有意識(shí)到,但這就是他們平時(shí)的審美體驗(yàn)與思考的結(jié)果。
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在無(wú)意識(shí)自動(dòng)寫(xiě)作過(guò)程中,經(jīng)常創(chuàng)造出奇特的形象,布勒東認(rèn)為這種形象的產(chǎn)生來(lái)源于兩種事物的偶然組合,這種偶然組合超越了以往傳統(tǒng)的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它是非理性、無(wú)意識(shí)活動(dòng)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果,但是在布勒東看來(lái)這種偶然的相遇并不是創(chuàng)作主體隨意而為,表面的偶然性中包含著必然性“在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者看來(lái),主體與客體的契合雖然具有偶然的性質(zhì),但在這種看似偶然的現(xiàn)象背后,必定存在著某種起支配作用的客觀規(guī)律”②當(dāng)我們閱讀超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時(shí),我們往往對(duì)其中的形象不知所措,不少評(píng)論者認(rèn)為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在此陷入了“排斥感性認(rèn)識(shí)和理性認(rèn)識(shí)的認(rèn)識(shí)論和方法論”③的“神秘主義”中,但是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并不是一味地沉浸于自己靈魂世界中的一群空想家,安德烈.布勒東在他的《談話錄》中明確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客觀偶然性”的看法:“我覺(jué)得客觀偶然性(它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巧合的軌跡)構(gòu)成了問(wèn)題之問(wèn)題的焦點(diǎn)……這個(gè)問(wèn)題似乎只有這樣提出:那些人類精神只能將它們歸于某些獨(dú)立的因果系列的現(xiàn)象,是如何相遇直到融合在一起的(說(shuō)實(shí)話,這是很少見(jiàn)地)?由這種融合所產(chǎn)生的閃光雖然轉(zhuǎn)瞬即逝,可它們?yōu)槭裁磿?huì)這樣強(qiáng)烈?只有無(wú)知的人才會(huì)把這些歸納為神秘主義范疇的思考。”對(duì)于超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中那些看似神秘的描寫(xiě)與令人震撼的形象,我們可以借用布勒東的一句話來(lái)概括:“偶然性也許是外部必然性的表現(xiàn)形式,外部必然性在人的無(wú)意識(shí)當(dāng)中為自己開(kāi)辟道路”,這樣我們就把超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表現(xiàn)出的天馬行空的形象奇特性與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無(wú)意識(shí)自動(dòng)寫(xiě)作聯(lián)系起來(lái)了,在超現(xiàn)實(shí)主義那里,創(chuàng)作主體可以通過(guò)自身的無(wú)意識(shí)把握住事物的必然規(guī)律,正如波德萊爾所說(shuō):“長(zhǎng)久以來(lái),我都認(rèn)為詩(shī)人是最高的智慧者,是杰出的智慧,——并且認(rèn)為想象力是一切才能最科學(xué)的才能,因?yàn)橹挥兴哦闷毡榈南嗨菩曰蚰撤N神秘宗教所謂的應(yīng)和。”在超現(xiàn)實(shí)主義那里,無(wú)意識(shí)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想象力得到了同樣的重視,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認(rèn)為想象力可以將人帶到內(nèi)心深處最隱秘的地方,同時(shí),在連接人的內(nèi)心世界和外部客觀世界的過(guò)程中,想象力也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就如同象征主義,在想象力的巨大作用下,讓神奇的形象成為溝通意識(shí)與無(wú)意識(shí),內(nèi)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橋梁。
布勒東說(shuō):“馬克思主義說(shuō)改造社會(huì),蘭波說(shuō)改變生活,這在我看來(lái)都一樣”在布勒東看來(lái),這些改變都是以人為最終目的的。所以在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人被擺在了第一位,他力圖前所未有的使人獲得精神上的解放,使人從那種令人桎梏的理性教條主義中擺脫出來(lái)。猶如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為茹毛飲血的人類送來(lái)光明與溫暖,“這個(gè)世界(外部世界),我知道它存在于我之外,我從來(lái)沒(méi)有對(duì)它失去過(guò)信心。我并不像費(fèi)希特那樣,認(rèn)為這個(gè)世界是由我的自我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非我。當(dāng)我在汽車行駛的道路上東躲西閃的時(shí)候,我不可能檢驗(yàn)搶的功能是否完好,管他打著誰(shuí)呢,那怕是我自己,我甚至還會(huì)對(duì)這個(gè)世界致以最深切的敬意,我想這就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對(duì)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態(tài)度有一個(gè)明確的了解,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將很大一部分經(jīng)歷用于無(wú)意識(shí)自動(dòng)寫(xiě)作,并不能說(shuō)明,這一群作家完全沉浸于各自的狹隘精神世界中,特別是將人的無(wú)意識(shí)作為自己的最終創(chuàng)作目的,實(shí)際上,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張上比以往任何一個(gè)文學(xué)流派的創(chuàng)都更傾向于行動(dòng)。
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自動(dòng)寫(xiě)作有其自身的客觀性與現(xiàn)實(shí)性,從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無(wú)意識(shí)自動(dòng)寫(xiě)作過(guò)程中,我們看到了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破壞存在的平庸面貌,讓精神超出自己習(xí)以為常的視野,使其在意外面前感到錯(cuò)愕,這樣,它就能使精神隱約瞥見(jiàn)另外一個(gè)現(xiàn)實(shí),即超現(xiàn)實(shí)”。
注釋:
①王忠琪等譯《法國(guó)作家論文學(xué)》 三聯(lián)出版社,第136頁(yè),1984年。
②安德烈.布勒東著 袁俊生譯《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宣言》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 ,第54頁(yè),2010年。
③杜布萊西斯著 老高放譯《超現(xiàn)實(shí)主義》三聯(lián)書(shū)店,第162頁(yè),1988年。
(作者簡(jiǎn)介:趙東蕾,杭州師范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