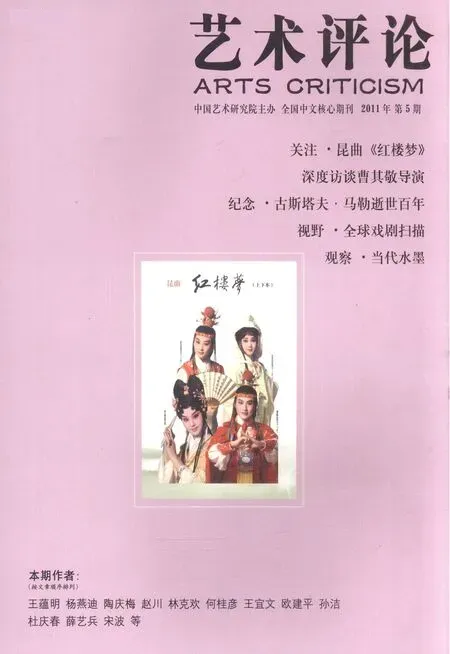現代陶藝不應摒棄實用性
齊 彪
現代陶藝不應摒棄實用性
齊 彪

日本前衛陶藝家八木一夫以其名作《薩姆薩氏的散步》而成為現代陶藝界的扛旗大將,人們對他的盛贊來自于“封住了用來插花的小管的口,使之完全拋棄了‘實用’觀念”和“把器身立了起來,使之脫離了‘器型’的困擾”。無論是有意或無意,這在其時被視作是一種創造:他用純藝術的觀念給了陶藝一個新的詮釋,為陶藝拓展了一個新的領域。然而這種意義一直以來被希望看到陶藝光明的人們善意地夸大并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只有非實用性的陶藝才是“進步的”、“現代的”陶藝,并以此作為區分傳統陶藝與現代陶藝的重要標志之一。事實上,完全摒棄實用性造型在創新與突破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種新的限制,因為它只能代表一個方向或類型,而不是唯一的選擇。而且這也許并非八木一夫的初衷。
八木一夫出生在陶瓷世家,理解傳統陶瓷的價值與意義,他的陶藝觀念很顯然來自對傳統的認識和對歐洲現代藝術的迷戀之間的沖撞,這在他的一次對記者的談話中可以說明:“新生事物與古典傳統結婚,是我的目標。在作品上如何將畢加索、克利的現代繪畫與日本的轆轤味道結合是我的工作。”[1]“走泥社”重要成員之一鈴木治的作品,有著濃厚的日本原始土器的意味,20世紀70年代以后則表現出了對中國傳統青白瓷的迷戀,預示了對傳統陶藝本位的回歸。八木一夫之子八木明的作品也主要是有明顯實用性傾向的青瓷器皿。八木一夫本人的作品也仍有器皿器型的出現,但并未封住口部。其它作品也多“具象”造型,其中有件作于1973年的《肖像》可與同時期的陶瓷雕塑《阿麗莎人形》歸為一類,只是臉部已被完全省去,剩下一塊平板。雖然觀念相同,卻未能如《薩姆薩氏的散步》般引起轟動。現在看來,“八木一夫現象”是現代陶藝發展過程中與西方現代藝術所宣揚的抽象表現精神暗合時被抽出放大的一個特例。其根源仍然是出于“反傳統”與“反現實”目的。
事實上,現代陶藝并不能也不應該排斥實用性,否則其將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一)使現代陶藝成了無源之水。眾所周知,陶藝起源于日常實用器物,并一直沿著實用的原則盡可能地做到與審美的完善結合。甚至到了觀賞性器物從實用性器物中完全地分離出來,前者也還是主要以后者為依托,用日本人高村豐周的話說,就是“借用實用品的形骸表達內心世界”。而且人們對于二者“兩善俱全”的要求不僅沒有降低反倒得到了加強。這一點不僅可以從歷史遺留下來的器物中得到驗證,也可以從人們日常對器物的習慣評論比如“好看又好用”的欣喜和“中看不中用”的遺憾中加以說明。而現在忽然間有個聲音說:“所有具有‘純藝術價值’的作品都是與實用無關的,哪怕是看起來像也將不被允許!”事實上藝術的“純與不純”、“現代不現代”從來都不是“實用不實用”能夠決定的,唯一的解釋只有:它似乎不太符合西方現代藝術的標準。
孤兒曾經也有過父母。孫悟空被藝術想象為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但他不是凡人。遠古神話中有兩兄妹繁衍人類大眾,女媧摶土造的人都不是具體的。最為大膽的想象也就是說生出一個肉球,剖之而生哪吒;或夢見與龍或蛇相交而生王侯。這說明事物都有著明確的來源,陶藝來源于實用性器物,那么現代陶藝無論怎么“現代”又怎么能夠否認其實用性呢?李硯祖先生《現代陶藝論綱》認為:“造型、裝飾的變化與豐富,是藝術的力量,也是陶藝生命力的一部分。因此,陶藝的實用性常在與這種藝術的價值和力量互為統一中得以實現,而所謂藝術性則又是建筑在實用屬性基礎上的,它們是一張紙的兩面,一個互為統一的集合體。這是傳統陶藝的內在性質,也是現代陶藝的內在屬性。有人認為陶藝是純精神化的,無實用可言,從而將有實用性的陶藝摒棄在現代陶藝之外。事實表明,這是一種狹隘的陶藝意識,僅以實用與否作為區別陶瓷與陶藝的準則既無理論上的說服力,在實踐上又行不通。”[2]
(二)突破“實用性”自身,而不是一種排斥或摒棄。在現代陶藝的創作中,由于實際的審美需要而忽視或完全忽略造型的實用性及其特征是正常的,如果樂意,創作者甚至可以永遠放棄器物的實用性特征并以此為自己的藝術風格,但他卻不能夠以此為標榜或表現出“現代陶藝就是要摒棄器物的實用性”這樣的論調來。正如一個決意要和家庭決裂的孩子,他可以完全斷絕與家庭的親情關系,但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否認與家庭的血緣關系,更不能對外宣稱“所有的正常孩子都是應該與家庭決裂的”。
對“實用性”的突破在古代的陶藝中常有,那是一種陶藝對自身的突破,而不是排斥和摒棄。最早可以上溯到實用器向禮器的轉變,在古代流傳的器物中,壺、瓶和樽也是較早與實用性相脫離的器物。較早時期的壺不像后來那樣有著把手與流嘴,而是如現在的壇和罐一般,只是頸部要更加明顯一些;有的和瓶很相近,而腹部要鼓出來一些。它們開始時都是盛酒或水的實用器物。如著名的玉壺春瓶、梅瓶等都是用來儲存酒的,后來新的器型多了,它們中的很多形制就被作為觀賞器物而專門被用以陳設了。明清以來,一般的富戶人家都設有博古架,上面絕大多數的器物陳設都有實用性特征,但它們確實是專門用來陳設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如高更“自畫像”式的人面杯,畢加索的女人體器皿雕塑,是“有用”而不用;明清民窯油罐被用作插花,彩繪戲文磚被裝在木架里面專門用來陳設,是“實用”的轉移。都是對“實用性”的突破。高更、畢加索的陶藝作品也具有“實用性”語言特征,至今看來仍然前衛和“現代”,也不再具有實用價值,但都早于八木一夫對于“實用性”的突破。
畢氏對器物實用性的突破從米羅的評語中也可得到證實:“陶器藝術是畢加索藝術中最富人間性的部分,他的創造突破了慣常的形態學。藝術家的熱情與火的神秘交融,使恒常不變的物質增加了無限的高貴性,是陶器傳統觀念的創新,瞬間的即興的行動,產生了永恒的價值,是他對人間意識進行藍色的思考與創造。”[3]米氏的闡述幾乎涵蓋了現代陶藝所有的現代品格,其中的“慣常的形態學”當然也包括“實用性”在內。其它更有一大批專注于傳統器物造型創新的現代陶藝家,尤以日本為著,誰也不能輕易地否認蘊含在他們作品之中的“現代性”。
現代陶藝重大的創新之一不是對“實用性”的排斥或摒棄,而是對“實用性”自身的突破。近年來出現的“生活陶藝”和“環境陶藝”即是依據人們不同的生活環境而劃分的,較早提出“生活陶藝”與“環境陶藝”概念并將其應用于教學研究與實踐的是中國陶藝名家朱樂耕教授,他不僅較早地對生活陶藝進行了成功嘗試,還以韓國首爾麥粒美術館、音樂廳墻體壁飾的設計與制作的成功案例而聞名。這說明現代陶藝不僅不能排斥“實用性”,而且還要發揚它,對其注入新的文化理念。如對于現代的生活來說,最理想的生活陶藝作品莫過于能夠在實用的同時,又有近距離的藝術感受。能夠使人們在“無意識”中融入藝術氛圍,這才是現代陶藝的真正的“現代”理念。如果盲目地否定“實用性”,豈不是說現代陶藝是“只許看不許摸”的藝術?
(三)限制了陶藝自身的豐富性。縱觀陶藝的發展,從無釉到各種色釉,從釉下刻劃花到釉下畫花,從青花釉里紅到釉上彩繪,陶藝的發展史也是其自身不斷豐富的歷史。但藝術的發展不像生物的發展一樣是進化式的,而是對藝術表現空間的不斷拓展。我們不能說現代陶藝就一定要比古代陶藝高級,也不能說今天的一件現代陶藝作品要比一件原始陶器更有藝術價值。真正進步的是科學,是新材料以及藝術的新形式,但不是藝術性。謝赫有云:“跡有巧拙,藝無古今。”藝術不會變味,人的主觀意識卻容易變質。不少人甚至認為,正是中國深厚和悠久的陶瓷傳統限制和阻礙了現代陶藝的發展,成了陶藝創新者沉重的負擔。我想這種“負擔”應該是來自于傳統陶藝參照下的難于超越,傳統陶藝的豐碑如神話中的“照妖鏡”一般令藝術的妖魔無法藏身,而對修道者卻能夠“鑒容”。 河清先生在《藝術的陰謀》中說:“我覺得,‘過去的影子’對于中國現在的藝術家不構成什么負擔,而‘未來的幻象’倒時時刻刻折磨著今天中國的藝術家。他們始終有著一種為‘未來’而創作的沉重使命感,始終擔心自己跟不上‘時代’。”[4]
現代陶藝正是以一種“前衛”的姿態為陶藝界增添了一道另類的景色,然而很難想象一旦陶藝中沒有了“器皿”的身影將是一個什么狀況。晶瑩剔透的玉潤質感沒有了,對稱和諧的形式韻味沒有了,撫摸玩賞的生活情趣沒有了,剩下的是一堆礦脈不明的石塊,銹跡斑斑的出土物,和廢塑料的任意擺放或切割?或許有聲音會說:“現代陶藝是抽象與表現的世界。”然而抽象包含著“形”的抽象與“意”的抽象,現代派聲稱要表達“個人情感”,傳統器型中的“天圓地方瓶”則表達了一個完整的宇宙觀,而“馬蹄飯杯”中的蓋、托、杯則揭示了天、地、人相和諧的宇宙哲學。“個人”較之于“宇宙”何止于滄海之于一粟?畢竟現代陶藝界中致力于器皿類研究的陶藝家不在少數,一些大藝術家如高更、畢加索和一些陶藝巨匠如日本的“人間國寶”都沒有放棄“實用性”藝術語言的運用。所以,對傳統陶藝“實用性”的摒棄,不僅違反了現代藝術所宣揚的“自由”主張,也限制了陶藝自身的豐富性。現代陶藝界如果少了“器皿”類陶藝家的參與,也必將顯得寂寞而空寥。
注釋:
[1]轉引自鄭寧:《日本陶藝》第253頁,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1年。
[2]李硯祖:《現代陶藝論綱》,載《中國藝術學研究-張道一教授七十華誕暨從教五十年文集》,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
[3]轉引自卜維勒編:《畢加索陶器藝術》,四川美術出版社,1990年。
[4]河清著:《藝術的陰謀》第323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責任編輯:曉晨
齊彪:景德鎮陶瓷學院陶瓷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