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文體的“立”與“破”:“新散文”文體探索力度
⊙劉軍[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散文文體的“立”與“破”:“新散文”文體探索力度
⊙劉軍[河南大學文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現代散文基本觀念的確立幾近百年,在其演化過程中,既有著外部因素的束縛,也有著來自內部的突圍。在文體拓展方面,發端于上世紀末的新散文,其探索的力度、方向極為突出,本文力圖對此次探索做出梳理,鉤沉出其得失。
散文文體新散文文體探索
散文作為“文類之母”和古典文學的“正宗”,在古代中國一度取得了極高的成就,與詩歌并舉,“詩文大國”的稱謂由此而產生。進入現代史后,在中西文化深度對接的背景之下,經過西方“essay”體與晚明小品文的相互植入,以及周作人、郁達夫、魯迅諸公的文體實踐與理論探討,現代散文觀念得以確立,并在文本創作上達到了另一個高度,成為新文學創立過程中最為成功的一個文學范式之一。
總括一下現代散文所建立的基本觀念,代表性的有三種,一是周作人的“美文”觀和“大閑適與小閑適”說;二是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中所提到的“個人的發見和表現的個性”;三是魯迅先生的“投槍和匕首”說。以上三種理論恰恰構建了現代散文文體的內在規定性,使現代散文的精神品格在三個向度上充分展開。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落潮和時局之變,上個世紀30年代后期,散文逐漸走向式微。與小說、詩歌等其他文體相比,無論是17年文學還是新時期文學的第一個十年中間,散文的沉寂有目共睹。建國之后的散文實踐,政治的、歷史的、時代的以及個人的因素導致了散文“范式化”的創作格局。“形散而神不散”的局促,卒章顯志的定型手法,“文眼”的設置,詩化的語言,都在某種程度上禁錮了散文的創造。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里,人們已經熟悉并接受了以前那些結構單一、主題單一、語言陳舊的散文,認為散文別無他途。
文體的單一化與模式化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散文喪失了最基本的自由精神和作為文學的想象力品格。“文體是對常規的偏離”,這是對文體的一種深刻認識,它強調了文體與個體的關系。而“常規”的一個潛在含義即一種對于所有個體的統一要求,一種無聲的對于差異的排斥和拒絕,這對于以個體性為生命的散文而言,是一種深重傷害。17年恰恰是一個崇尚常規的時期,當時群體意識的不自覺及國家抒情機制的建立制約著散文創作,作家們自覺地將各自不同的生命體驗納入統一的公共情感軌道,形成了“頌歌體”與“抒情體”這兩種特定的時代散文文體。問題的關鍵在于,17年文學的流弊一直持續到新時期文學開始的幾年,散文在取材、抒發情感、思維方式、表達方法、文體樣式等方面被人為地限定在一個狹小的范圍內,抒情散文扶搖直上成為散文的正宗,導致本該活躍和最有創造力的散文文體成為當代文學中最沉悶守舊的一部分,這使得散文文類的包容性與開放性以及散文內在精神的自由性受到嚴重的限制。而同一時期,小說、詩歌、戲劇這些文體在藝術思維和方法的創新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小說界的方法熱和觀念熱,詩歌界的朦朧詩運動,戲劇界的實驗話劇,皆顯示出強烈的實驗姿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散文界開始了認真的反思,首先是對17年散文尤其是三大家散文的總結和批判,林非和佘樹森等學者就此展開了系統的評述,比如佘樹森先生對17年散文三大塊結構的分析“第一塊:文章開頭,旨在引人入勝;第二塊:文章重心旨在使思想意境不斷開拓與升華;第三塊:文章結尾,旨在直接點出所載之‘道’,強化讀者的理解”①。“三大塊”結構作為17年散文的典范結構方式在此遭到有力的清算。其次是對泛濫的抒情文體的批判,作家孫梨、董鼎山等皆對此有過尖銳的批評,其中汪曾祺先生的觀點尤為鮮明,他在1988年為散文集《蒲橋集》作序時強調:“二三十年來的散文的一個特點,是過分重視抒情。……散文的天地本來很廣闊,因為強調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圍弄得狹窄了。過度抒情,不知節制,容易流于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②
散文文體的自我窄化,導致散文界中一些人甚至發出散文即將解體和消亡的悲觀論點,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許多人認為散文應在文體上、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有大的革新,必須對傳統散文固有的格套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和超越。散文家們對于散文創作的現狀終于有了深刻的不滿,開始大聲疾呼散文的“變革”。女作家斯妤在1992年談到散文革新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我認為新時期散文發展到今天,已經面臨著一個形和質的飛躍,無論是17年間形成的‘三家’模式,還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夠,甚至不能很好的、完全地反映當代人的思考、探索、焦慮、苦悶,傳達現代人的復雜情緒與豐富多變的心靈。散文必須在思想上、形式上都有大的新的突破,才能和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相稱,和這個時代日益豐富復雜的心靈相稱。”③因此,她認為散文家應該具有強烈的創造意識,不因循守舊,不墨守成規,廣采博收,從20世紀豐富絢爛的文學成果中汲取營養,立志在文體上、形式上、語言上創新拓展,創造出真正屬于當今時代的“新文體”和“新形式”。散文家張銳鋒從文學史的角度這樣認識散文革新的必然性:“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問題,一切都是正常的。以古代文學為例,詩從四言發展到七言,然后到長短句,不僅是一個字數變化的問題,它涉及到詩的一系列美學特點和內在結構的變化,我們必須看到,其中滲透了深刻的質變過程。散文也是如此。它也在變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呈現自己。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就意味著創造已經停止了,散文已經變成了只代表過去的木乃伊,我們今天談論散文也僅僅意味著談論過去。實際上,散文應該永遠是活著的東西,它不僅有過去,有現在,而且有未來。”④以上這段話語集中呼應了古典文學觀念中的“通變”之說。在幾次有關散文的研討會上,張銳鋒還多次強調,過去的散文與讀者之間存在著普遍的教育關系,而非審美關系,所以要改變傳統散文講道理的方式,重建其審美品質。而從創作上來考察,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批青年散文家就開始創作帶有先鋒意味的新潮散文,其文體探索集中在藝術手法的多元并舉,以及對他種如繪畫、音樂、建筑等藝術形式的兼容與借鑒方面。不過從陣容的角度來考察,本次散文探索的方陣中,如果把臺港散文家去除之后,大陸方面的參與者在數量上并不算太多,主要有祝勇、王開林、葦岸、張銳峰、馮秋子等作家。其實驗的成就也僅僅集中在三部編選的散文集中。而且,若從時間段上來審視的話,其持續的過程也僅僅集中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這幾年的光陰,所以無論從覆蓋面、影響的深度還是實踐成果來看,這一次新潮散文的崛起皆難以稱得上是一次大規模的散文革新運動,只能看作是散文變革的先聲。
上世紀90年代,隨著意識形態的松懈和淡化,市場經濟的高歌猛進,整個中國文學的思想文化語境比之以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散文迅速地由冷變熱,文化散文、大散文、學者散文、思想隨筆、女性散文、新散文等等爭相登場,建構了多元的閱讀空間和數量龐大的消費市場,這在文學不斷邊緣化與泛化的整體背景下,顯得尤為出眾,因此,有學者稱90年代是一個“散文時代”⑤。散文家韓小蕙形容這次散文熱為“太陽對著散文微笑”。
散文的繁榮持續至今大約有20個年頭,但仔細考量這次熱潮所發生的“場域”就會發現,并非是因散文文體的突破和散文理論的建樹有多么卓然之故,而是時代契機和散文話語策略調整之因素,使得散文這一文類切合了眾多讀者的胃口。這樣以來,散文表面的強化是以自身的弱化為代價換取而得來的,比如說,散文由原來的意識形態的整合與訓導走向了對大眾的迎合,由原來的僵硬姿態轉向了如今的深度軟化。散文經過多年的困頓之后終于有機會去除了上身的鐐銬,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它在今天又迅速被戴上了“市場化”這一鐐銬,這一現象確實值得深思。散文熱的另一面是散文的泛濫化,面對日益高漲的“文化化”與“世俗化”傾向,散文的原創力正走向萎縮,商品化與模式化再度擠壓了散文話語轉型的空間,正是在此種景況之下,“新散文”的出場也許能夠成為新時期散文實現話語突圍的絕佳機會。
“新散文”現象,發軔于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至今業已十幾個年頭,其先鋒性、探索性、實驗性逐漸得到散文界的注目和認可,當然也因其前衛姿態招致了一些學者的置疑。其代表作家有祝勇、張銳鋒、周曉楓、格致、寧肯、龐培、鐘鳴等,他們的反叛發軔于對過去散文的地位和寫作模式的不滿,試圖重新建構散文的審美品格,其探索方向主要集中在對傳統散文文體的沖毀、超越與重建之上,他們以特立獨行的話語方式和多向度的精神追求也許預示著一場較之詩歌小說遲來的文體革命。新散文的寫作者們不滿于新時期以來傳統散文這個“常量”給散文文體帶來的束縛和禁錮,著力于對“變量”的探索,把散文當作一種創造性的文本經營,而不僅僅是記事、傳達思想的工具。在藝術表現上新散文作家們呈現出自覺的開放姿態,銳意實驗,像詩歌和小說一樣不排斥任何可能的表現手段,并試圖建立自己的藝術品位。其探索姿態和先鋒意識,使散文有了更有力的表現手法和更廣闊的藝術空間。
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新散文”的出現并非偶然,它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藝術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創作潮流的延續和伸展。立足于90年代散文熱的大背景和思想文化界“去中心化”的社會基本語境,是散文界努力“恢復個性”的集中體現,在這一點上,也與五四散文傳統遙遙相應。在具體實踐中,他們致力于重新確立散文的話語秩序,在文本的敘述姿態和語言創新上走得很遠,某種程度上具有拓荒的文學史意義。并在多個層面上對傳統散文文體形成挑戰和沖破的局面,新散文諸作家有著自覺的文體探索意識,個別作家甚至走的非常遙遠。
散文文體自身的開放性與多元性,為新散文的文體探索奠定了理論基礎,而新的思想文化語境又為散文的求新求變提供了相應的社會基礎。新散文的文體探索體現在創作實踐中則是多層次的,具體表現在:其一,是跨文體寫作方式,新散文寫作兼容了小說、詩歌的質素,呈現出一種開放的姿態。這種寫作方式的敞開恰恰表征了散文自由寫作的本體特征;其二,是新散文在體制上的突破,眾多長篇散文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散文“短、小、輕”的弱小格局,提升了散文的氣象和境界。幾萬字甚至幾十萬字的散文作品在新散文寫作中集中登場,不僅跨度很大,更重要的是,題材方面也從個人情感處突圍開來,延伸到歷史、人文、記憶、集體敘事的疆域;其三,是消解了傳統散文的真實觀,融入想象與虛構的品格,使散文的表現力有進一步的拓展,文本內部的張力也得到擴大;其四,是對散文抒情的糾偏,調整了散文的描述方式,把敘述推到散文描寫的前臺,在敘述的推進上,新散文作家普遍采取了底層敘事的視角,讓寫作回到大地之上,用生活或歷史本身的復雜邏輯去構筑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重建了散文的審美個性;其五,是新散文采取了物象并置的結構方式,新散文文本在結構上的充分敞開,人們已很難用主題學的研究來探察文本,他們并置式的營構使散文在各個角度上向世界敞開,這無疑增加了散文在結構上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其六,是個人性話語秩序的建立,突出了散文文體對個體性的倚重,讓語言回到事物本身,致力于恢復散文話語的活力,沖破既有的散文語言的編碼秩序,借助隱喻手法充分發揮詞語的能指功能。并充分調動散文話語的內在感覺化,發掘語言的質感,追求語言的陌生化功能。總之,新散文文體探索對當代散文寫作形成了一次不小的沖擊,其鮮明的主體性色彩及新穎的散文文本的營構對舊有的散文觀念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戰,留給讀者和散文研究者很大的思考空間。
不過,新散文在文體探索的過程中也留下諸多問題,比如過度寫作、細節沉迷、為個性而個性、理論伸張過于單薄等。近幾年,學界關于以上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如何克服這些問題,這是新散文寫作在以后的創作實踐中必須解決的因素,也是新散文文體探索能否繼續深入的關鍵。
①佘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②汪曾祺:《汪曾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頁。
③斯妤:《散文需要新的思考、新的活力》,《散文百家》,1992年第7期。
④張銳鋒:《自白》,收《新散文九人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22頁。
⑤吳秉杰:《散文時代》,《當代文壇》,1997年第3期。
[1]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M].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2]佘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3]汪曾祺.汪曾祺散文選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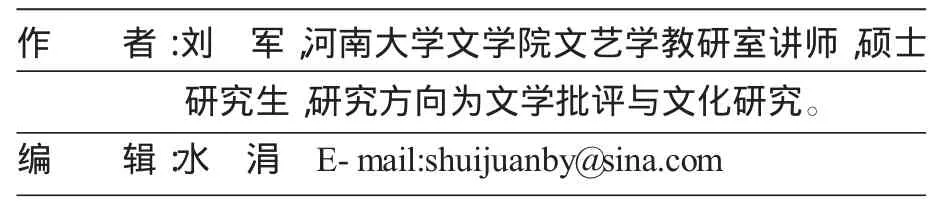
作者:劉軍,河南大學文學院文藝學教研室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編輯:水涓E-mail:shuijuanb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