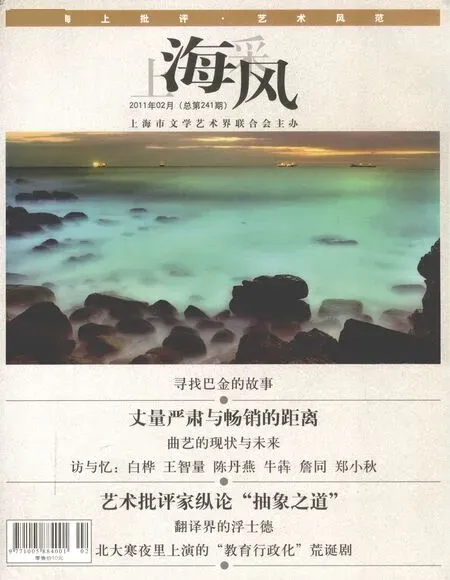回憶父親詹同
文/詹 詠
回憶父親詹同
文/詹 詠
許是望子成龍的心情過于急切,我在教育孩子時常常會顯得耐心不足。一日,兒子忽然發問:“爸爸,以前爺爺是怎樣管你的 ?”孩子的詰問許是對我的小小抗議, 卻突然勾起了我對父親的無限懷念。一轉眼,他已經離開我們整整十五年了。
父親詹同是我繪畫的啟蒙老師。自打我記事時起,就覺得他一有空就在畫畫、看書。那是我記憶深處的一個星期天,父親領著不滿三歲的我去看外灘的大輪船,我騎在他脖子上興奮得手舞足蹈,順手把他的眼鏡打落到黃浦江里。回到家里,我吵嚷著要畫大輪船,父親馬上拿出了毛筆和宣紙。看著我盡情地在紙上涂鴉,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以后的學畫經歷中,他就很少夸我了),就這樣,我被自然而然地引入繪畫的大門。三十多年過去了,那情形恍若昨日……后來,父親特意把我的第一幅畫裝裱起來,掛了好久。從我開始畫畫起直到工作前的所有美術作品,都被父親裝訂成冊,仔細保存著。其實他一直很在意兒子取得的點滴進步,這種情感,直到自己身為人父后我才開始真正懂得。

詹同自畫像
受家庭熏陶,姐姐詹螢也很喜歡美術,她從小就受父親指導,系統學習工筆繪畫、金石書法,練得一手好字并擅長篆刻,對民間美術也很在行。我們姐弟倆都是在父親帶領下走入美術這扇大門的。
中學時的我,對歷史和文學突發濃厚興趣,很少畫畫。父親非但沒有生氣和指責,反而很高興地在他苦心收集的眾多藏書中,找出很多相關書籍,指導我如何閱讀、怎樣系統和全方位地吸收知識。漸漸的,我開始用更廣闊的視野去觀察、在超乎繪畫技巧外的領域探索,汲取營養。父親對我進行的這些畫外功夫的啟發和悉心培養,在他去世多年后——當我由一名報社的美術編輯漸漸成長為少兒報刊的部門主管和主編時,當我在民主黨派的機關行政崗位上開始全新領域的開拓時——才讓我越發覺得受益匪淺,也終于讓我明白了一位父親對孩子的良苦用心,可我現在已不可能讓他親眼目睹我這些年取得的每一個進步,聆聽他的教誨了……
父親對我們很嚴格,要求我們:只要學就一定要認真。我在大學主修油畫專業,為了讓我不沉溺于形式上的嘩眾取寵,打好扎實的繪畫基礎,在我每周回家時,他都要親自畫一幅水彩或者油畫給我做示范,并拿出當年求學時的素描、速寫、聽課筆記,耐心地給我講解透視學、藝用解剖學、美術史……還時常講起他當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求學時,班主任董希文先生教的很多繪畫經驗和知識,但同時他也很尊重我的意愿,并不強求我全盤接受,只希望我在理解后去慢慢消化。每次過完周末,我總能滿載精神和物質上的食糧返回校園……我大學時期開始漫畫創作,畢業后踏入報刊出版這一行。十幾年前的繪畫圈里,子承父業的“父子兵”很多,畫風很近似,有不少已形成很鮮明的“家族風格”。姐姐的畫風與父親頗像,而我從小就喜歡叫嚷著要走自己的路,仗著年輕氣盛,常理直氣壯地說:“不做爸爸的翻版,要多學會些本領,最后再學爸爸的精髓!”在畫風上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受日式漫畫影響。對此,父親雖有遺憾,但還是很尊重我的選擇。或許那時他相信兒子確有自己的考慮,欣賞兒子的志向,只期盼著兒子真能早些領悟。直到父親去世后,母親洪金鳳告訴我,其實他一直擔心我浪費太多寶貴的時間,非常迫切地想把他大半生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讓我少走彎路。可那時的我根本不懂他的良苦用心……病魔過早地將父親從我們身邊奪走,帶走了他豐富的知識、一身的本事。而我被年少輕狂所誤,在有更多機會向他求教時,完全不懂得珍惜,如今只能從他留下的繪畫作品、文章、書籍以及留給我的記憶中去體會那諄諄教誨,更多的是無法彌補的遺憾與后悔!
2004年,為參加全國美展,我開始了停滯多年的漫畫創作。作品的主題是我思考了許久的,但因為那時工作繁忙,繪制時未花很多時間,只在截稿前幾天才趕著畫出來。作品最終落選,理由是不少國畫、油畫的專家評委們認為“此畫技法粗糙”。自認為該畫的寓意、題材都不賴的我,不服氣之余,靜下心來想起了父親的話。他常說:真正好的漫畫,應該是經久耐看的。一方面要有好題材,處理得巧妙、高級,另一方面,應該是技法高超的繪者精心創作的,哪怕是一揮而就、寥寥數筆,也是經反復推敲錘煉得來的,絕非常人認為的隨便涂上幾筆了事。他通過晚年的力作《擺平》,身體力行來告訴我這個道理的。那時,還在大學念書的我參加獻血后在家休養,父親為了讓我多學些技法,就開始創作這幅作品。在這幅以文藝復興三杰之一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為原型的漫畫中,父親用水彩顏料模擬古典油畫的效果,運用勾、染結合等多種手法,將原作中的眾多細節還原得惟妙惟肖——如今,用電腦繪畫軟件可以很方便地在電腦上做出那樣的濾鏡效果——而在十七年前,他完全是憑深厚的寫實功底和高超的手繪技法完成的。每次回想起那時的情景,我就更加明白,這是一種言傳身教,那一筆一畫間飽含了他許許多多的漫畫理念、藝術觀。
現在雖然工作繁忙,但我還是在業余時間堅持著漫畫創作。盡管力求自己的每一幅作品都能達到父親的要求,可惜得到他的評點只能是一種癡心妄想,唯有期盼他在冥冥中給我啟示了。
父親一直告誡我們姐弟:“這輩子,人品和畫品都很重要。如果死后還會有人記得你,記得你的畫,那才算沒白活。”幾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收到《諷刺與幽默》社寄來的樣報,這份久違了的中國漫壇第一大報——熟悉的報頭,全新的版式,更多的版面和信息量,更精美的印刷——讓我倍感親切。更令我心頭一熱的是,該報八版上登出了父親的一幅舊作:《百鬼斬盡,此精獨留》。沒過多久,漫畫家鄭辛遙先生又寄來了該報責編托他代轉的稿費單。我更是百感交集了。去世多年的父親,早已遠離眾人的視線,但父母的多年摯友時時關心著母親的健康,關心著我們的成長,依然有我們陌生的朋友記起他,記得他的為人、記得他的畫。我真心感謝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前輩、同行、朋友們,感謝大家多年來對我們一家的關心、幫助,感謝大家對我父親的情感,也感謝大家讓我更深切的理解了父親對我們的教誨。

詹同水墨漫畫《陋室銘》
父親走了整整十五年,姐姐和我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努力而出色地工作著,在繪畫上繼承著他未走完的道路,母親和我們一起共享著天倫之樂,孫輩們也茁壯成長。僅以此文告慰父親詹同。我深深地懷念他,一是為了提醒自己今后要不斷努力,做一個不丟臉的兒子,二也為了提醒自己亦要做個合格的好父親。
book=70,ebook=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