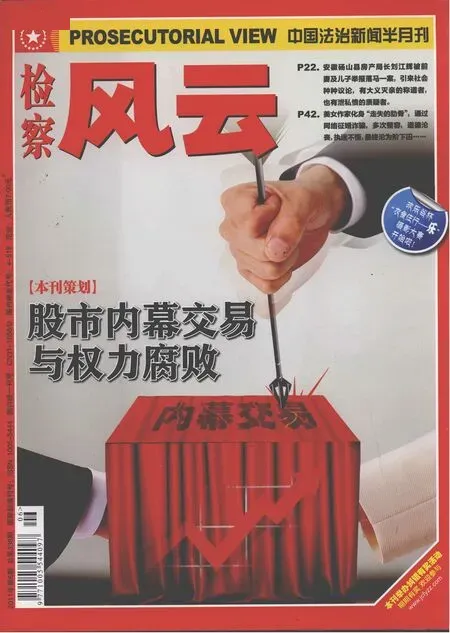內幕交易,證券市場的罪與罰
文/彭興庭
內幕交易,證券市場的罪與罰
文/彭興庭
我國的金融市場要走向成熟,公平是第一要件,只有充分保證了市場參與者的機會公平,把中國的金融市場演變為避免“絕對剝奪”的市場,才能真正為國家崛起和持續繁榮增長注入新鮮血液。
2010年11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依法打擊和防控資本市場內幕交易意見的通知》,要求證監會、公安部、監察部、國資委、預防腐敗局抓緊開展一次依法打擊和防控內幕交易專項檢查,查辦一批典型案件并公開曝光,震懾犯罪分子。
今年元月6日下午,中國證監會通報了兩起內幕交易案件的查處結果,分別是上海北孚有限公司及部分個人內幕交易“ST興業”股票案和張小堅內幕交易“SST集琦”股票案。這標志著我國打擊內幕交易行動的升級。而在過去的2010年,證監會將打擊內幕交易當成了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淳陶瓷案、中山公用案、黃光裕案、上海祖龍案等一批內幕交易大要案相繼查處、判決。
“內幕交易”歷史鏡相
自從有了證券市場,內幕交易就像鬼魅般如影隨形。
英國是股票市場的創始國之一,在股票市場的體制建設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在經歷光榮革命后,18世紀的英國煥發出勃勃的生機,其中,對外貿易特別是遠洋貿易迅速發展,股份公司紛紛設立。而其中成立的一家國家授權的壟斷公司,就叫南海公司,專門致力于南美洲的金銀礦藏和貿易。南海公司就是金融史上著名“南海泡沫”的主角。
在那時,雖然新公司的股票交易活動十分活躍,可另一方面,市場的公平交易機制尚未完善,這注定了這一時期的股票交易活動內幕重重,欺詐不時發生。以《魯賓遜漂流記》而聞名世界的英國小說家,同時也是新聞記者的丹尼爾·笛福曾寫過一本小冊子《交易巷剖析》,他甚至極端地認為,股票經紀體制于私是欺詐,于公是背叛,“這種交易基于欺詐,出自虛假,生于詭計花招、營私舞弊、爾虞我詐、掩人耳目、欺罔視聽的形形色色的騙局。”
“南海泡沫”事件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早的股票內幕交易詐騙案。南海公司在得到英國的特許壟斷權后,就放出消息說在美洲發現了金銀礦、香料等。人們被南海公司海市蜃樓般的利潤前景所吸引,狂熱地買入該公司股票。然而,在股價越漲越高的時候,當時那些知曉內情的政府官員(可以說是最早的內幕交易者)及時脫身,免卻了血本無歸的下場,但普通大眾卻損失慘重。在這場“泡沫慘案”中,就連大名鼎鼎的科學家牛頓也沒有幸存,他在南海泡沫中損失超過2萬英鎊。事后,牛頓自嘆道:我可以計算天體的運行,卻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
另一個著名的內幕交易案例,則是1814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利用拿破侖滑鐵盧戰敗的消息買賣政府債券,并因此而獲得暴利的事件。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后,美國在《1933年證券法》及《1934年證券交易法》中都確立了反欺詐規則,將“禁止內幕交易”正式列入監管范疇。但是,內幕交易并沒有因此而收斂。就是到了今天,美國雖然已經有了包括舉證責任倒置等在內的、堪稱世界上規范內幕交易最完整的制度體系,仍未能有效制止內幕交易。在2010年,《華爾街金融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出臺后不久,美國即開展了史上大規模的內幕交易調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執法部就表示,目前美國金融市場存在大量內幕交易,甚至遠遠超過預想。
中國證券市場的內幕交易
在中國股市并不久遠的歷史上,“消息市”幾乎貫穿始終。深圳證券交易所研究員何基報博士曾做過一項研究,他通過5 類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所引起股價的反應和換手率的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市場對各重大事件提前作出反應,尤其是高送轉、重大投資事件和控制權轉移等重大利好事件的信息披露引起了股價明顯提前反應和異常波動,這表明重大事件的信息在披露前就已泄露。此外,何基報博士的研究還表明,各類重大事件公告前,換手率急速放大,而在公告日后急速下降,公告前的日均換手率要比公告后高,這也表明,內幕信息已經被徹底泄露。
北京邦和財富研究所所長韓志國就認為,內幕交易是中國股市目前最大的弊端,幾乎每一起重組案例中都存在著內幕交易行為,尤其在創業板和中小板,內幕交易已經登峰造極。來自證券監管部門的數據顯示,在2010年1-10月,證監會新增非正式調查案件100件,和內幕交易有關的74件;正式立案的88件案件中,有42件是內幕交易案件。內幕交易占了證券市場違法違規的半壁江山。資本市場是一個信息市場,“消息”就是生命線。在內幕交易普遍的情況下,企業信息過早地反映到股份中去,嚴重打擊專業投資者搜集信息的積極性,也有可能導致價格操縱,最終降低市場效率。
在過去的2010年里,也有一些內幕交易案值得我們回顧。一是中山公用案,公司原董事長及總經理因涉嫌內幕交易被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而剛剛落馬的中山市市長李啟紅也被傳聞牽涉其中。二是黃光裕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30日作出判決,對黃光裕因犯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罪、單位行賄罪,三罪并罰被判有期徒刑14年以及罰沒8億元人民幣,對其妻子杜鵑因犯內幕交易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且緩期3年執行,并處罰金人民幣2億元。三是南京原經委主任劉寶春及其妻子陳巧玲涉嫌股市內幕交易罪案,這是全國首起國家機關人員涉足內幕交易被刑事起訴的案件。
被消息左右的中國股市,2010年表現可謂乏善可陳。可是,對于券商而言,則是百味雜陳。這一年,“老鼠倉”、內幕交易、PE腐敗等丑聞頻頻爆發,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謝風華案。謝風華是投資界的著名才子,時任中信證券投行部執行總經理,并著有《市值管理》、《中國證券發行制度與市場研究》、《保薦上市》等專業著作,卻因涉嫌ST興業重組項目中重大內幕交易的操作,而被證監會調查。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謝風華卻最終舉家逃之夭夭,成為“內幕交易逃亡第一人”。
內幕交易的罪與罰
內幕交易行為與證券市場一樣古老。然而,有關內幕交易的立法卻姍姍來遲,直到世界經濟大蕭條后的美國《1934年證券法》,才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內幕交易。根據《1934年證券法》第10條(b)款及證券交易委員會據此制定的規則10b-5的規定,任何投資者有意(包括耳語、偷竊在內)或無意從內幕知情人員(包括大戶)處得知可供圖利的內幕信息,均可能因內幕交易而遭到監控。然而,這條規則在頒布之初一直無所作為。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有關內幕交易的立法才再次被提上日程。《1984年內幕交易制裁法》規定,對內幕交易行為可處以相當于所得利益或所避免損失3倍的罰款;《1988年內幕交易與證券欺詐執行法》引入了舉證責任倒置,除非被告能夠自證清白,否則推定其有罪;《2000年公平披露規則》則要求,一個公司在對市場專業人士或有可能利用信息交易的股東披露其非公開信息時,此信息還必須同時向公眾詳細披露。相比之下,其他西方世界國家對內幕交易的禁止則采取了相對謹慎的態度。直到1980年,英國才開始禁止內幕交易,而日本是在1992年后,德國是在1994年后。
有人認為,內幕交易之所以遲遲沒被立法禁止,唯一的解釋是法律現實主義:在各國證券市場發展初期,證券市場在整個國家中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國家都沒有正式的法律對證券市場予以規制,更談不上對證券市場中的一個小問題予以專門立法了。這種說法雖有道理,但卻并不深刻。美國學者Coffee曾針對法律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提出了這么一種觀點:初步市場發展在前,然后才可能有以“股東中心主義”為基本理念的法律變革。在1929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前,美國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聯邦證券法。但是,“在一國經濟發展到第二階段,也就是一國試圖尋求更加長遠、成熟的經濟發展時,法律的變革是必需的。因此,法律秩序未必是發展初期的前提條件,但卻是市場成熟發展的前提條件。”
這對我們的啟示是,我國的金融市場要走向成熟,公平是第一要件,只有充分保證了市場參與者的機會公平,把中國的金融市場演變為避免“絕對剝奪”的市場,才能真正為國家崛起和持續繁榮增長注入新鮮血液。
著名財經評論員葉檀曾指出,對于涉及內幕交易的企業和人員,應該強調民事賠償,給普通投資者以司法救濟渠道。在我看來,民事訴訟在協助執法、威懾內幕交易方面的功能是極其有限。中央財經大學耿利航就曾指出,在內幕交易中,內幕人的交易行為和公司內部信息不公開實際上有不同的受害者。內幕交易行為和投資者損失之間通常沒有因果關系,投資者所遭受的損失主要來自市場信息風險,沒有理由將投資者的市場決策風險轉嫁給事后被發現的內幕交易者。所以,在對內幕交易的規制中,通過不同方式加強公共尤其是行政執法才是更有效率的選擇。

遏止內幕交易的有效性
Bhattacharya曾調查了103個國家制定、實施內幕交易法律的情況,結果表明,只有16個國家沒有內幕交易監管方面的法律,但真正實施內幕交易法律的國家卻只有35個,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實施內幕交易法律的國家則只有23%。Bhattacharya認為,這是因為內幕交易法律的執行非常困難,一方面需要付出很大的執行成本,另一方面沒有真正實施內幕交易監管的政治意愿。
在中國,情況也不會好多少。盡管在2009年,我國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七)》,對于內幕交易行為,最高可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再加上《證券法》、《內幕交易認定辦法》等,我國在內幕信息交易的法理和條文上應該都已有了完整的建制。然而,法律天生就有過剩的危機。中國法制的重要障礙并不在于法律的制定,而是法律的實施和執行。雖然我國內幕交易行為十分普遍,但內幕交易的查處、特別是刑事責任的認定,則寥寥無幾。
站在理性人的角度,制止違法犯罪應該有兩個手段,第一,是加大懲罰力度;第二,則是提高破案和量刑的概率。破案率和懲罰力度這二者的函數關系告訴我們,單純提高刑罰嚴厲程度,其威懾力是邊際遞減的。刑罰的嚴厲程度并不意味著刑罰的必定性,如果泄露內幕信息、內幕交易罪只是徒有其表,犯罪嫌疑人受到懲罰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那么,這個法條的效率就依然低下。
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有一句名言,他認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因為,即便是最小的惡果,一旦成了確定的,就總令人心悸。”
內幕交易難以被認定和取證,這種客觀原因當然存在,但我國證券市場的整體環境才是根源。我國證券市場有約2/3的國有股、法人股,這些非流通股權高度集中,在上市公司中“一股獨大”,這樣的后果,是“內部人控制”現象極其普遍。毫無疑問,股權的高度集中和內部人控制為公司管理人員實施內幕交易大開了方便之門。相比之下,我國證券市場中廣大“散戶”則投機心態嚴重,很容易受到市場“跟風”行為的影響。至于監管者,在“發展”的偏好下,對內幕交易行為往往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法律的效率在于執行,而不僅在于制訂。在內幕交易中,立法只是政府監管的外在形式,問題的關鍵在于執法行動的力度。特別是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只能通過法律條框定罪,很難對隱性的違法行為通過“模糊認定”的原則量刑。我想,遏止內幕交易還可以從市場角度出發,比如通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建立合理的薪酬體系,從而降低內部人實施內幕交易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