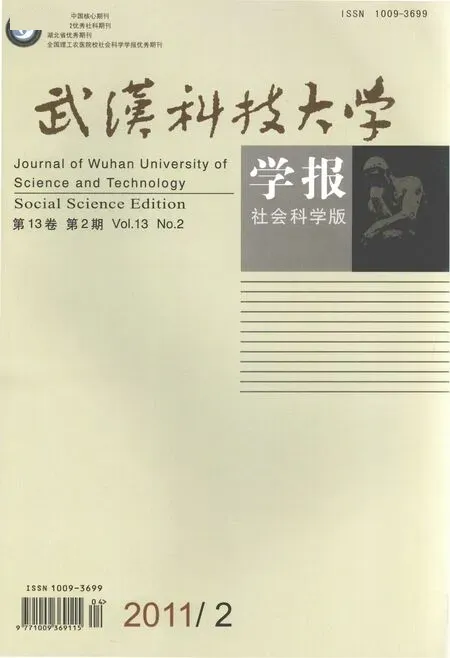略論晚清荊沙社會變遷
徐凱希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湖北武漢430077)
略論晚清荊沙社會變遷
徐凱希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湖北武漢430077)
鴉片戰爭后,在外國資本入侵和國內商品經濟緩慢發展的雙重刺激下,湖北荊沙城區經濟開始出現明顯變化。一方面,它逐步喪失了原有的自然發展狀態,逐漸納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經濟發展的軌道;另一方面,它則擺脫了以往發展的相對遲緩,增加了許多近代化的時代特征: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成為晚清荊沙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隨之而來的是商人社會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傳統商人組織的不斷發展。
晚清;荊沙;社會變遷
一
城市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市的形成與興衰,對于區域經濟的繁榮和社會進步都起著促進或制約的作用。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某一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演變,必然在這一地區的城市文明中得到充分體現。沙市古稱江津和沙頭,昔日為荊州古城之外港,自漢代開通至沙洋的大漕河后,江津成為江南向洛陽進貢財物和運送漕糧的樞紐,商業從此大盛,取代荊州古城,成為著名的商業要會。明清時期,沙市已位居國內十二大商業都會之列,是湖北僅次于漢口的重要市場。晚清荊沙經濟的發展演變,大致以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沙市辟為通商口岸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前一時期,荊沙經濟基本上仍處于自然成長的狀態。由于深處堂奧,外國資本侵入的直接影響尚不明顯,推動荊沙經濟發展演變的主要因素,是因川鹽破岸行楚而導致沙市川鹽總匯地位的形成。荊沙經濟的發展曾因此而出現一個短暫的“黃金時期”。川鹽大舉濟銷楚岸,不僅大大加強了四川與東部各省的經濟聯系,同時有力地刺激了荊沙商業和水上運輸業的發展。荊沙經濟驟然繁興,江面蜀舶云集、連帆接舶,從二郎磯一直排列至玉和坪。在港攬載的民船更是數以千計,船工、船民、力夫多時達四、五萬人。咸豐十年(1860)臘月一次大火,延燒江面木船竟有幾千條之多。川省鹽販因初次來荊州公賣,銷鹽既不熟練,納稅又無現款,鹽棧、鹽號遂應時而起,一度發展到20余家。米舶鹽艘往來聚焉,鹽運在很長的時間里成為沙市經濟活動的中心。荊沙市場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在此間得到明顯的增強。沙市一躍成為長江十大港口之一。湖南富商大賈為躲避戰亂慕名而來,相率遷居于此。隨著資本的集聚,荊沙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同光年間,僅沙市一鎮人口就已突破8萬,“煙民之藩應,商賈之輻輳,邑中稱最。”(光緒《江陵縣志》,卷五十·藝文)
中日甲午戰爭前后是外國資本侵略中國的一個轉變時期。由于中國的戰敗,外國在華工業投資伴隨著大量的商品輸入急劇擴張,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進一步解體,建筑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城市傳統經濟結構亦相應發生明顯變化。依據《馬關條約》第六款規定,湖北荊州府沙市辟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制作”[1];同時依據向開通商口岸或向開內地鎮市章程一體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等亦當一律享受,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駐扎。晚清荊沙經濟結構由于這一外部力量的直接作用而逐漸發生變化。
(一)外國租借地和商業機構的相繼建立
沙市鎮開埠后,外國政府官員和商人紛至沓來。光緒二十二年(1896)日本駐沙領事館設立,同年10月開設中國海關,英國人牛曼任海關稅務司。光緒二十三年(1897),日本商品標本陳列所在日本駐沙領事館西側開設,“頗受當地商人關注”。(《湖北商務報》第十三冊,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同年,英國開設駐沙領事館。光緒二十四年(1898)沙市發生中國民眾火燒洋碼頭事件后,清荊宜施道俞鐘穎與日本駐沙領事永瀧久吉簽訂《沙市日本租界章程十七條》,劃定沙市文星樓至玉和坪江岸為日本租借地,永租日本商民。嗣經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準將荊宜施道署從荊州城移至沙市鎮,以負責華洋交涉和地方治安。
外國商務機構方面。沙市鎮辟為通商口岸后,陸續前來荊沙設立洋行或支行的有太古、怡和、三井、三菱、日信、大倉、古河、瑞記、寶隆、和記、美最時、渣甸、禮和、味地、福來德、華昌、德泰等三十余家,其中以日本商家最多,留居荊沙的日本商人、技師及領事館官員,一度達到百人以上。日本領事館開署伊始,事關本地通商貿易者,無論土地、情勢等,一切不怠查報介紹,“以期引起日本商人注意,一面使沙市商人知我商品,冀相擴張,漸成進步,以收大利于將來”。(《湖北商務報》第十三冊,光緒二十五年七月)沙市開埠前,輸入荊沙的洋紗以印度棉紗居多,開埠后,日本棉紗源源涌入,銷路初未見好。日商經過調查,發現二十支細紗為本地織戶所樂用,于是改制十六支粗紗,且按中國織戶習慣,改為正旋。同時在推銷過程中,允許紗號賒款,以此來與印度棉紗和當地土紗相競爭。“現今日本人織物業年年進步,其種類亦甚多求中國人適用而改其染色、花紋、尺寸,得以擴充銷路,亦不為少”。(《湖北商務報》第二十七冊,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到晚清末年,荊沙城區已完全是日本棉紗的天下,對日本貿易已約占沙市對外貿易的67%,荊沙經濟受到日商日益全面的影響。
(二)傳統市場結構的變化
沙市開埠前,荊沙商人很少同漢口、重慶、長沙以外的口岸進行貿易往來,屬于典型的內貿型商業城市。適應湘鄂川三省貨物轉運的特點,荊沙市場以川鹽、疋頭、米谷和百貨的批發為其交易大宗,基本保持著以糧食為基礎,以布、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結構。沙市開埠后,隨著外國洋行、商行的相繼建立,農副土產輸出逐年增長,外國商品源源輸入,對外進出口貿易成為荊沙市場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輸出的洋貨主要有洋紗、洋布、染料、車糖、海產、煤油、洋傘等。輸出的農副土產主要是棉花、豆類、五倍子、桕油、芝麻、雜糧、絲、綢緞等。出口土貨多為洋行收購運出。如分屬日本在華三大棉商集團的安部、瀛華、大昌、日信、吉田、武林六家日本洋行,專事經營棉花購運,購棉之數,每年約七、八百包至千包,“以其貿易之大,市價幾聽其操縱矣”。(《農商公報》第十三期,第28頁)從事豆類購運的主要是三菱、三井、武林、大倉、嘉泰、湯淺等公司或洋行。英商和記洋行沙市分行則大量收購荊沙及附近各縣所產禽蛋、豬腸等,運至漢口加工冷凍后,報運出洋。光緒二十七年(1901),沙市口岸首次輸出芝麻1 300余擔,次年增加至23 800余擔,大多運往法國。外國洋行利用子口稅制及運輸、海關等方面的便利條件,不僅壟斷了荊沙農產品的對外貿易,同時還極力操縱其國內貿易,逐步形成了一個從城市到農村、為洋商服務的商業網。伴隨著機制洋貨的源源輸入,大批農副原料的大量運出,荊沙進出口貿易額逐年增長。光緒二十八年(1902),沙市進出口貿易額為150萬關兩,到1912年則猛增至570萬關兩。
(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現
荊沙地處九省要沖之區,西接巴蜀,右顧川陜,左控湖湘,下瞰京洛,舟車相會,水陸交通甚為便利,其中尤以水路運輸見長。東有便河與漢水相接,南與岳州遙遙相望,自古即為南北貨物交流的樞紐和東西貿易的連接點。光緒三年(1877)輪船招商局在沙市開設辦事處,辟設招商局碼頭。光緒四年(1878)漢宜線開通。同年,英商立德為開辟川江航線所造“彝陵”輪途經沙市停靠,是為外輪入港之始。但直至沙市開埠前,由于荊江北岸尚無躉船碼頭,輪船很少停靠荊沙,即或偶爾停留,只能錨泊江中,裝卸貨物和上下旅客全賴過駁,十分不便。商人運貨每每苦于“船舶到達時間經常不定,白天黑夜難以預計”。(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編《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第三輯,第264頁)艙位且常常不能滿足需要,不得不等候很長的時間。沙市開埠后,隨著對外貿易額的逐漸增長和運銷范圍的不斷擴大,為了使輸出農副產品能夠及時投入價格有利的市場,運輸方式以迅捷為貴,輪船運輸的地位日見重要。先后有怡和、太古、日清三家外國輪船公司在沙市設立分支機構,各自修筑棧房,劃定碼頭。輪船招商局沙市辦事處更是大興土木,修筑辦公樓、倉庫和棧房,辦理招攬客貨各事,并將福建舊軍艦泰安號改作躉船,安置于碼頭,以與外輪公司競爭。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前后,沙市至宜昌、漢口至沙市間已有固定輪船航班通行。
二
外國資本勢力的侵入,不僅對荊沙經濟造成深刻影響,同時也為荊沙傳統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作為荊楚古都和歷代封建王朝封藩設府的重鎮,荊州古城曾是長江中游地區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傳統手工業技術素稱發達,其中尤以紡織業和漆業著稱。“荊州麥熟繭成蛾,繅絲憶君頭緒多。”時至清末,每年運往西南各省的紡織品數量仍十分可觀,其中荊莊大布每年除有山西、四川、江西諸省客商來荊沙坐辦外,亦有本地商人自辦而銷售他處者,多為水運至雅州、重慶、龍潭、萬竹、云南、江西等地。“總共合荊郡南門及沙市夾貴街豬場口每歲所出約三四百萬疋,錢約二百余萬串。”荊緞、荊綾綢則行銷京城各地,最為馳名。
棉花及其制品在舊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地位的演變,是說明近代中國經濟變化過程和半殖民地性加強的一個重要標志。隨著甲午戰后荊沙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演變,荊沙傳統手工業發生明顯變化。鴉片戰爭后幾十年中洋紗、洋布的大量輸入,日益沖擊著耕織緊密結合的自然經濟基礎,造成荊沙城鄉停紡、停織現象日趨普遍。大量棉花從成千上萬架手紡車上轉移出來,棉產商品化進程顯著加快。同時,由于國內棉紡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出現了新的棉花消費方式。甲午戰后的這一系列變化,不僅有力刺激著荊沙城鄉自然經濟基礎的分解,并且逐步改變著素以手工制品為主要輸出品的市鎮經濟結構。這種趨勢隨著外國資本勢力直接深入荊沙城鄉和耕織進一步分離而變得日益明顯。沙市開埠前,土布仍是荊沙棉花的主要消費形式,剩余棉花則以西運四川為主。“棉布,江陵有京莊門莊之別,監利車灣者佳,蜀客賈布者相踵。南門外設有布廠”。(光緒《荊州府志》,卷六,第10頁)紡織之業“皆自土民操之,非有大股商人開廠制造也”。印度棉紗最初在荊沙并無銷場,“因數年前雖已用過,后經布商會議,以土產棉花甚多,是以禁用耳。”但因使用洋紗織布,具有需時較少,織布甚易,且紗絲堅細,堅則難斷,細則質輕,如以同等重量之紗織成布匹,其數量可比土產之紗數見長,紗縷亦甚勻細等優點,進入二十世紀初年,荊沙使用洋紗織布者日漸增多。“各鄉織布,其業逐年增進,然近年其經緯紗,共用洋棉紗。”“如日本棉紗本年多逾三千擔,因鄉人樂于購用,故銷流頗暢。”(《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冊,第16~37頁)武漢、上海等地各華資紗廠產品,每年亦有大批輸入。“輸入洋布類大字號,凡數十余家。”(《湖北商務報》第二十七冊,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宣統元年(1909),僅沙市輸入機制棉紗價值即達43.45萬兩,“最為巨擘”。
機制棉紗日見銷流的結果,一定程度地推動了荊沙城鄉織布業的發展,并對社會經濟產生深刻影響。隨著摻用洋紗織布者日益普遍,越來越多的農戶賣棉買紗,織成土布出賣。這不僅擴大了城鄉間的商品交換,為機器紡織業拓展了銷售和原料市場,進而為把農村手織業變成資本主義的家庭勞動準備了條件。“本口工價正廉,又系產棉最多之處”,有發展成為制造中心、特別是紗廠的適宜條件。“所出棉紗等運往重慶,運費既較他處運來者減省,價格自可便宜”。民國初年,先后有來敬臣購進高腳織機,與布商合股開辦“西亞”、“協合”等三家織布工場,共有織布機60余臺。四川臨水人梅溫如則購置德國織襪機5部,合股創辦“大豐裕”襪廠。又有吳子敬進口日本織布鐵機28部,用蒸汽機帶動,興辦云錦機器織布廠,成為荊沙棉織業機器生產的開端。
中國古代城市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意義往往要大于其經濟意義,城鄉之間的聯系一向十分有限,產品交流相對單一。隨著甲午戰后荊沙經濟的不斷演變,荊沙城鄉經濟聯系漸趨密切。甲午戰前,荊沙農村仍基本上停留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2]。同時,由于農村經濟自給自足,也拿不出較多的東西到市場上去出售。廣大農民同城市市場較少發生聯系。沙市開埠后,由于對外貿易市場的擴大,農村中商品性生產的比例逐漸提高,農戶對于城鎮市場的聯系和依賴程度明顯增長。尤其是甲午戰后荊沙棉產商品化的迅速發展,不僅明顯改變了荊沙農村傳統的農業經濟結構,使其從單一稻作為主,向著糧棉多種經營過渡;同時由于商品性植棉業的不斷發展,也推動了整個農產商品化的進程,特別是糧食的商品化,使其逐漸成為“農村普遍的而且統治的形態”。(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史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參考資料》(二),第261頁)晚清末年,沙市商業貿易額的迅速增長,市場的不斷開拓,大大加強了荊沙城鄉的商業往來。這種城鄉間較為穩定的多種經濟聯系的建立和發展,使得荊沙市場真正成為鄂西地區的經濟中心。
荊沙市鎮經濟的發展還帶動了新式農產加工機具的引進。作為盛產土布之區,荊沙城鄉的土布生產在外國資本入侵后的幾十年中,曾經頑強地阻滯了洋紗、洋布在這一地區的銷流。但時至晚清末年,國內市場上出現的花貴紗賤現象,使得手工紡紗愈益顯得不合算,遠不如賣出棉花買回洋紗織布出售更為有利。隨著荊沙市場棉花的大宗輸出,棉價且趨于漲勢,荊沙鄉間越來越多的農戶放棄紡紗,而將余力從事軋花。僅據沙市海關的不完全統計,光緒五年(1879)進口日本軋花機152臺,由于頗受一般農戶的歡迎,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已有總數達4 000臺的鐵制軋花機經便河輸入。“查此項花車,鄉民出資購用者無處不有,軋軋之聲,入耳可聽”。(《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冊,第28頁)
三
近代中國城市既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外國資本侵略中國的重點所在。中國城市近代化與半殖民化同步進行,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由于西方列強的商品侵略,近代中國的封建經濟結構日趨解體。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清末荊沙社會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以下幾個明顯的時代特征。
(一)商業貿易的發展是近代荊沙經濟發展演變的基本條件
“商業依賴于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3]。同近代中國許多沿海、沿江城市經濟的發展軌跡一樣,晚清荊沙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在外部力量的直接作用下,首先從商業貿易開始的,從而對城市經濟后來的發展方向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沙市開埠前,荊沙商業雖已有一定規模,但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封藩重鎮,市場仍處于半封閉狀態,更沒有與世界市場發生聯系。相對發達的自然經濟與便利的交通條件相結合,決定著荊沙商業長期處于自然成長狀態之中,仍屬于舊式商業范疇。沙市開埠后,外國商品開始大批直接運抵荊沙,通過眾多的洋行、公司和代理商,外國資本的觸角伸向荊沙及周邊各縣鎮。由于外商大量傾銷商品和收購農副土產,造成沙市進出口貿易額迅速增長。農副產品的集散和中外機制工業品的分銷,逐漸成為荊沙經濟的一個主要功能。這首先表現在商品流通數量的增長方面,宣統三年(1911)沙市的進出口貿易凈值已相當于開埠之初的10倍之多。商品流通的數量決定著市場的規模及輻射范圍。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沙市土貨開始直接輸出海外起,荊沙經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直接聯系起來,逐漸形成了一個以荊沙為中心的洋貨分銷和土貨購銷網絡。“本地區物產豐富,一旦開拓了遠方市場,突破本省范圍,商品會流通更廣。近年來,棉花、五倍子、桐油、芝麻、植物油等在長江下游各口及國外市場大量銷售就是這樣成功的例子。因此,對本港的發展,沒有理由持悲觀論點”。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4]。進出口貿易的迅速增長,為晚清荊沙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它不僅改變了荊沙商業市場的成份,同時也使整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帶動了交通、金融等行業的相應發展,推動著荊沙經濟逐步從傳統的手工業生產,向以機器生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階段過渡,走上了由商而工的商業城市經濟發展道路。為了適應大宗農副產品集散、加工的需要,一批新式產業陸續興建,它們雖然數量不多,規模有限,但在荊沙經濟發展的歷史上卻是前所未有的。
荊沙商業貿易的迅速增長,市場的不斷開拓,使得其與鄰近地區各主要縣鎮的商業往來日益密切,并且有力促進了周邊市鎮經濟的興起與發展。清朝末年,以荊沙市場為中心,相繼形成了江口、藕池口、斗湖堤、沙道觀、郝穴、草市、后港、彌陀寺、拾回橋、萬城、河溶、董市等一批農產品初級市場。這批小市鎮大多地處水陸交通干線附近,物產豐富,夾河為市。由于荊沙市場上農產原料的大宗輸出,帶動了周邊市鎮原來依附于農業的各種加工工業的獨立發展,使得以紡織為主的家庭手工業和專業機戶大量出現,進一步擴大了商品交換的范圍。這種城鄉間較穩固的多種經濟聯系的建立和發展,使得荊沙市場真正成為鄂西地區的經濟中心,成為湖北省內僅次于漢口的重要市場。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國內市場棉花需求量不斷增加的刺激下,沙市棉花貿易更是進入了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棉花輸出額常年保持在20~50萬擔左右,1936年更達到90萬擔,成為舊中國最重要的棉花輸出商埠之一。
(二)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與傳統商業組織的發展
中國歷代封建政權大多奉行“重本抑末”、“重農輕商”的經濟教條,視經商為“奸偽之業”,從而推行抑商政策。鴉片戰爭后,面對外國商品潮水般的涌入,朝野有識之士起而提倡商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湖廣總督張之洞宣布“通商惠工”三項措施,相繼創辦漢口商務局、工商展覽館和西式商場,竭力提倡商業,這對于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推動湖北商業的發展,不能不產生深刻的影響。
荊沙商業上百種,商戶幾千家,傳統的商業組織建立較早,且具有相當的活動力。各省客商先后在沙市組織行幫,建立會館。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輳,繁盛甲宇內,即令今京師姑蘇,皆不及也。咸豐七年(1857),沙市商人曾為厘金負擔過重,共同要求撤銷宜昌平善壩厘金局,否則“歇業罷市”。府縣官員對此多表同情,惟遭巡撫胡林翼嚴詞駁回,沙市商人雖最終被迫屈從,然其實力已可見一斑。同光年間,隨著荊沙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組織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僅沙市就有商人會館15處。來自安徽、湖南、四川、河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區及省內的客商,被稱為“十三幫”,這是一種具有明顯地域性的外地旅沙同鄉會性質的幫口組織,帶有濃厚的鄉土色彩。其中在省內以府為區域的有四幫,即漢陽、武昌、黃州和荊州府的安荊幫;以省為區域的有七幫,即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和陜西合組成的山陜幫;以大城市為區域的有南京幫;以外省州府為區域的有安徽省的徽州幫和太平幫等(見表1)。各幫中以四川幫根基最深,勢力尤大,荊沙各大鹽號、糖號均為川幫所開設。十三幫公推總會首一人,辦公的地方在旃檀庵,此處經常是荊沙官商名流的聚會和交易場所。

表1 沙市十三幫名稱及會館設置
除商人會館外,荊沙還另有商業會所11處。商業會所成立雖較“十三幫”為晚,但因其按行業組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血緣和地域的聯系,更具時代特點。隨著近代荊沙商業貿易的長足發展,荊沙商人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憑藉其資金、組織和活動能力,他們在城市經濟生活中的許多方面,起著操縱和壟斷的作用,并成為地方文教、慈善事業以及修堤筑路等許多社會公益事業的主要贊助者。“官場最重十三幫,凡事相邀共酌量,轎子跟班都擠滿,旃檀庵里接官忙。”(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編《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第四輯,第257頁)日益提高的社會地位和所擁有的較為雄厚的資本,使得荊沙商人成為影響這一地區社會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
商人組織的發展直接反映著市場的興衰。伴隨著荊沙商人社會地位的逐步提高,荊沙傳統的商業組織這時也相應有所發展。宣統元年(1909),湖北勸業道札文荊州等地迅速籌辦商會,商會為聯絡商情、振興商務之總機關,現鄂屬十府未能一律舉辦,因特先就荊州、沙市、襄陽、樊城、老河口等鎮,派委留日商務畢業生前往各處辦理,已札飭各屬,特令籌款整頓,限年內一律稟復核奪。次年,江陵縣沙市商會宣告成立。會長由川幫會首彭雨春一身二任,30名會董多為十三幫各幫會首。有會員632人,人數之眾僅次于武昌、宜昌商會人數,居全省第三位。
商會是商人勢力聚集所在。商會的成立對于打破地域界限、減少封建積習、促進貿易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通過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商會在清末民初復雜動蕩的政治環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宣統元年(1909)6月,湖北各界掀起要求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請愿運動,沙市商界積極響應,踴躍認股。盡管因連年水災商業疲敝,但廣大商戶對自辦粵漢鐵路仍心所向往,并抱以極高的熱情。經商會出面“開會招股,飆馳云涌”,三日內便認報股金500萬元。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后,荊沙城鄉人心浮動,出現了空前的擠兌湖北官票風潮,湖北官錢局在荊沙各兌錢處均被搗毀,大清銀行及荊州、沙市各錢莊都停止付款。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沙市商會出面,會同有關人士組成守望會,招募500余人的民間護衛組織,日夜維持社會治安;同時勸說當鋪,準許市民賒當,免算利息,大大緩和了金融市場混亂的局面。其后,沙市商會又在革命黨人與荊州八旗軍之間竭力斡旋,并參加雙方的談判,勸說清軍放下武器,開城投降,為荊沙和平光復及荊州古城免遭戰火破壞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都會之區,晚清荊沙社會經濟緩慢而畸形的發展,正是中國近代化艱辛歷程的真實寫照。由于中國社會并未經過一場真正的產業革命,社會性質的變化首先是通過貿易方式,從市場變化開始的,因而深入探討晚清荊沙社會經濟,尤其是商業貿易和商人組織等方面的發展變化,不僅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歷史文化名城的系統研究,同時也是探討和總結中國傳統商人組織特點的重要途徑。
[1]黃月波.中外條約匯編[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
[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62.
[3]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371.
[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67.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Jingsha District in late Qing Dynasty
Xu Kaixi
(Hube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uhan 430077,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Jingsha District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economy due to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capitals and the slow growth of domestic commodity economy.On the one hand,it gradually deviated from the previous natural state of development and moved onto the track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On the other,it developed faster and came to demonstrate many modern features.Fast growth in import and export became the precond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istrict in late Qing Dynasty,with which the social status of merchants was rising and traditional merchant organizations were growing.
late Qing Dynasty;Jingsha District;social transformation
K252
:A
:1009-3699(2011)02-0150-06
[責任編輯 勇 慧]
2010-12-23
徐凱希(1953-),男,江蘇宜興人,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湖北地方史研究.